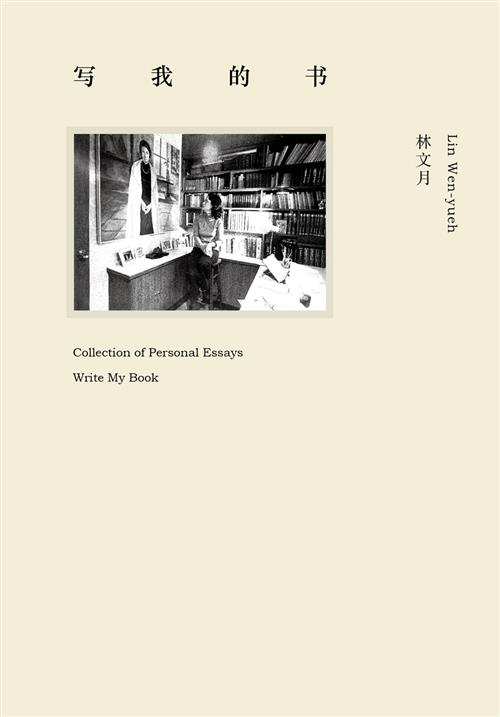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5-01-01
定 价:48.00
作 者:林文月 著
责 编:罗丹妮
图书分类: 中国现当代随笔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文学
开本: 32
字数: 80 (千字)
页数: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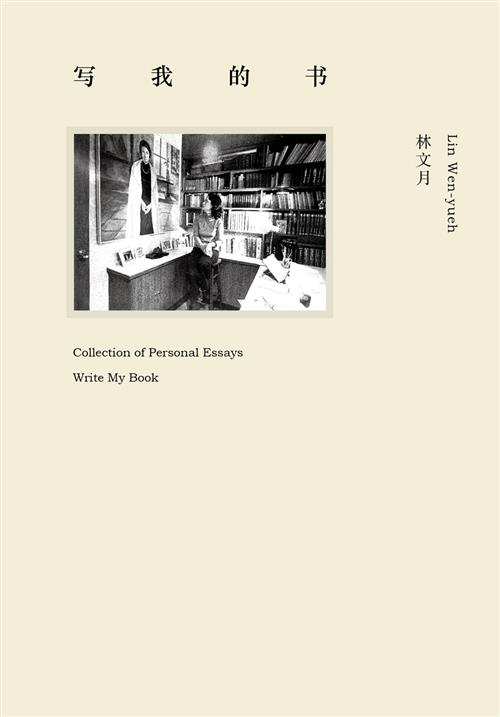
《写我的书》,原是作者在《联合文学》开设的专栏单篇,写自家书房藏书,“记录面对一本书无端端心情转折”,名为写书,实为怀人,围绕着书的动人情分,记述了一连串与书、与人有关的回忆。作者以《庄子》写外祖父连横和他的雅堂书局、以《论语》写京都一年时期与平冈武夫教授的师生情谊、以《陈独秀自传稿》写师长台静农先生晚年对遗失书稿的挂念……许多历历往事因为书而屡屡被翻阅,不仅开创了一种散文的新体制,也令读者看到了一代文人学者的气质与趣味。
林文月,生于1932年上海日租界,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迁归“陌生的故乡”台湾,是“台湾太史公”连横的外孙女、连震东的外甥女、连战的表姐,其家世脉络,独秀台湾文坛。精通中日语言文字,师从台静农,交游夏志清,今与董阳孜荣获台湾最高文化奖项,身兼文学创作者、学者、翻译者三种身份。1958年至1993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专攻六朝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并曾教授现代散文等课。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等。
那些年的林文月,是台湾大学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她学识丰富,气韵生动,文笔典丽,姿态优雅。台大中文系毕业的作家郝誉翔写道:“曾经听一位师长说,每逢他们那一辈人聚在一起,回忆学生时代,竟然整晚谈论的话题都围绕在林老师身上,可见林老师是青春时代最美好的记忆……我也听另一位师长感慨地说,天底下的美人很多,但如林老师一般,无人不以为其美的,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重要著作有论文《谢灵运及其诗》、《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澄辉集》、《山水与古典》、《中古文学论丛》;散文《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遥远》、《午后书房》、《交谈》、《作品》、《拟古》、《风之花》、《夏天的会话》、《饮膳札记》。其散文集《遥远》获第五届中兴文艺奖散文项奖、《午后书房》获第九届时报文学奖散文推荐奖、《饮膳札记》获第三届台北文学奖。
因为研究白居易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1972年在撰写《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的论文时开始翻译《源氏物语》全书,并因此获得第十九届“国家文艺奖翻译成就奖”。其后陆续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包括《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亦因在翻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之诸多成就,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特颁赠纪念赏。
自序
庄子
变态刑罚史
景宋本三谢诗
文学杂志合订本
源氏物语
日本书纪古训考证
论语
奈都夫人诗全集
巴巴拉吉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郭豫伦画集
Lien Heng(1878—1936):
Taiwan’s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Tradition
陈独秀自传稿
清昼堂诗集
文字,是鲜活的,而书,是有生命的。
是怎样一种因缘,让我遇到了一本书,得有机会阅读一些文字,丰富了我的生命!
其实,我大概是一向关心围绕一本书的心情转折的,关于书的内涵和与我相遇的因缘,以及某些人和事的记忆。书,不但其本身有鲜活的生命,并且与我自己的生命如此密切地关涉着。
我把那种面对一本书的心情转折记录下来。
——林文月
自序
选择了教学研究为职志,复偶尔以写作翻译遣兴,我的生活里,书自然成为十分亲密的伴侣,不仅书房内有数不清的书册,便是客间、卧室、饭厅,乃至于无可名状的小小空间的台面墙角,有时也堆放着一些书。这些书和那些书,对我的意义,其实并不一致。有些是正襟危坐而读之的对象,有些则是教学研究与写作翻译之余随意浏览者,另有一些,甚至因为书房拥挤,空间逼仄,不得不将其退次于书橱的后排,久而久之,竟或遗忘了其存在。
退休以后,属于自己的闲在时间比较多起来,漫读杂书,成为生活中颇堪安慰的习惯。原先被我束诸高阁,或隐藏于底柜深处的书,有时不经意间发现了,则有一种久违再遇的惊喜。于是,就地翻阅,三行五行,十页八页,时则索兴搬移到书桌上,彻头彻尾地读起来。夜深灯孤,重读的心情往往和当初并不相同。
是有一些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原因,未必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对于内容的感受领悟,而常常是那书的本身,以及关涉那一本书的属于我个人的记忆怀念。与书重逢的喜悦,遂渐渐沉淀,迷惘感伤之情,不由自生。
我把面对一本书的无端心情转折记录下来。
其实在很久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即是《一本书》。记述在一个阴沉的元旦假期,偶然闲步古书店,与一本外表丝毫不起眼的旧书相遇的经过。那是一本半个世纪前于日本大阪出版的现代诗集。出版社及诗人们,都名不见经传。我把那本略微残损的书从古书店一隅层层堆放的旧书籍中挑出购回,可能是一时好奇,或者竟是价钱便宜,抑或是其他更微不足道的原因,如今已不复记忆。然而,在些许慵懒的假期夜晚,随兴浏览那些不认识的作家们所写长长短短的诗章,内心渐渐不克自 主的情思汹涌澎湃。那种感动,我却一直没有忘记。为了对一群不相识的异国诗人表示敬意,我选出一首诗译成中文,题名为《陈旧了的Sentimental》,作者是我所不认识的泉浩郎。我把自己二十余年之前翻译的那一首日本现代诗重录于此。
我心远处的地平之极
小小的生活的过去啊……
它与现在的心仍牢牢连接着
尽可以将这么麻烦的过去舍弃掉
却赶不走地藏着
陈旧了的Sentimental。
我现在忽然取出西装
走在寂寞的野径……
外套的口袋里
有一封未及寄出的信
如今已不想投函于将忘的人的心
只好珍藏在怀中
陈旧了的Sentimental哟。
在我绞痛的心象里
将忘的人的
悲伤的心情溢涨着
滴落不已的回忆。
未及寄出的信的心哟
无人访的青春的暗室哟
伫立路旁的徒然的感情哟
独行于旷野
我的心热烈跳动。
经由一字一句,我感受到泉浩郎的“小小的生活的过去”,那种珍藏着的隐秘的“陈旧了的Sentimental”。一个个铅印的文字,在我阅读的刹那,如此鲜活生动地变成低沉微弱的又似乎十分热烈的声音。想当初那一位心象里溢涨着多感绞痛的回忆的作者,必然是诚诚恳恳将他的心情借由文字说出来给自己听。多么幸运,过了不知几多年后,我遇到了那一本书,阅读那一些文字,于是,文字都还原成为他当初的声音,进入了我的心象里,让我分享了那种“滴落不已的回忆”和“徒然的感情”。我听见泉浩郎对我的交谈,如此真挚,如此诚恳。
文字,是鲜活的,而书,是有生命的。
是怎样一种因缘,让我遇到了一本书,得有机会阅读一些文字,丰富了我的生命!
其实,我大概是一向关心围绕一本书的心情转折的,关于书的内涵和与我相遇的因缘,以及某些人和事的记忆。书,不但其本身有鲜活的生命,并且与我自己的生命如此密切地关涉着。
我把那种面对一本书的心情转折记录下来。成稿三数篇之后,由于偶然的机缘,在《联合文学》发表。自去夏至今,每月一文,倒也持续了一年。似乎成为一个专栏。专栏的名称,初时颇令我踌躇犹豫;不如姑且称其为《写我的书》吧。所写对象,未必是善本孤册,多 数只是平凡普通的书,然而都是我自己书房里的一部分,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和感情。重新翻阅时,犹如翻阅自己的生命,种种的情绪涌上心头来,愉悦美好的,或感伤激越的,时则清晰,时或幽微。我把那种感觉记录下来了,也把一部分的书和相关的资料影藏起来。每一篇的书写,顺其自然,初无次序安排,只是写到今年五月份,想起我略略知悉的“五月画会”的缘起,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亡故已五年的人,遂书成《郭豫伦画集》,并附制了一些图像。都是遥远的过去了。
回首迢递缈约,似已无法把握。然而,当我执笔为文,试着记述那些逝去的往事时,文字本身仿佛有其神奇的能力,会将缈约的迢递的过去一点一点牵引回来,于是,许多遥远了的过去,又都在我眼前了,十分鲜明,十分生动。写我的书,便如此在书写的过程里,自自然然地呈现出一些人事点滴了。
感谢《联合文学》在过去一年里,把我这些“写我的书”系列的文章刊登于杂志的前端,并结集成书。书名仍沿用专栏当初之题称《写我的书》。排在后面的三篇, 是系列以外的文章,性质上却是一贯的,故并录之。“陈独秀自传稿”虽非一本书,但一度为我所有,原稿已捐赠于台大图书馆。文章稍早亦发表于《联合文学》。Lien Heng, Taiwan’s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Tradition,刊登于《联合报•联合副刊》。“清昼堂诗集中所显现的诗人的寂寞”,系为郑因百师百岁冥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撰写的论文,所写的是因百师的两本著作,并透过其文字呈现了他的人格特色。亦系于书末。
林文月志于辛亥路寓所
二○○六岁次丙戌端午
1. 小小的生活的过去,陈旧了的Sentimental,林氏散文的代表作
特点在于,这是一本“写我”的书,个人性十足的“我的”,意味着这是一本跟林文月的生命历程有关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学术/文学/艺术方面的启蒙、师友、至爱,以及她生命中的各种“不可忘”。
2 . 以书写人,展现一代学人的气质与趣味
虽以书为名,实则写书与人的微妙关系。谈与书相关的人与事,谈书的内容、来历,在书中回忆了外祖父连横、师长台静农、郑骞、夏济安、叶嘉莹、日本汉学家平冈武夫、吉川幸次郎、神田喜一郎、韩国汉学家车柱环……许多历历往事因为书而屡屡被翻阅,不仅开创了一种散文的新体制,也令读者看到了一代文人的气质与趣味。
3.文字中既有学者的冷静简约,又有作家的细腻动人
台湾著名作家和诗人陈义芝:“林文月创作散文逾30年,游心于人世,寻思于学府,描写生命因缘、岁月感悟,以个人独特的欢愁与同时代的光影契会,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古人云‘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林文月的散文冰清慧美如其人,原因就在她胸中溪壑有深致。” 譬如在《源氏物语》一文写译作的斟酌苦恼,但也因此得来中外同业不吝给予各家译作版本的惊喜,她写着:“在艰辛孤独的译途上摸索前进,我彷佛突然看见有另一个同道的身影,那影像不是十分清晰,却觉得遇着颠顿危急之际,至少伸出去的手指可以触及一些什么”;又如介绍日本的《变态刑法史》,写道:“不宜夜晚阅读,不宜阴雨阅读。读时令人毛骨悚然,但发人深省。泽田抚松筚路蓝缕整理史料,功实不可没。”短短数语,文意兼美地记叙了读者心情与作者评价。
庄子
我的外祖父连雅堂先生在他五十岁之秋,曾与比他年轻的黄潘万、张维贤两位朋友,在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二二七番地(今延平北路)合作开设“雅堂书局”。当时日本占据台湾已经三十余年,正积极推行日本语文,逐渐禁止中国语文,从而达到消除中国文化之目的。然而,“雅堂书局”所售的各类书籍,及兼营的杭扇、湖笔、徽墨、诗笺等物,却都是采自大陆的国货,一概不卖日文书籍及日制文具。古文书籍,以线装经史子集类居多,同时也出售与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艺相关的书,如《三民主义》、《中山全书》,以及吴稚晖、胡适、鲁迅等人的著作。
“雅堂书局”开办之初,外祖父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到店,略事巡察后,若无顾客,即取书埋首研读。店内的新旧书籍各种,他都兴味盎然地饱览,遇有疑虑,必查究字书类书。有时买书的青年人请益讨教,也会热心指导。中午回家午膳,下午二时许再到书局。晚间关店前,他总是选一本书带回家阅读,次日归还书店。
文人不擅长营商,而“雅堂书局”的风格又与当时大环境的走向相左,这个专售汉文书的书店,初时业绩还不差,除台籍人士光顾外,甚至还有任教于大学及高校的日本学者前往选购。其后则逐渐因为收入不敷开支,加上日人没收禁书超过资金四分之一,虽以少采办、多卖存货苦撑了两年,不得不结束收场。
外祖父撰著《台湾通史》、编纂《台湾诗乘》、《台湾诗荟》的心意,乃为台湾保存史料,维护祖国文化;甚至开办“雅堂书局”而专售汉文书籍、中国文具,也显然可见用心深刻。在书店开办的期间,他也曾主持汉学研究会,于晚间七时至九时授课。至于他个人的兴趣和最投入的研究对象,则逐渐转入台湾语言和文物考古方面,这成为他日后出版《台湾语典》及《雅言》的基本;而在那一段时间里能够拥有一爿书店,日日埋首书中,遇有大小疑难即可就便查考,定必为他最满足欣慰之事。
书店结束后,他在距店址不远的台北桥附近赁一楼房,廉售存书。其后,遂以余书委托台南的兴文斋、崇文斋、浩然堂等书店代售,而他也移居于台南故里。
台湾为日本人所占据,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外祖父始终不甘为殖民地民。他五十四岁之年,撰一书函与张溥泉先生,令他的独子震东先生携书投奔祖国。此函句句凄怆动人,有言:“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地,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冑,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
舅父震东先生在国内的工作安顿后,为了保存台湾的文献,外祖父仍在台南继续研究撰著。越二年,五十六岁之春,因为我的母亲夏甸女士(外祖父长女)婚后居住在上海,而姨母秋汉女士(外祖父三女)也已自淡水高等女校毕业,外祖父毅然决定携眷内渡,遂其终老祖国之志。
行前,日本台湾总督府委托尾崎秀真,向外祖父洽请将所藏的台湾文献割爱。通史既久已刊成,而此行恐暂无返期,外祖父便将书以半卖半送方式出让。他旧藏的书刊,一部分归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所有,另一部分归总督府图书馆所有。唯后者于二次大战期间,因遭盟机轰炸,竟无片纸幸存。
外祖父和外祖母晚年居住的寓所在上海江湾路公园坊八号,是我父亲林伯奏先生的房产之一。我的母亲就近照顾了双亲的晚年生活。
外祖父定居上海以后,仍以读书写作及持续关怀台湾文物为生活重心。他五十九岁之年六月二十八日,因肝癌逝世。身后遗留的许多文稿和书籍,由于舅父当时远在西安工作,所以部分由我的母亲承收保管。
抗战胜利之次年,我们举家自上海返归台湾。在众多琐物间,母亲竟然把外祖父遗留的书籍也安然带回来。而在繁忙的家务之间,我常见到有时她会抚摸那些已呈黄褐色的旧线装书。她必然是在怀念着她的父亲吧。
及至母亲自己也衰老时,她把外祖父的书送给了我。母亲过世后,外祖父遗留给她的书,遂成为母亲遗留给我的宝物了。我小心摩挲着书面虽然微损而内页仍完好的这些书,怀念着母亲,也怀念着外祖父。
外祖父逝世时,我尚未满三岁,仿佛记得一些事情,但其实许多事情也可能是听母亲的叙述,或者竟是日后阅读他的诗文,乃至于阅读他阅读过的书籍而想象亦未可知。
外祖父遗留的线装书之中,我最珍视的是一套四册的《庄子》。这套郭象(子玄)注,陆德明音义本,系民国二年扫叶山房石印,于民国三年三月出版。外祖父曾言:“台湾僻处海上,书坊极小,所售之书,不过四子书、千家诗、及二三旧式小说。即如屈子楚辞、龙门史记,为读书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台,无处可买,又何论七略所载四部所收也哉?然则欲购书者,须向上海或他处求之,而邮汇往来,诸多费事,入关之时,又须检阅,每多纷失;且不知书之美恶,版之精粗,而为坊贾所欺者不少。”(《台湾诗荟》第十八号“余墨”)“雅堂书局”所售的线装经史子集类,都是由外祖父亲自选择订购,书目种类丰多,版本精美讲究。主要的来源为扫叶山房,千顷堂。不过,这套扫叶山房《庄子》倒未必是他开办书店之后才拥有,因为早在“雅堂书局”时期以前,他已经不止一次旅游过大陆;相反的,也可以说主持采购书籍之际,他对于内地的出版情况已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才能选择优良的版本。四册线装书虽然年久而发黄,封面略有渍迹蠹痕,但内页十分完好。非仅原书的大小字都清晰可辨,外祖父在字旁所加朱笔圈点,乃至工整的眉批,亦皆历历犹新。从这些眉批圈点,颇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得感受。《在宥第十一》起首“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诸句旁字字加朱圈,上有眉批:“在宥,即自由。其音相近。在宥者,天然也,自由者,人为也。人为之患,障以法律,天然之极,放于德性,不治而有治矣。”《天地第十二》:“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上有眉批:“群治至此,则无所谓道德,所谓功名,所谓权利,所谓义务。至矣,尽矣!”外祖父崇佛亲道,虽关心民生政事,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无为而治。而身为史家,读书之际,难免比照古今,多所感慨。《胠箧第十》:“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眉批虽只书:“一部二十四史,皆作如是观。”但语重心长可以感受。
不知道圈点批写这些字时,外祖父是怎么样的境况?几案之上除了书籍笔砚外,尚有一只小茶壶为伴吗?他不嗜酒而好茶。那只常年使用的小小茶壶,后来,母亲也送给了我。他阅读的时候,可能把眼睛近贴着书。黄得时先生在《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四期有一段回忆他年少时的文章:“另有一次,我到开设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功学社对面)的雅堂书局去买书。当时,只有先生一个人在看守店里。但是他的近视眼却贴着手里的书,一心一意正在看得入神,完全没有感觉有人进来。等到我向他打招呼,他才吓了一跳,猛然抬头,脱去了眼镜说:‘哦,得时君,你来得正好,昨天商务印书馆寄来了英国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写得非常好,你看看吧!’他随即从书架上拿下那本书给我,立即又套上近视眼镜看他手里的书。”
黄先生回忆的文章,写得极为传神,把一位爱书提倡阅读的老人栩栩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摩挲着手中微黄的书叶,指尖追踪那上面的朱笔圈点和眉批,仿佛可见清癯的深度近视眼的外祖父正认真地逐字逐句细读着这一本线装书《庄子》。
变态刑罚史
这一本日本的线装书《变态刑罚史》,是许多年以前静农师送给我的。台先生退休后,日子过得平静闲淡,我有时自台大下了课,在回家中途去拜访探望。有一个秋日午后,他见我趋访,说:“你来得正好。我整理小书房,有些买了多年也看不懂的日文书,送给你翻翻。”他指着堆放在“龙坡丈室”一隅的一些旧书籍。
“龙坡丈室”是位于台北市温州街十八巷六号的客厅兼书房。主要布置是一个稍大的书桌和一把老藤椅。台先生在那里读书、写作书法和接待客人。书橱在他的背后,四壁悬挂着沈尹默、张大千等名家书画。而桌上、书橱里,甚至窗台边,到处都是书。为了收藏过多的书籍和区分客厅与书房,台先生曾经在客厅与卧房之间装修了一个“小书房”。那一个狭长的空间,靠墙安装了一大排书柜,确实减轻不少客厅里放置的书的负担,但那个较小的书桌,显然有些局促,何况房间窄,通风不佳,夏日闷热冬季冷,台先生还是习惯在原先的大桌上工作。不过,那个“小书房”紧贴“龙坡丈室”,门一推就可以找到书,倒像是丈室主人的私人图书馆。非仅供藏书之用,我发现里面似又收藏了一些烟酒,尤其逢年过节各方赠送的良烟佳酿,往往堆放在桌面和地板上。
台先生所说的买了多年的日文书,包括这本《变态刑罚史》,大概是从“小书房”取出,暂时放置在两间书房连接处的墙角。那一阵子,台先生身体相当硬朗,他颇费了时间和精神整理好一些书,分赠与有些老学生。他告诉我:“刚来台湾时,有些日本人还没有回去,他们把带不走的东西摆地摊卖。我常常去延平北路那一带逛逛,买一些便宜的书。看不懂文字,看看插图。”
台先生送我的日文书,果然都是有插图的。
《变态刑罚史》共七十六页,插图竟占二十四页,而且全页为图者有十四页。这些手绘的各种刑罚图,虽然笔调拙稚,但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十分可怖。这大概是我始终不敢正式阅读,将其束诸高阁的原因。
最近,我决心要面对这本书,遂分两次看完。
这是大正十五年(1926),由日本文艺资料研究会出版,泽田抚松所撰的专著。据前言,本书为日本首现之刑罚史。泽田氏解释所谓“变态”,并非将刑罚史写成变态的样子,而是指:“人类对人类加以刑罚,乃是一种人类生活的变态。”全书分二篇,第一篇自日本太古至德川时代之前,第二篇自德川时代至明治时代。显然详于今而略于古,而后半段又以德川家康所制定的刑罚为主,明治时代的内容仅有半页。
泽田抚松著述的态度严谨,文笔简要古朴。他追踪日本最古的刑法至神话传说时代。素盏鸣尊因暴虐无道有罪,将被定刑。太古时代的日本人,认为罪者秽也,故有罪便行祓以赎之。而行祓之目的在赎罪,所以犯罪者须提供物品。至于所提供物品之多寡,端视其犯罪之轻重而定。素盏鸣尊因罪行重大,提供所有物品乃至衣着,仍不足以赎其罪,故美髯被剃除,手脚的指甲亦被拔去。著者写:“受此变态刑罚的素盏鸣尊,被逐出高天原,限居于八重垣之内。”
泽田氏依据日本古史《古事纪》、《日本书纪》推论,除了素盏所受剃髯拔指甲的毁伤刑之外,自上古又有死刑、黥刑、徒刑及追放刑等刑罚。他又写:“欲知上古之后,刑罚如何进步(或退步),须加研究。”遂有各类刑罚发展之探究,使这一本书充满了许多“变态”可怖的文字。不过,作者依据史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纯属学术之论述,不为文学之夸张渲染。例如关于切腹,颇费笔墨,盖以切腹为日本刑罚之中最具特色之故。
圣武天皇神龟二年(725),因受佛教轮回思想而有再生观念,而人一旦受死刑则不可再生,以其太残酷而废除死刑,当其罪者改为流放。然而,其后纵火、盗贼等罪犯猖獗,四十八年之后,光仁天皇宝龟四年(773),遂又恢复死刑。阅读至此,不得不掩卷慨叹。人对人用刑,诚为“人类生活的变态”,但无为而治,甚至慈悲为怀,竟皆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
至于切腹刑之始,泽田氏系于足利时代(1336—1573)。谓时至足利时代,各地豪族任意制定刑罚,绞首、车裂、火焙、烹杀等酷刑不一而足。但身份高者即使当死罪,亦不加刑,而令其自尽,称为切腹。此说在时间上,与小学馆的《国语大辞典》所称“切腹为江户时代(1603—1867)科于武士之刑罚,为死刑之最轻者”,二说略异。大概泽田氏之说在追究其源,辞典则说明此刑普及之现象。不过,切腹刑于武士,殆无疑问。
关于切腹,本书于众刑罚之中,着墨最多,唯仅就事论事,相当抑制笔触。所以血淋淋的场面,虽然可怖,反不如往昔读过的三岛由纪夫《忧国》写步兵中尉切腹的一段文字,甚至李昂《杀夫》中屠夫宰猪的景象,由于使用文学的渲染,更为刺激可怖。泽田氏行文,不仅字字句句必有依据,并且时有考证辩驳之处。如本章开首云:
切腹,以行之于庭上为正式。重叠二张榻榻米,其上铺以浅绿色棉被,复撒以细砂。德川时代之切腹形式如此。尝见《忠臣藏》(代亡主复仇之古装戏),切腹的场面用白布敷之,显然是不知故实者之误。所谓切腹,系对武士刑罚的一种宽典,故避免鲜血染白布之惨状,而特使用浅绿色者以铺之。
泽田抚松以相当大的篇幅详记此刑各节。举凡执法之人物,行刑之顺序,乃至刑毕后事,等等。其中,引我注意的是,古时日本武士讲究礼节的一面。被科以切腹的武士,无论胆子怎么大,刀术如何高,都不可能刀刺入腹立即毙命,所以身后有持利刃执行斩首者,称为“介错人”。优秀的介错人在切腹的武士举匕首刺入腹部的刹那间落刀,可以减少服刑者的痛苦。所以武士临刑来到刑场与介错人会见,先询问其姓名。介错人报出役职及姓名后,鞠躬殷勤道说:“不肖担任介错。请平心静气。”而服刑者亦行礼道:“劳驾了。多多拜托。”
这种传自德川幕府的刑罚规矩,实源于德川家康。家康虽是武将,但是他好儒而亲善书籍,招聘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硕学儒臣查究古书旧记,编成幕府政治根本的各种制度。泽田氏称赞道:“家康不愧为大政治家,知虽以武力得天下,不可以武力治天下之道理”,遂制定德川家的宪法。《德川百个条》,虽是其家族的法典,却由于详尽而且巨细靡遗,又因德川一族掌权甚久,乃成为十七世纪以来日本国家刑罚的中心。《变态刑罚史》的后半部,便是作者条析《德川百个条》而成。
施刑之目的在惩罚犯罪者,其轻重则依所犯罪之小大而定,故有游行示众以惩之条例。其中,比较特别的有两条:一是僧侣犯妇女,二是殉情未遂者,都与男女情欲相关。此等罪犯都系以绳,牵行如犬于大街,而示众于日本桥的桥畔。日本桥至今仍为东京最热闹的区域,于其桥畔设简陋小屋,三面围以草席,前方敞开,令众人围观,但立双重木栅,防止观众过分贴近犯人。这种示众的刑罚,目的在羞辱罪人。男女私情本见不得人,故以游街示众罚之。作者对此,除简要说明刑罚内容,又比照历史为记。僧侣示众,通常不是个别办案,而是聚合五六人后,同时示众。天保十二年(1841)三月,曾一度以四十八个僧侣同时示众,足见色戒犯者为数甚夥,小屋有必要扩大。至于殉情未遂而一方已死,其存者示众,若双双未死,则男女同时示众三日。而僧侣或殉情犯人,其身前都有告示牌说明犯罪经过,且记其姓名、住所与年龄。僧侣则更系其宗派、寺名及身份职称于告示牌上。这种示众的刑罚,通常另有比照其罪轻重的各种后续惩罚,但即此一项而言,身体虽然未必受损伤,心理难堪之程度已足想见。
诚如泽田抚松所言:人对人科加刑罚,是人类生活的变态;如果没有这种变态,则无法达到人类生活共存之目的吗?而即使古今世界各地都有这么多的变态刑罚,始终仍无法遏止犯罪,又该当如何解释呢?这些问题,泽田氏执笔之际或者曾经思考过,却非本书所能处理的问题和范围。而这些问题,也是全人类无论刑罚学者专家,乃至普通一般人都应该继续思考的事情。
这一本《变态刑罚史》,不宜夜晚阅读,不宜阴雨天阅读。读时令人毛骨悚然,但发人深省。泽田抚松筚路蓝缕整理史料,功实不可没。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