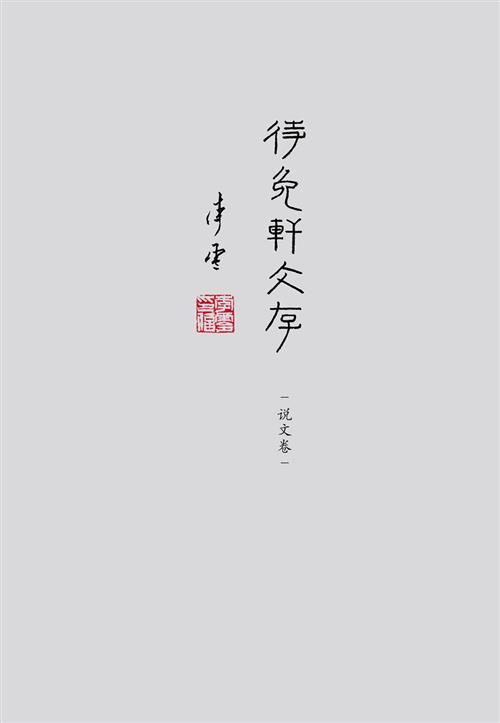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5-06-01
定 价:88.00
作 者:李零 著
责 编:吴晓斌
图书分类: 语言文字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中国古代史 文字学
开本: 32
字数: 380 (千字)
页数: 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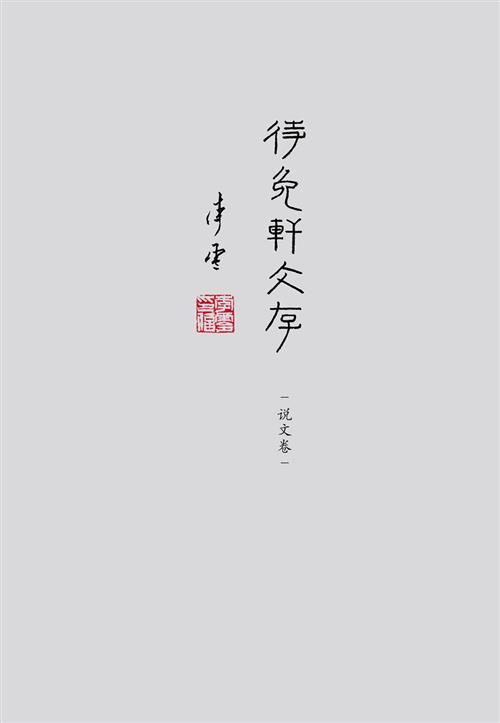
著名学者李零的有关古文字研究,重要的论文差不多收集于此书中了,主要分为文字考释、西周甲骨、商周铜器、东周铜器、简帛和战国文字等几个部分。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有方法论方面的阐述,有释读古文字的专业论文,也有借助古文字的研究来解读相关的历史、文化、思想,等等。
李零
1948年生,祖籍山西武乡。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
主要著作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
《郭店楚简校读记》
《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丧家狗——我读<论语>》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
《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
《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
《中国方术正考》
《中国方术续考》
《入山与出塞》
《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
《李零自选集》
《放虎归山》
《花间一壶酒》
《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
《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
《待兔轩文存•读史卷》
《小字白劳:李零自序集》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文字考释】
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3
为《说“引”字》释疑/13
古文字杂识(十五则)/16
【西周甲骨】
读《周原甲骨文》/45
读周原新获甲骨/88
【商周铜器】
“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99
重读史墙盘/106
论■公盨发现的意义/133
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152
冯伯和毕姬/169
【东周铜器】
春秋秦器试探/177
读小邾国铜器的铭文/191
楚■陵君三器/204
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212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259
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264
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307
【简帛和战国文字】
读《楚系简帛文字编》/315
读九店楚简/349
读上博楚简《周易》/365
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392
读清华简《保训》释文/397
视日、日书和叶书/404
自序
我有个梦想的书屋,四面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实的办公室呢,则是学校所赐,暂时借给我,地点在北大老化学楼的三层,挨着女厕所,很小。我刻了块匾,不好意思挂起来。
我说,北大有个临湖轩,我有个临厕轩。
“待兔轩”是我的斋号,命室之由见我的小书:《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的第一种,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我讲了个故事,这里不再废话。
我是个为兴趣而读书而写作的人,书是副产品。我从没想过读多少书才算合适,也从没想过写多少书才算合适。读书写书,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玩哪儿算哪儿,不是为了学校,不是为了教育部,更不是为了他们的钱。
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我居然写了不少东西。本来就是加速度,缓慢上升,2000年后,突然提速,和生理水平相反(我的记忆正加速流失),回头一看,吓一跳。
以前写得少,名气小,出版难,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为了单位和学术界,为了领导和老同志,为了“媳妇熬成婆”,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后来,等我终于“熬成婆”,我觉得非常失落。为了会议,为了评审,为了各种固辞再三不得已的“红白喜事”,我还是一样身不由己。我问自己,难道你就这样下去吗?
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
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白劳”就是代价。
“白劳”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学界并不例外。
当年,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龄最轻,地位最低,当过小媳妇儿。我想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当年的我,“白劳”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至1978年,考古所编《新出金文分域简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基础工作就两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刘(刘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个油印本,我俩的名字还排在前面,但书印出来,却排在后面,排在“0%”后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我参加过最初的资料准备,书要一本一本对,拓片要一张一张找,除了室内整理,还要到各大博物馆拓铜器,我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名没有,书没有,什么都没有。老刘说,你为这书付出那么多,别人装糊涂,我知道,留个纪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给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卢(卢连成)、陈平和我。1982年,我在沣西挖西周遗址,也是跟他们在一起(还有郑文兰)。最后,我和陈平调走,老卢也离开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劳累也“雨打风吹去”。
俞伟超先生知道我的经历。他说,你的时间并没白费,所得还是胜于所失。
真是这样吗?破涕为笑吧。
我调过两回工作,早就没有归属感,经历使然,教训深刻。我已看穿看透,与其“从一而终”,不如“移情别恋”。我才不死心塌地跟谁干,特别是有如“修长城”的浩大工程和集体项目。
摧眉折腰,我不开心;呼奴使婢,也不乐意。最好的选择,还是自己领导自己。我是单枪匹马惯了,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四面出击,其实只有一条枪。
杂文不谈了。学术,涉及三个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三古”是基础学科,我重视,我喜欢,但对我来说,这是训练,不是目的,我更关心的是问题。三代无学科,问题并不属于哪个“古”。更何况,我是现代人,我的立足点还是现代。
三十多年来,跟着问题跑,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我还涉及过很多行当,至少有五六种。研究《孙子》,涉及军事史;研究方术,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简帛古书,涉及思想史;四出访古,涉及历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艺术史。虽然,这些行当,没有一行是我的“本职工作”,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还承认我。
人文学术,所有文科系,我都插过一脚。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教过书。
孙悟空语录:“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把这两句抄下来,挂在墙上。
他是中国的自由神。
书不在多。
一个诗人写一辈子诗,最后能有一首诗被人记住就不错了。
书也是这样。
但这需要以勤补拙,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谁都只有一条命,我不比别人聪明。书都是逐渐写薄的,为了薄,先要厚,厚积才能薄发。
我是个按计划写作的人,单篇文章是为了编书,编书是想讲出点儿道理。其实,我做的一切,都只是铺垫,不管是为自己铺路,还是为他人铺路。
研究学术,我是从文献整理入手。最初,我是拿《孙子》练手。这方面的文章已收入《掖孙子业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后来,我迷过一段古文字,深陷于拓片而不能自拔,没有一帮老同志帮忙拔,我还拔不出来。根儿都拔掉了,剩下的只是训练。
再后来,跑国外,我是靠方术屠宰时光。最初是写散稿,然后才汇编成书。《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是这么写成的。翻译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是配合这一研究。
研究简帛,我也有个准备过程。比如写楚帛书,写郭店简,写上海简,我花费了不少时间。特别是上海简,很多精力都白费了,我很后悔。所幸,我还写了一本《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书是为了讲课。
我在学校讲经典,也是先讲后写。比如《丧家狗——我读掖论语业》、《兵以诈立——我读掖孙子业》,还有四本一套的《我们的经典》(已经印出三本),就是从课堂而来。
历史地理,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还没编。
访古,有不少日记和照片,也要整理。
考古和艺术史,我一直在写。老文章多已收入《入山与出塞》,新文章还没编;我还写过一本《铄古铸今》。
这些都是铺垫,为了我心中的学术。
本集所收,是我的学术论文,不是全部,只是上述集子(已编或待编)以外的散稿,侧重点是文史方面。我讲历史的文章,差不多都收进去了;文字方面也选了不少(不是全部)。
十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论文集:《李零自选集》,就是此书的基础。现在有所删削,有所增补,有所订正,分为两册,一册读史卷,一册说文卷。
这两册书,只是过河的石头。
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就是圣贤,也不能不出错。过去,我说过一句大实话:“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216页)
我也曾经年轻。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老想不明白,好些年纪一大把、头衔一大堆的人怎么也会犯错误,而且是最低级的错误。他不明白的道理,其实最简单,再大的学者也是人,是人都会犯错误。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这门学问可大了去。研究错误是一门大学问,报上说,国外有这门学问,国内则未之闻也。
错误,意必固我,是人都会犯。累,会犯;忙,会犯;年轻,有精力没经验,会犯;年老,有经验没精力,也会犯。怎么都会犯。光是生理、心理、气质、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记忆力差,思维跳跃,推理过度,联想失控,也是陷阱。
错误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而且肯定是绝大部分。黄金不可能比沙子多。
我知道,我的书,错误一定很多。我不是精密仪器。
不犯错误不是人。机器才不犯错误(要犯也是跟着它的主人犯)。
错误分两种,一种是大错误,在总体认识上犯错误;一种是小错误,在字词、标点、引文等各种细节上犯错误。前者是探索性的错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不一定能以对错论功过,如果它是为大问题当“靶子”,能以自己的失误,启发别人,引起争论,引起思考,很可能是成功之母、正确他爹。后者,一般叫“硬伤”,错就是错,不容商量。这样低级的错误,当然应尽量避免,却最不容易避免。
这次编书,我只对后者做一点订正,不做大修改。认识上的纠正,写在补记中,也只限非说不可、不说就可能误导读者的地方。我对别人的错误没兴趣,自己的错误也不想十步九回头,不断找补。无论大错误还是小错误,都只是当作一种认识过程来反省和检讨。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就让它付诸东流吧。
不过,有件事,我倒有点后悔,即过去发表的论文,脚注不周密、不统一,对读者查核原文不方便。这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过程,部分是因为我国的学术界原本就没规矩。刊物,吝惜版面,往往求简,有人甚至认为,脚注太繁是为了骗稿费。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我在《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的后记中有详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
这是我的回顾与检讨,是为序。
2009年12月2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 相关图书
1.李零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力,贯穿三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旁涉诸多学术领域,积累精深,治学广博。
2.本书历经五六年之久,才编辑出版此书,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还是书中几百个古文字的精心造字,都是用心用力甚勤甚苦。
3.内文精选适宜的纸张,封面选用精美的布料,采取高贵的布面精装形式,给予本书不可多得的品味和气质,实为可读可藏的佳作。
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
一般对古文字研究缺乏了解的人,常常会对文字破译有各种误解。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起新旧之争,虚构了许多新旧对立。像“宏观阐释”与“考据学”的对立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们看来,文字破译是老掉牙的“传统思维”,与“宏观阐释”毫不相干(楼上楼下,不在一个层次)。前者是靠大处着眼,假设先行,而它靠的却是精雕细刻,积沙成塔。
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想未必是这样,或者至少说不完全是这样。
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
朱德熙先生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文字破译最像侦探破案。这个比喻很形象。
文字破译与侦探破案的相像之处,首先是它很重想象,有时能像福尔摩斯,凭蛛丝马迹,就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虽然现在有不少学者都在总结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文字的结构分析(偏旁分析),声旁啊,形旁啊,六书呀,三书呀,很重视,从中归纳出许多规律。但我们学这些东西,又用这些东西教人,常常免不了会有“纸上谈兵”的感觉。因为它很难解决的是“运用之妙”。
古文字学的“运用之妙”是什么?是想象。而想象总是包含了猜测的成分。以至有人老是把文字破译当作猜谜射覆、智力游戏,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凭想象力“跑马”的自由领域。
1955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安徽寿县发掘过一座蔡侯墓,在当时很轰动。这个蔡侯是谁?本来出土铭文是写明了的:他的名字叫。但这个名字很怪,谁也认不出来。没办法,大家只好猜。怎么猜呢?我们都知道,蔡国迁都寿县,只有五代就灭亡了。也就是说,大家只能在这五个蔡侯或略早的蔡侯中选择。而当时也真的就有六七种意见。实际上是把所有可能都占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303页。。这种情况在研究早期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很常见,说得好听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得不好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于想象力的充分运用,各种假说的并存也许是一种补偿。中国话叫“平分秋色”。说实话,干我们这一行,有人希望的就是这种情况。“无头公案,死无对证”,对真正的侦探当然是不幸,但对侦探小说的作者反而是好事。因为他正好可以借此编各种“推理小说”,调动读者的想象。在这方面,我们碰到的情况与宏观阐释并没有两样。大家一样是“大处着眼,假设先行”。但问题是你怎么证明你的想法呢?在有些人看来,证明并不是去发现事实,而只是为自己的假设铺设逻辑轨道,中国话叫“自圆其说”。他们觉得空白越多,自由度才越大。所以还专挑年代早、线索少的字来考。讲战国秦汉还小心一点,越往前胆子越大,甚至以为文字破译要比其他领域更多想象余地《金文编》王国维序强调“阙疑”,但郭沫若不以为然,讥为“懒汉思想”。其实这个词可做正反两面理解。从肯定的方面讲,它是一种必要的慎重。西方法律讲究“无罪推定”,即在正式判决前,先要假定被告无罪。中国古代治学讲究“阙疑”,也是害怕冤枉古人。考证古文字虽非“人命关天”,但也不能乱造“冤假错案”。。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看情况正好相反。因为文字破译要回答的是简单事实,就像拿破仑死于哪一年,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争论的。它的答案只有一个,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比起各种复杂的阐释系统,反而最少选择余地。虽然在线索不明的情况下,想象总是不可避免,但这和文字破译的答案是两回事。文字破译的答案也许我们不知道,就像“历史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但这正像你的童年经历,即使回首如梦,什么也记不清,但不能随意编造。破译文字胡猜乱蒙,最大克星是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中国有句老话,叫“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地下发现一出来,很多猜测都要扫地出门,这是件很不客气的事情。比如上面这桩公案,真相大白是在20多年以后。真相一出来,众说并存的局面就被打破,剩下的其实还是一个答案。
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申”字。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一)70年代,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编钟,铭文提到各国钟律。这些国名中恰恰就有这个字。当时裘锡圭先生参加整理,马上就想到以前碰到过这个字。虽然这个字的出现,在辞例上也是孤立的,但是它却把认识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因为现在情况与以前已有很大不同,以前大家的猜测哪个是对的,现在必须符合新的条件,即它必须是东周时期常见的一个国名,而且这个国名又可排除在铭文所见的其他国名之外。在这种线索的启发下,裘先生猜测,它很可能是申国的申字。也就是说,上述各说,只有陈梦家先生的蔡昭侯(名“申”)说是对的。
(二)这个猜测是不是对,还要拿出结构分析的理由。过去在西周金文中有个字。这个字常见于册命金文。古代实行世官制,父死子继,在手续上要经过重新任命。遇到这种场合,铭文常常会说:从前先王曾命你的祖考如何如何,现在我又“乃命”如何如何。前人曾把这个字释为,以为是形旁,与糸相通;是声旁,与重同从东得声,辞义是继续的意思。但裘先生在提出上述猜测时,产生了另一个思路。他认为上述难字与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并非从东得声,而是从田得声。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古代的陈齐,汉代人叫田齐,陈与田古音相近;第二,陈字虽然从东,但并非从东得声,其古文写法是作,说明与申读音相近;第三,古人讲重复旧的命令恰恰是用“申”字(即“三令五申”之“申”)。这也就是说,“申”字的古体是从田声(《金文编》2204的“”字与2113的“”字是同一个字),严格讲是假“绅”字为之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徐青松发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三)过去,裘先生提出他的新解,很多人不相信。但古代的申国在河南南阳。80年代,南阳地区先后出土了申公彭宇瑚和南申伯太宰的铜器。铭文“申公”是楚灭申之后所设的县公,见于《左传》;“南申”则是周宣王所迁封,见于《诗•大雅•嵩高》。这些铜器铭文中的“申”字就是写成“”。它们证明,裘先生的说法是可以视为定论的。
这个例子在文字破译中很典型。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成功的破译。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破译,无论多么巧妙,总还要靠一定的线索。说得不好听,就是还要靠一点“老天保佑”。因为没有线索,你的想象也就无所附丽;没有线索,你的猜测也就无法证实。这种线索有时也许并不能直接逼近答案,但它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使你不至于面对无数可能,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样的价值也是很大的。
二、几点反“常识”的经验之谈
在实际破译过程中,经验常常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想选几个实际的例子,对破译方法做一点描述。
(一)越是看着相像,可能反而越不是这个字。
辨识古文字,入手处总是形体线索。一般人认为,破译文字,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它与哪个字相像。但这个方法失败的可能也很大。过去中国唱戏的有个对联,上联是“是我非我,我是我,我又非我”,下联是“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是讲演技的乱真。古人留下文字,虽然并未使出什么“障眼法”,故意要难为我们,但这里面疑似之间,扑朔迷离的情况确实很多。一个字和另一个字也许只有一点点不同,你可能会忽略它,或宁愿迁就自己的想象,不肯去承认它,但这一点点不同往往就是至关重要的。你越是看着它像这个字,它往往越不是这个字。正合得上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
(1)(廴、引)〔毛公鼎〕(弘)〔史墙盘“宖”字所从〕于豪亮《说“引”字》,《考古》1977年第5期。李零《为〈说“引”字〉释疑》,《古文字论集》(一),《考古与文物丛刊》第2号。
(2)(豊)〔朱家集楚器〕(铸)〔朱家集楚器〕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19辑。
(3)(愆)〔朱家集楚器〕(盥)〔蔡侯申缶〕李零《释“利津”和战国人名中的与字》,《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这三组例子,左边一字过去都被误释为右边一字,新版《金文编》甚至把(2)(3)的左右两字按误释同时收入。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这种形近误释之所以值得警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古文字中凡与小篆比较变化不大的字,前人多已认出;二是古文字的讹变往往变化莫测,特别是战国文字,有些讹变简直莫名其妙。例如曲作,与匕难以分辨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8辑。;冶作,与侃极为相似。现在北京有些商店把“罐头”写成“缶头”,你要单把“缶”字挑出来,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它是读为“罐”。战国文字怪起来,有时就很接近这种程度。
对于防止形近误释,反证很重要。一个字的破译有时不仅要证明它是什么字,还要证明它不是什么字。像上面的右边一字就都是反证。
(二)线索不够,最忌“空白想象”。
对文字破译,想象很重要。但想象的掌握很难,常常会“溢出”事实的边缘。对有些事,你铆足了劲去干,就一定会有好处,但想象可不一定。我在前面讲过,文字破译的答案很窄,角度一偏,就会落空。而人脑有个规律,它在空白的地方一定要想象,而且一旦想开来,就很难停止,会弥漫扩散,“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原来没这个想法还好,有了就很难去掉。它会引导你,让你越想越像,一条道走到黑,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例如我们都知道,文字破译经常使用缺文。古人语短,只要缺文有四、五个字,你就很难补出来。过去楚帛书用普通摄影机拍照片,有不少字看不清,各家进行补释,花了很多心血,但我们拿红外线照片一核对,却几乎都是错的。它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空白想象”命中率太低。
以前,李学勤先生常说,古文字难认,难起来就是你做梦也梦不见。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确实是经验之谈。现在搞古文字,有些人好做“绝膑之举”(北京话叫“撅着自己”),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妨碍思维的正确导向。文字破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认识古文字,说实话,还是因为它有一条始终未断的线索。20世纪初,甲骨文一发现,很快人们就能把它认出,原因还是因为前面有宋人对金文的研究做基础,而宋人对金文的研究又是托福于汉代的小学和古文之学。线索一直可以通到先秦。
中国的古文字,纵有几千年,横有六七门,线索的搜寻范围很大。有些很早的字是靠很晚的字认出来。像商代甲骨文中的“引”字,西周金文中的“叕”字(),线索是在秦汉简帛文书中。现在的古文字学,从线索的角度讲,是个逆溯比较体系。前人识字,在没有大量的出土材料发现之前,主要是靠两条线索,一条是籀文—小篆—隶书系统的线索(来源于秦汉小学的识字课本),一条是六国古文系统的线索(来源于汉代古文经本的解读)。前者是西周文字的近亲(周秦地土相袭,文化相承),沿袭性较强,不像后者的变易度那么大。大家比较重视的主要是前一条线索,而比较忽略后一条线索。所以直到今天,大家仍有一个印象,就是西周文字比起战国文字反而好认。这里好认不好认,关键还在于线索。
(三)结构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
结构分析是破译文字的重要方法。老一代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是聪明绝顶。他喜欢讲,你们认字都是“手工操作”,效率不高,我是“机械化生产”,一认就是一大批。他说的“一认一大批”,当然与他博闻强记、左右逢源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说他有一个法宝,就是偏旁分析。偏旁分析,从来源讲,还是出自许慎“六书”。但现在的古文字学家见到的材料要远远超过许慎,对各时期的文字特点有不少新认识,又受到现代语言学的影响,所以有各种新的偏旁系联方法(如唐兰、岛邦男)和“三书”说(如唐兰、陈梦家)的提出。这一方法当然很重要,可是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往往要以一定的解读线索为前提,并且要由一定的解读线索来检验,特别是离不开文字材料的辞例和语境(context)。
现在在中国,研究一般文字学的和研究铭刻学的,中间分野越来越大。搞铭刻学的,识字都不是孤立的,要附属于解读,认字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去认。而搞一般文字学的不是这样,往往一上手就是各种文字编,甚至根本不管古文字,只在许学的范围里兜圈子。我记得唐先生有一次讲过,他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是被“章(太炎)、黄(侃)之学”革出教门。现在在中国,搞《说文》、《广韵》的人多集中在中文系,而搞甲骨、金文的则与考古、历史关系更深,的确是两个路子。但前者虽然推崇许慎,许慎《说文》的背景却是汉代的古文之学。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西汉小学本来是不讲古文的,学的都是秦系统的识字课本。东汉以来小学开始讲古文,这是来源于古文经本的解读。《说文》与当时研究古今字(今古文对比)的书有关,而“古今字”的研究正是从古文经本的解读总结出来的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第3卷第1期。。
在解读过程中,字体的比较和辞例的研究往往要先于结构分析。这点古代和今天是一样的。特别是辞例,对破译的导向影响尤大。古文字中有许多字,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怎样分析它,或者说不明白它与后来的字体在结构上有什么联系,但它是个什么字仍然可以确定。这里关键就是辞例把它卡住了。例如西周金文中的(就)字,过去有人把它读为京,后来陕西长安县出土了史惠鼎,上面也有这个字,辞例与《诗•周颂•敬之》中的“日就月将”相同,才知道它是个“就”字陈颖《长安县出土的两件青铜器》,《文博》1985年第3期。李学勤《史惠鼎与史学渊源》,《文博》1985年第6期。。还有古文字中的贵字(馈字从之),它的写法是,过去一直不认识,后来我从鸟书带钩中发现“不择贵贱”这样的辞例,“贵”字正是这样写,才明白这是“贵”字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但这两个字到底应当怎样分析,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四)越是曲折的解释往往越不可信。
在老一代的古文字学家当中,于省吾先生也是一位识字能手。他有个讲法,说古文字的答案近在眼前,只不过中间隔着张纸,一捅就破。我在考释文字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体会,即古文字的答案一经说破,都相当简单,根本用不着什么复杂的解释。相反,如果你的解释越是曲曲折折,假设套着假设,那我们就有一个直觉,这恐怕是靠不住的。
现在搞破译文字搞弯弯绕,最常见的是滥用通假。通假对于破译文字当然很重要。比如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不经破读,就很难理解。但这一方法的“自由度”也是有限的。第一,它要受古音学规律的限制,古代通假,读音相近(韵纽均相近)是一层,比较宽;声旁相同(或同从某字得声)是另一层,比较窄。窄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第二,它还要受书写习惯的限制,有时并不是说读音相近就一定可以落实(音近只是一种可能),各时期的文字有各时期的特点,需要通过较多的实例去总结。有人不但不管第二层,就连第一层的规定也不遵守,仅凭想当然的“一声之转”曲成其说,这除了满足自己的想象,一点用也没有。
古文字的通假规律应该通过较多的实例去总结。过去,朱骏声按“右文说”分韵分声旁排列文字,探讨通假与词义的关系,主要是靠古书中的实例。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是如此。这种工作当然很有益,但不足是没有吸收古文字中的大量实例。古文字不仅可以提供新材料,还可纠正我们对通假规律认识的许多不足。
三、文字破译的虚实:“漫无是非”与“铁板钉钉”
现在,置身于古文字学界,人们常常会被一种“漫无是非”的气氛所包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漫无是非”呢?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在古文字的认识上,“今之所知”与“古之所存”差距太大,有些线索可能永远看不见,有些线索则藏头露尾,让你看不清。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划一道界线,但实际上却很难掌握。例如现在的很多文字编,正编中的字其实并不可识,而附录中的字反而早就被人认出。
(二)在古文字的研究上,研究者的意见过于分歧。“小萝卜头”不用说,即使是大家,意见也难得统一。比如孙海波先生编了《甲骨文编》,容庚先生编了《金文编》,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工具书,但让唐兰先生说起来,认对的还不到一半。唐先生水准高,看不上眼的东西自然很多。但他的意见是不是大家都能接受呢?也并不是,文字破译是冒险事业,犯错误的机会到处都是。在这个领域里没有“常胜将军”,即使大家也会犯错误,而且错起来照样是一塌糊涂(不可能说是什么“高明”的错误)。
(三)中国的古文字学界有手工业习气,几乎人人都搞“闭门造车”,信息不灵,缺乏及时的评价,前人做了什么,后人做了什么,别人做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很多“已识”和“未识”常常是一笔糊涂账。古文字学界的人都爱争“发明权”,但又没有“发明记录”,常常搞“重复制造”,不但今人与古人“撞车”,而且今人与今人也“撞车”。比如西周金文中“履田”(踏勘田界)的“履”字,过去见于大簋、散氏盘,吴式芬、章太炎已经认出,大家不注意。等到五祀卫鼎、九祀卫鼎出来,唐兰先生重新认出这个字,大家还以为是新发明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卷三之二;章太炎《论散氏盘铭二札》,《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第3期。。现在这个字出现已经很多,除上述各器,还有倗生簋和师永盂,也都有人写过文章。可是新版《金文编》却把散氏盘的“履”字收在“眉”字下,大簋、师永盂和倗生簋的“履”字列为不识字,根本没有“履”字这一条。
但是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我还是认为文字破译并非“漫无是非”。它里面不但有许多东西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落实,而且还包括了一些铁板钉钉的东西。因为第一,文字破译是否成功,毕竟还有不少标准可以判断,如字体线索的依据、辞例线索的依据、结构线索的依据。只要这些条件都具备,像上面讲的“申”字,就可以叫“铁板钉钉”。第二,判断文字破译是否成功,最好的办法是“读”,即把破译结果回输到有关材料中,看是否读得通,经得起重复和反证。现在的古文字研究,要想达到像“读”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那样一个水平还很不容易,但其各个分支都有一定的“可读性”,这里面肯定已包含了许多“铁板钉钉”的东西,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加以认真总结罢了。
对文字破译的结果加以落实,现存的各种工具书还做得很不够。过去,容庚先生曾对宋代的金文研究做过总结,但对宋人识字的得失却未能详加论列。宋代以下,情况就更别提了。近代的古文字学(罗王之学),其实是个年轻学科,年头只有80年,传人只有四代。唐兰、容庚、郭沫若、董作宾、于省吾可以算是第一代,陈梦家、胡厚宣、张政烺可以算是第二代,李学勤、裘锡圭是第三代,下面的一批人是第四代。但就是这么一些人的研究,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学科内部没有一个自我估计。
所以,我很希望有人能写出一部古文字学的“发明史”出来。
四、不是结论的结论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文字破译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我想,这个印象在许多方面都与一般的宏观阐释息息相通,如逆溯比较、假设先行,还有证伪方式,等等。如果说它们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我看倒是在这样一点,即它比一般宏观阐释往往需要更多的想象,但也受到更多的限制。
文字破译是“小道”,宏观阐释是“大道”。“小道”固应兼容于“大道”,但“大道”是不是也可以从“小道”受到一点启发呢?
1989年11月2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
原载《学人》第4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453—464页。
补记:现在看来,我对“猜测”和“犯错误”在破译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点估计不足。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