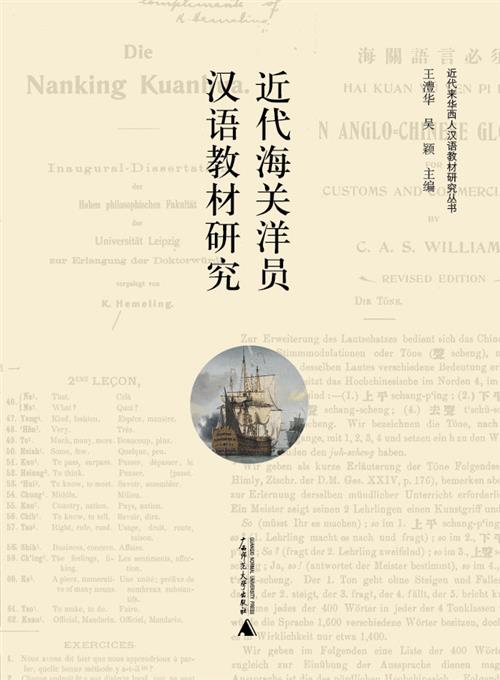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6-05-01
定 价:48.00
作 者:王澧华 吴颖 主编
责 编:刘艳 高东辉 樊中元
读者对象: 中文专业本科生、研究生
开本: 16
字数: 295 (千字)
页数: 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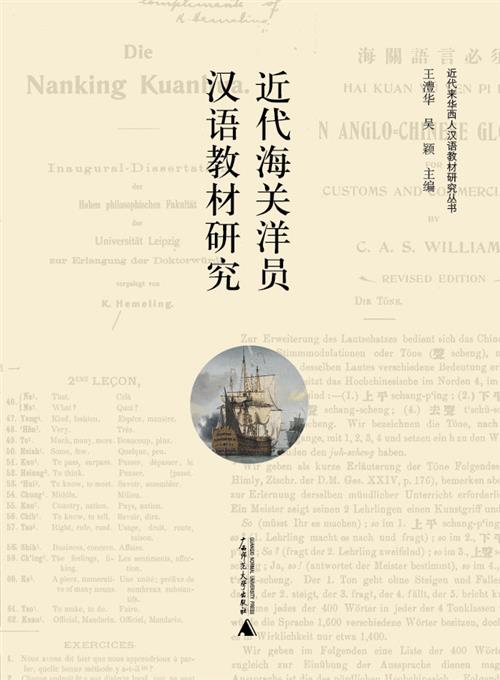
《近代海关洋员汉语教材研究》选取赫德等12名洋员汉学家汉语教材,从第二语言教学、西人自编汉语教材的视角,做专人专书研究。书稿主要依据《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英文版、《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以及目前整理得见的两册《赫德日记》等十多部历史文献,梳理了晚清海关汉语学习的起因与过程,评述其培训成效与经验。
王澧华(1961— ),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吴颖(1966—),女,博士,女,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业负责人。
夏德《新关文件录》及其《文件小字典》研究…………………………董丽娟 (16)
穆麟德《官话学习指南》研究…………………………………………何玉洁 王澧华(30)
赫美玲《南京官话》《英汉国语词典》研究…………………………韩 笑 蔡琦玲(85)
帛黎《铅椠汇存》及其《圣谕广训》法译本研究…………………………付 碧(110)
穆意索《公余琐谈》研究……………………………………………………傅永莹(133)
孟国美《温州方言入门》研究……………………………………………………蔡 瑱(144)
文林士《海关汉语必须》研究………………………………………………………韩 笑(182)
费妥玛《学庸两论集锦》…………………………………………………………何玉洁 (202)
费克森《邮政成语辑要》研究……………………………………………………何玉洁 (213)
布列地《华英万字典》研究……………………………………………………傅永莹 (224)
巴立地《邮用语句用语》研究………………………………………………傅永莹 王澧华(239)
总税务司署汉文秘书科汉语学习股《汉语学习》研究…………………………张 欣(251)
后记
赫德的汉语推广与晚清洋员的汉语学习(代序)
王澧华
19世纪在华外国人的汉语学习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冷落、最近复苏的课题。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其主妇、子女,是当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主要群体。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对各种学习群体逐一归纳分析,探讨其学习缘由、学习方式与过程,分析其学习成果,评价其经验得失。
随着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签订与实施,其所谓“条约口岸”即沿海及内地通商城市逐步增加,更由于清帝国一再遭受内乱与外侵,国家主权陷入重大困境,晚清海关基本被外籍税务司掌控,各级洋员遍布全国66个海关。而英国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大力推行的汉语学习制度,使得洋员的汉语学习与培训,历时长,人数多,力度大,成为当时来华西人中最大的汉语学习群体。因此,它更值得重视与发掘。
为此,本文依据《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英文版、《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以及目前整理得见的两册《赫德日记》等历史文献,梳理晚清海关汉语学习的起因与过程,评述其培训成效与经验。
一、赫德掌管晚清海关,严令洋员学习汉语
(一)外籍总税务司掌控晚清海关,全权招募洋员来华就职
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列为五口通商城市,第二年,参与攻占并且驻守上海的英军炮艇舰长巴福尔(G.Balfour),被战争期间英国全权代表、战后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H. Pottinger)任命为首任上海领事(副商务监督衔),11月17日,巴富尔行文通告,宣布上海对外开埠通商,后在县城之外洋泾浜租地开馆。随着外洋商船先后入境装卸,江海关的派出机构“西洋商船盘验所”也随之设立,后来进驻外滩,号称“洋关”,就近监管外国商船的出入境申报与关税缴纳。
1853年3月,洪秀全太平军攻占南京,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下大小官员遇难无数,东南军政濒临瘫痪,各地秘密帮会纷纷暴动。9月7日,天地会分支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击杀县令;第二天,外滩洋关遭到暴力劫掠和焚毁,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也被拘押,次日经美国领事交涉逃入租界。随后10个月,吴淞口外,黄浦江畔,各国商船陆续进出,起初是英美驻沪领事代收外商将来缴税的书面承诺,继而是吴健彰设立的流动征税船遭外商与领事拒绝,最后是美国政府否决领事代征权限,美领事宣布上海为自由港,英商、英领事继而效仿,上海海关税收完全失控。
在历经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1954年6月29日,在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的操持下,美、法领事同意各派一人,临时参与上海海关税务监督,而一直在租界避难的吴健彰,除了签订协议也无能为力,连这个协议的对外宣布,都是三国领事以联名通函的方式登载在当年7月8日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上。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围绕领事、道台对外籍税务监督选任的互相制约:海关必须任用洋员,领事推荐人选,交由道台任命,接受双重领导,负责对外通关征税,领取中方薪金。 7月12日,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F.Wade)、美国领事馆贾流意(L.Carr)和法国领事馆史亚实(A.Smith),面向三国领事宣誓就职,组成一个临时的关税管理委员会。而此前一天,清廷已经下旨将吴健彰罢官治罪,所以,这个外籍关税委员会也就基本独立行使职权了。1855年5月,威妥玛辞职,副领事衔的英国译员李泰国(H.N.Lay)接替威妥玛,美、法两国,也分别派出飞佘(N.W.Fish)和伊担(B.Edan)接替前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方再败,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10条,议定通商各口“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各口划一办理”。1859年5月,前任上海道台、现任江苏布政使兼署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薛焕,解聘飞佘(默认)和伊担(抗议),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在领事馆的支持下,李泰国坚持自行招募各口岸外籍税务司,这就不但否决了吴健彰与三国领事的最初协定,即洋员“应由道台慎选遴委”(“the persons of foreigners,carefully selected and appointed by the Taotai”),随着该职位在1861年1月被清廷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文认可,洋员招募的权利便完全被外籍总税务司把持。
1861年4月,李泰国回国休假,安排上海海关英籍税务司费士来(G.H.Fitz—Roy)与广州海关英籍副税务司赫德联合代行其职。1863年11月,李泰国因阿斯本舰队事件解职,上海海关税务司赫德正式接任总税务司。随即,赫德协助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卜鲁斯 (F.Bruce)起草《通商各口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1864年6月21日,由总理衙门以《海关衙门章程》颁发各地。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欧美各大国的应聘者便络绎不绝来到中国,成为海关洋员。历年洋员总数,保守估计,也当在2000人以上。
(二)赫德严令洋员学习汉语,坚持不懈
总理衙门下发《海关衙门章程》的同一天,据赫德日记,他在凌晨四点亲笔起草“致各税务司有关其职责的通令初稿”,“指出他们应遵循的原则等”,这就是随即颁布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第8号》,“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应遵循之方针与应履行之职责之思考及诸专项规定”,第八条是:“为提高海关效率,诸税务司应以身作则……应关心汉文学习,能学之人都学汉文。汉文并不枯燥乏味,一旦贯通汉文,日后将于个人有益,于海关有用。”此后近半个世纪,赫德在一系列通令中,一次次地重复和强调了这一基本方针:
1866年2月20日,赫德在担任总税务司后第一次返回英国之前,他特别下达当年第4号《通令》,要求各地税务司须事先通知所有洋员,总税务司将在数月后巡视各口岸,届时“将亲自检验各员对海关业务与条约之相关知识、汉文写作与口语以及其他中国事务之熟悉程度”。因为“此类知识内容,乃每一在中国海关中取得晋升者所必须具备者”。
1869年11月1日,针对部分洋员对汉语学习的抵触情绪,他一连颁发第25号、第26号《通令》,一再强调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先是反复论证“余推行讲汉语之理由”:第一,“任何政府部门之雇员均应讲雇佣国语言”,这是国际通例;第二,“中国海关监督时有来信,要求勿调派不懂汉语之税务司至其所在口岸”,这是现实需求;第三,如果“雇佣不能操汉语之税务司,令译员在困境中左右局势,显属反常”,因此,“此类意见绝不可取,即使暂时有说服力,本总税务司也绝不支持”。最后,他还用带有感情的笔调这样写道,我“寄予厚望”的,是“有如此众多有教养有才能之在华雇员,发愤学习汉语”。接着,他又用“不学汉文不得担任税务司职务、只留任原职、不如学汉文者之事实”,“促使关员努力学习汉文”。这是因为,“缺乏学习汉文之能力者”,“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落后于在中国海关中得到升职者”。与此同时,赫德也规劝这些落后者“无须过于灰心”,因为“在海关内尚有时间学习汉文以弥补不足”。刚性制度之外,再三温语劝导,赫德可谓用心良苦。
就在下达这两份《通令》的同一天,赫德还颁布了《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其中关于“税务司职位与副税务司职位之任命”,明确规定,“总税务司将按下列各点遴选”,在七个任职条件中,第四点为“汉文知识”,第七点为“凡各类考试不及格,或其汉文知识不足,在处理特殊事务时需要译员帮助者,则不能任命为税务司”。力度如此之大,堪称罕见。
赫德本人于1854年以使馆翻译生身份来华,进入海关之前,他曾经在领事馆担任过5年的专职翻译。他深知汉语学习的困难,需要自身的毅力和必要的外力督促,1884年3月21日的总税务司《通令》规定:“各关税务司本人须对汉文学习产生兴趣,并以不时测试确保其下属人员之汉文学习不致中断,以时而劝导,促使学员以更多时间致力于汉文学习。所有人员尤应重视汉文作文之提高。尽管‘汉话’已达良好水平,但海关中极少人员之‘公文’造诣能胜任襄办汉文文案副税务司职务、胜任汉文文案税务司职务者,更属凤毛麟角。望所有人员为之努力。”
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关通令数十次的明文规定、严格督促,运用行政的权威、制度的力量,结合职位的聘用、职级的升降,在近代中国,如此推广外籍人员的汉语学习,这样的力度,不但为欧美各国基督教的诸多差会所不及,而且在各国外交部(甚至包括亚洲的日本)及其驻华领事馆中,也是很少见到的了。
二、晚清海关洋员汉语培训的历史考察
赫德在宁波使馆做翻译生时,一边工作,一边自费聘请中国文人教读汉语。教材、教法与课时皆不尽人意。当时他就有过集中授课的想法,他甚至还给当时的公使馆任职的威妥玛写信说:“我想,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跟着好的老师学习,并得到精通这门语言的长者的建议与指点,会比一个单独的又有别的事打扰的个人,取得快得多的进步,并且获得更有用的汉语知识,因为这个人从来不知道可称为是他自己的时间有多少,每天的奇思怪想,时而飘向这里,时而飘向那里,从来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是否花在值得努力的追求上,或者是否在按恰当的方式工作。” 此信写作年代不详,如果威妥玛此时已如费正清(J. K. Fairbank)等人所称之“Chinese Secretary”(汉文正使),那么他可能已经跟随使馆进驻北京,时间是1861年以后。稍后,由他参与主持的使馆翻译生的汉语招考培训付诸实施,即大学生候选应考、来华集中见习、带薪培训,结业后分配各地领馆。 1865年,赫德将海关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往北京,而他的海关汉语培训的组织形式,也与馆翻译生的学习模式大体相似。
以下是据《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英文版与《赫德日记》勾勒出来的海关洋员的招考、培训与分配的基本轮廓:
(一) 学员选择
1.在职洋员具有潜力者
这是赫德汉语培训的早期形式,它早于成批次招考洋员进京学习。从1864年起,赫德的日记中就不断出现“学生”、“我的学生”等词句,而从前后记载推定,他们就是赫德将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之初,从海关各口岸选调的新进洋员。在此,可以略举二例:
葛德立(W.Cartwright),英国人,1862年随阿斯本舰队来华,1863年1月进入海关;1864年开始在北京学习汉语,为期一年。
康发达(F.Klenwachter),德国人,1863年2月进关,1864年7月从芝罘(烟台)任所赶到北京,开始汉语学习,为期一年。
2.资深洋员脱产进修
这个判断来自海关设在英国伦敦的“无任所秘书”(通称“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D.Campbell)1903年9月9日写给赫德的一封信:“您会记得,在1867——8年(金登干原信如此,中文版照译)的冬天,正当吉罗福、休士、汉南诸税务司在北京学习中文。”吉罗福(Geo.B.Glover)是美国人,1859年8进关,10月任广州代理税务司,此时,当年6月进关的赫德是他的副税务司;1860年10月,吉罗福升任税务司,赫德仍旧是他的副手;休士(Geo.Hughes)是英国人,1859年11月进关,1861年5月升任宁波税务司;英国人汉南(C.Hannen),与吉罗福同时进关,1863年3月已是芝罘(烟台)海关首任税务司。
3.新聘洋员之品学兼优者
鉴于人手与经费的原因,能够参加岗前汉语学习的人,只能是其中的少数人。在此,略举数例:
1876年,赫德与金登干在英国物色到工程师魏斯勒(G.E.Wellesley),此人不仅有上流社会的出身背景,而且在英国工程界有良好的声誉,为此,赫德特意致信金登干:“魏斯勒有无语言才能?假如他有,我可以给他一年的时间,在北京攻读中文。”(1876.3.37)
英国财政部职员戴乐尔(F.E.Taylor)年轻有为,曾经在该部工作并且担任部长私人秘书的金登干特意招聘戴乐尔为办事处“编外办事员”(1880.7.2,致赫德信),赫德闻讯,立即要把他正式招聘来华。金登干则一再挽留,而赫德也是再三写信催促:“至于戴乐尔,我调他来中国的本意,是为了让他学中文,以便使他逐步获得担任税务司的机会。”(1879.12.21)“戴乐尔已到达(北京),现正在学中文。”(1881.5.22)一年后,戴乐尔升任上海海关二等帮办,以后历任牛庄(营口)、九龙、宁波、亚东(西藏日喀则)等地税务司。1900年夏,义和团“扶清灭洋”,海关与驻京使馆遭受围困,戴乐尔临危受命,在上海以总署造册税务司代理赫德总税务司之职。
安格联(F.A.Aglen),赫德大学同学之子,据金登干信中说,“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还不到19岁,刚刚离开莫尔伯勒学院,他在那里名列前茅”(1888.8.24)。1888年12月,安格联进入海关,在北京完成两年的汉语学习。1892年,他便得以升任厦门、广州三等帮办后班,1894年调京,升任总署代理汉文案副税务司,职位随即显赫,随后数年,直线上升,直至总税务司。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新职员先到各口岸见习数月,然后进京学习,如1883年进关的英国人夏立士(A.H.Harris),第二年才调至北京学习,1892年,他还获得了牛津大学戴维斯汉语奖学金;1890年录用8名,仅英国学生克乐司(A.W.Cross)一人直接到京,同样来自英国的桑德生(H.S.Saunderson)等人,则属于前一种。
(二)学习情况
1.地点
北京:选择以北京为主要学习地点,当然是因为它的种种便利条件,1865年,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支持下,赫德将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往北京。北京不仅有使馆汉语翻译生的汉语学习群体,而且还有优越的官话语音环境和相对充裕的学习时间,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赫德对学习态度的就近督促与学习成绩的随机检验。
现在可以确定,总税务司署之“南院”(赫德致金登干信称之为“学生居住区”,1874.1.28),就是海关汉语学生的住地及教学场所,在赫德的往来通信中,“南院”几乎总是与“学生”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我准备把他(笔者:即克赅儒,A.Klark)和璧斯玛(C.Bismarck)、别里尼(D.Pegorini)、沙鄂文(E.von.Zach)、伟傅德(W.H.C.Weippert)派到南院去学中文。”(1897.10.31,致金登干)上述各人,即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英国的新入关洋员。
上海:1874年7月,美国人马士(H.B.Morse)与他的哈佛同学客纳格(C.C.Klarck)、司必立(W.F.Spinney)一同进入海关:客纳格分至汉口、司必立前往厦门,马士则在上海学习汉语。1879年,赫德已经说“他的中文非常好”,特意从自己的办公室派往伦敦办事处。
南京:1898年6月,两名奥地利人被录取为四等帮办后班,其中马德那(F.Marterna)在北京学习,而郝马良(M.F.Hey)则在南京学习汉语。此外,德国人赫美玲(K.E.C.Hemeling)、荷兰人费克森(J.W.H.Ferguson)以及剑桥大学硕士毕业的贺智兰(R.E.C.Hedgeland),都是在南京学习汉语。
早期传教士与外交官的汉语学习,一般都在广东与福建,接触的多为南方方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欧美使馆纷纷进京,南京官话进而北京官话成为学习首选。北京、上海与南京,显然比广州、福州与宁波等地具有更好的语音环境。
2.师资
目前看到的材料,海关汉语师资,大体是中国文人与资深洋员。
检《赫德日记》,1864年8月3日有这样的记载:“我的文案今日为康发达和德善带来几个老师:他自己的儿子……(另)一个人名其林,是举人……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这个文案和他的儿子,应该就是后来随赫德出访英国的满族文人斌椿与广英。满人入关之后,八旗子弟自小学习汉语,其中一批人就成为京畿地区最早的一批汉语国际教育师资。这则日记提到的第二位教师,更是一位中举的高级文人。另外,美国资深税务司杜德维(E.B.Drew)在介绍赴哈佛任教的中文教师戈鲲化时,也明确提到:“我毫不怀疑戈先生担任教师的资格,我曾跟随他学过一段时间中文。” 由此可见,北京、上海等地洋员汉语学习的师资主要是中国文人。
当然,有时出于各种原因,洋员也只有或者更乐意向欧美同行学习汉语。如金登干致赫德信中说过,“戴乐尔正在跟马士学中文,每周一个晚上在自己家,一个晚上在马士的住处”(1880.3.5)。另据金登干向赫德抄录其堂弟甘博家书:“这里的负责人夏德现在偶尔给我一些指示,这是对我的莫大帮助。哦,来到北方已十二个月,在这里学习起来实在困难,连一位像样的老师也没有,没有机会提高外语能力。”(1879.11.7)夏德(F.Harth)是德国博士,1870年进关,曾任亚洲文会主席,1902年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首任汉语教授。1888年,他还出版了《新关文件录》、《文件字句入门》和《文件小字典》。这些都是洋员学习汉语的必备工具书。
3.教材
《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规定:“由三等提升到二等帮办,必须通过米德(笔者:即密迪乐T.T.Meadows)之《随笔》、威妥玛之《会话丛书》(笔者:当为《语言自迩集》之“问答章”)及同类题目考试……同样,由二等提升至一等帮办,必须通过威廉士(笔者:即卫三畏S.W.Willimas)之《中国》、威妥玛之《公文丛书》(笔者:即《文件自迩集》)及同类题目考试。”
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文件自迩集》于1867年在上海出版,1886年又推出修订本,由设在上海的海关造册处免费印刷,算是对威妥玛这位过渡时期“外籍关税委员会”第一任掌班的特别照顾。而美国公使馆参赞卫三畏的《中国总论》、英国领事官密迪乐的《随笔》,都有论述汉语学习的专章。
4.年限
1864年6月25日,赫德致信美国公使浦安臣(B.Anson)说:“如果你能为我在美国物色三名有教养的青年,年龄在18岁以上,22岁以下,受过大学教育,我将极为感谢……他们最初两年将住在北京学习中文,那里将提供住房,一年薪俸按400镑付给。第二年期满,每个薪俸将增至600镑。” 次年10月,联邦大学的廷得尔(E.Goe.Taintor)、耶鲁大学的吴德禄(F.E.Woodruff)、哈佛大学的杜德维进入中国海关。他们学满了两年后,第三年都晋升到了副税务司。
使馆翻译生一般是学满两年,从一代代传教士积累的经验,也是安排两年的汉语自修期.但海关由于经费限制,能够学满两年的极少,如果人手紧缺(如洋员轮休),学员还会被临时抽调。如赫德致金登干信中就说:“各处都要人手,我只好从北京派出了九个人”(1887.3.5),其中7个是学员。翻译出版《论语》《孟子》的英国人赖发洛(L.A.Layll),在北京就只学习了6个月。
至于具体的学习安排,大体是半天学习汉语,半天见习工作。如赫德《致金登干》:“杰米本星期将抵达这里。我将把他安顿在我的住宅旁边的新院子里,并给他上午的时间学习中文,下午在办公室工作。”(1892.4.10)杰米是金登干的长子,来华后取名金真备(J.B.Campbell)。金真备也确实像他父亲期望的那样,一到北京就“开始热切地学习中文”(金登干《致赫德》1892.6.24)。在来华后的第一次季度考试中,他获得399分(满分为600分,考官为葛德立)。可惜的是,三个月后,金真备因感染伤寒在北京去世。
5.考试与分配
目前已经问世的赫德日记截止于1866年,在此,仅以1865年日记记录的结业考试为例。本次考试满分为200,考生6名,据赫德7月7日语8月15日的两次记载,名次与分配结果如下:
第一名,葛德立,162分,“充任我的文案”,他的法国同学“德善(de E.Champs)对他的升擢十分高兴”。葛德立后任总理汉文案税务司,1885年,赫德一度出任英国驻华公使,葛德立还被提名为总税务司的候选人。
第二名,包腊(E.C.Bowra,),也是英国人,126分,分配到广州海关,任三等帮办,后任斌椿使团翻译,官至宁波税务司、广州税务司。
第三名,德国人康发达,99分,分配到汕头海关,三等帮办,赫德在日记中特意写到,“但是包腊和康发达以3dCC(即三等帮办)离开北京,感到非常失望”。康发达后来升任镇江、宁波、汕头、广州等地税务司。
第四名,法国人德善,94分,分配到芝罘海关,后任斌椿使团翻译,历任九江、淡水等地税务司。
第五名,哈密尔德,21分,日记中未见分配记录。
第六名,道蒂,9分(成绩揭晓当晚,他向赫德解释是失恋而“受到伤害”),随即被赫德解除海关任职。
这还只是海关初期的汉语考选情况,上述六人(哈密尔德除外),都有先在各地海关任职,中途抽调进京学习的明确记载。而据赫德与金登干的往来通信,中后期的洋员学习分配,绝大多数都是先学汉语再做分配,任职也都是从四等帮办做起,以后逐级晋升。但书面测试、择优分配的原则,则是一以贯之的。
三、汉语成为西方人“职业外语学习与考试”及其意义
(一)“赫德的汉语推广”之评价
1.力度大,目标明确
在赫德掌管的晚清海关,汉语学习直接关系到洋员的就业、晋职与加薪,这在总税务司通令中多次重申:“有关汉文学习及公事处理两事,各关税务司应令所有人员时刻毋忘其任命状中之条款(参阅其中第5节第5项及第6项),即凡不称职及考试不及格者将予以停止雇用。再不具备合格资格者当不继续雇用。”(《通令》273号,1884.3.21)“内班人员,凡不能用汉文汉语处理事务者,不发予酬劳金。无同等与足够之工作汉语知识者,不得提升为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一业已提升或以后将提升至副税务司或税务司而不再掌握足够工作汉语知识者,将予解除职务。于其第三年终未具备汉文口语、或第五年终未具备汉文书写条件者,将被免职。”(《通令》880号,1899.1.18)
具体事例:马士于1874年8月进入上海海关,学习汉语,以优异的汉语成绩升任天津关四等帮办前班,随后调北京总署,1879年,赫德将之作为三等帮办派往伦敦办事处。在英三年,马士竟然因为“在这里实际上无法保持已有的汉语水平”,“担心会把汉语忘记了”而“急于”得到赫德的“同意后回到中国”。为此,他甚至要放弃为期两年的长假(金登干《致赫德》,1882.2.24)。而他返回中国后,果然如愿升任上海海关二等帮办,以后历任北海、汉口、上海、广州等地税务司。
除了内班洋员(机关人员)必须学习汉语,赫德还在外班洋员(外勤人员)中推行汉语学习:“(外班)晋升:……其他条件相同时,最谙汉语者优先,如在上海或任一南方口岸,会操当地方言,如在长江或北方口岸,会操官话。”(《通令》14号,1867.9.19)“鼓励外班掌握相当汉语,并学习最常用之汉字。任何外班人员,如具备汉学家之高水准,能操某种方言或官话,并能训读汉文者,则每年可于其薪俸之外获得奖银150两,凡学习或能操方方言作日常会话者,每年可获得75两之奖银,由主管税务将此类人员姓名及所需奖银逐年上报。验货与总巡,尤须具有汉语知识,外班不具备该二职位所要求之汉语知识者,不得晋升其中任何一级。”(《通令》第880号,1899.1.18)1888年,金登干在伦敦招聘外班洋员,在写给赫德信中说,“‘开办’号管驾副罗斯(Ross)看来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他打算读中文。‘开办’号管轮副邓阿乐(G.G.Donald),据大家说是个很令人满意的人,他也打算读中文”(1888.4.27)。应聘之初即“打算读中文”,对招聘者来说,当然“令人满意”。
汉语学习的力度与目标如此明确,所以,《海关题名录》早期偶见的“Has not studied Chinese”,后来就很少出现了。
2.制度化,层级考试
1883年3月21日的第273号《通令》,主题是“为税务司如何测试并呈报属员汉文学习成绩及公事处理事”:
有关汉文学习,本总税务司特命各关税务司,利用下季度(4月至6月)中任何闲暇时间,对各关任职满三年之内班人员,测试其学习“韦氏会话”丛书(笔者:即威妥玛《语言自迩集》“问答章”)之成绩;对所有任职时间更长之关员,测试其学习“公文丛书”(笔者:即威妥玛《文件自迩集》)及一般局面语言之成绩,并于6月底按下列表格呈送报告:
下一生日年龄,姓名 入关日期 在上海以北工作年限 在北京学习时期 会话(受雇三年之关员) 公文(受雇三年以上之关员)
满分 总分 满分 总分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发 音 *口 译 英译汉(笔译) 汉译英(笔译) 汉字及四声知识 总分 汉译英(笔译) 英译汉(笔译) 指定题目之会话 汉字书写 特指读物例如[三国志][红楼梦] 总分
A. B……
B. D……
E. F……
*由主考人口述语句,应试者译成汉语。
根据这份表格以及文字说明,内班洋员在任职三年之后,需要通过汉语口语测试,其中“发音”、“口语”、“英译汉”、“汉译英”、“汉字及四声知识”一共5项测试内容,每项100分;超过三年以上的洋员,还要通过汉语书面知识测试,其“英译汉”、“汉译英”、“指定题目之会话”、“汉字书写”与“特指读物如《三国志》《红楼梦》”一共5项测试内容,每项也是100分。如此明细,如此具体,执行起来也就有章可依、有据可查了。
通过一次次的总税务司《通令》,赫德坚持将汉语考试制度化,不论何人,一视同仁。在1879年的帮办级例行考试中,金登干的堂弟甘博(S.Campbell) “没有做中文试卷”,为此,赫德特意向金登干通报,金登干则为甘博辩护,声称主考马吉(J.Mackey)“未必公平”,并将甘博回信抄送赫德,意在转圜:“现在我正循规蹈矩、勤奋刻苦地进行学习。我正学习《文牍丛书》(笔者:即威妥玛《文件自迩集》),并模仿办公室的某些公文程式试着写写。”(1879.11.7)在赫德与金登干的督促下,甘博不得不继续坚持汉语学习,甚至在他回国成婚之时,赫德仍“希望他会忙着学中文”(赫德《致金登干》,1883.10.24)。稍后,甘博由伦敦办事处一等帮办后班升任上海署理副税务司,1897年升任总署稽查账目税务司。
比利时人柏帖勒(H.de.Ponthiere)的事例尤有说服力。他于1898年12月进关,在上海任四等帮办后班,几年后循例回国休假,期间请求续假三个月,赫德对金登干的回电指示竟然是:“柏帖勒是个很好的办公室人员,但不注意学习中文。他要求续假,照准。但鉴于中文知识是工作所必不可少和提升所必需的,告诉他我不指望他回来。”(1904.3.15)柏帖勒得此消息,随即赶到金登干办事处恳求,如果能够回到中国,“他一定会努力学习中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身为总税务司,赫德人在北京,却了解并掌握着一个远在芜湖的低级职员的汉语学习态度及其水平,足见他对洋员汉语学习的关注之深;第二,续假与批复的电报往来在两天之间,赫德能够如此快速并且明确指出柏帖勒“不注意学习中文”,则表明通令规定的各地税务司对下属的年度考核汇报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第三,即使你“是个很好的办公室人员”,但“中文知识是工作所必不可少和提升所必需的”;第四,洋员若要保留职位,“他一定会努力学习中文”。
3.影响长远
赫德于1908年4月请假回国,1911年9月在英去世,10月,署理总税务司安格联转为实授。在他将近20年的任期内,安格联一直坚持赫德汉语推广的传统,并6次专门下发通令,就汉语学习方法、科目设置、推荐书目、考试安排以及考后奖罚等,做出了更为明晰的操作规定。安格联去任之后,梅乐和(F.W.Maze)时期、日伪时期,更有对口的海关汉语教材,如《海关汉语学习》(三册)的英语版与日语版。
(二)“海关汉语学习”之评价
1.集中培训,初具规模
1902年4月6日,赫德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说:“我们每年可以支配的空额不超过10个,但要分配给十几个国家。”这指的是海关每年的录用名额,而根据他们的往返信件,这些新聘洋员一般都要事先完成汉语培训。也就是说,近40年间,每年10名左右,带薪学习,为期1—2年,另有资深洋员脱产进修,海关洋员的汉语学习,与使馆汉语教学一同将汉语纳入西方人的职业外语学习行列。
2.学员来源广泛,语种覆盖面广
晚清海关洋员的汉语学习,其国别与语种可能确实多于“外交汉语”、“传教汉语”。据初步统计,洋员的国籍,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瑞典、丹麦、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挪威、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士、意大利、希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20多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并无驻华使馆,因此也就没有翻译生的汉语学习了。
3.功利性强,初见成效
按照海关惯例,洋员进入海关,应该在四等帮办后班任职数年,才可提升。俄国学员柯乐德(V.von Grot)1888年6月进关,在北京学习汉语,次年5月19日,赫德《致金登干》便称“柯乐德学习一年汉语,成绩卓越”,越级“升至四等帮办前班”。1894年,这名俄国人已跃升总署襄办汉文案、代理总理文案税务司。而且,考察总署汉文案税务司的履历,他们大多有参与汉语培训经历。由此可见,洋员的择优分配,择优晋级,可能是第一次让汉语成为西方人的职业外语考试。
此外,海关还为驻华使领馆提供了不少现成的外交人才,德国、法国、奥匈帝国等,就一再抽调洋员出任翻译或参赞、领事,编有《官话学习指南》《宁波方言音节表》的德国人穆麟德(P.G. von Möllendorff)就是显著例证。至于编著汉语课本,如夏德《文件字句入门》、英国人孟国美(P.H.Montgomery)《温州方言入门》、编译公文教材,如法国人穆意索(A.M.de Bernieres)《公余琐谈》、帛黎(T.Piry)《铅椠汇存》、编纂专业字典,如荷兰费克森《邮政成语辑要》、意大利巴立地(F.Poletti)《邮用语句辑要》、翻译名著,如英国邓罗(C.H. Brewitt—Taylor)英译《三国演义》、荷兰费妥玛(Ferguson, T.T.H.)编译《学庸两论集锦》),直至出任汉语教授(如夏德、法国雷乐石(L.Locher),荣获法国儒莲汉学奖(英国文林士 C.A.S.William),那就更是海关汉语学习的骄傲了。
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启西方人汉语学习的序幕,清初的中西礼仪之争关闭了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之门。19世纪英美新教传教士重新走上汉语学习之路,并借助鸦片战争后的一次次条约,伴随各国外交官成批次涌入中国,而晚清海关失守导致的外籍税务司制度,更是促使欧美各国青年考试竞争、来华就业,通过制度性学习与规模化培训,将汉语作为辅助性工作用语,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促使汉语进入西方人外语学习与考试行列的直接动力,则是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其长期推行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一个国家的语言要成为国际性语言,需要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种条件与机缘。汉语成为西方人的外语,是因为传教士、商人与侨居者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但他们对汉语的学习与掌握,似乎还处于自发状态。驻华使领馆翻译生的选拔招聘与培训录用,带来新的培训模式,而把这种考选与培训模式制度化并且持续几十年的,则是赫德掌管的晚晴海关洋员的汉语学习。它的培养目标、培训方式、教学环节与教学效果,堪称一时之选。这种成人招考、带薪学习、制度管理、择优分配、计划招生、长年开办的外籍职员外语教学模式与管理经验,对当今的汉语国际推广与汉语国际教育,应该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9)》,中华书局, 1990—1996。
[2]Chen Xiafei,Han Rongfang,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Foreign Langeuges Press ,Beijing,China,1992
[3]〔美〕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司马富编,傅曾仁等译:《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1854—1863)》,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
[4]〔美〕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司马富编,陈绛译:《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1863—1866)》,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5]〔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黄胜强:《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1—3)》,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
[7]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驻华使领馆翻译生的选拔招聘与培训录用,带来新的培训模式。这种成人招考、带薪学习、制度管理、择优分配、计划招生、长年开办的外籍职员外语教学模式与管理经验,对当今的汉语国际推广与汉语国际教育,应该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作用。当时的培训内容及成效也可从对相关教材的研究中窥见一斑。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