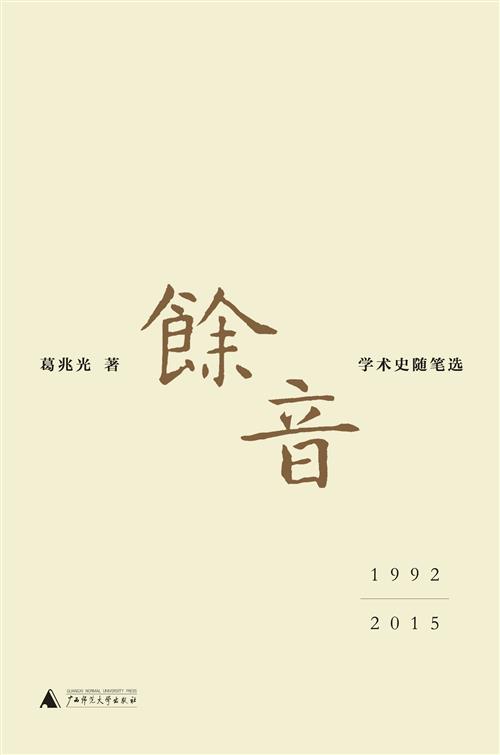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7-01-01
定 价:62.00
作 者:葛兆光 著
责 编:莫嘉靖 马小溪
图书分类: 经典阅读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思想 历史
开本: 16
字数: 230 (千字)
页数: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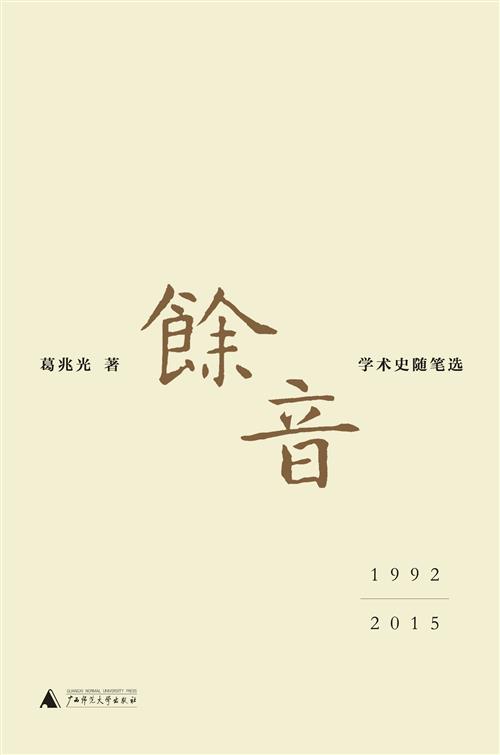
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在这些学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这些人中,有的融入历史的大动脉中,有的成了被遗忘的暗流。作者回顾他们的经历,探寻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变”与“不变”,捕捉思想史与学术史、时代与个人间那微妙的角力与交融。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至2013年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序 / i
一个佛教居士的忧思 / 003
世间原未有斯人 / 013
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 / 027
阴晴不定的日子 / 043
佚札留存在异乡 / 055
王国维手稿本《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跋 / 065
最是文人不自由 / 079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 093
万里之外总有人牵挂 / 107
学术的意味 / 113
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 / 119
吾侪所学关天意 / 131
“刮骨疗毒”的痛苦 / 145
谋万国知识之沟通 / 155
重读潘光旦 / 161
不是旅行季节的旅行 / 165
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 / 169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 175
重读杨联陞日记 / 189
黄河依旧绕青山 / 201
看人如伊吕 / 217
遥知水远天长外 / 221
师友三十年 / 231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 / 237
附录一 运化细推知有味 / 247
附录二 世家考 / 259
序(节选)
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这个选集。照例,交出文稿,就该写序和定名,可是,用什么为题,写什么作序,我却很彷徨。原来这些文章,大概有近十篇不曾编入各种集子,但也有十几篇,曾经分别收入前些年出版的《考槃在涧》(1996)、《并不遥远的历史》(2000)、《本无畛域》(2010)几本随笔集里。现在回想,编那几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总觉得前辈学者余荫犹在,如果“发潜德之幽光”,沿着余波或许仍可以溯流向上。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余音”这个多少有些无奈的词语。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因此现在我想到的,却是“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
一
从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在我看来,这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尽管我写了不少有关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但我总觉得,把这些别有怀抱的随笔看成学术史,其实多少有些误会,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谈王国维,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谈陈寅恪,应该讨论的是他的那些预流之学问,比如中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至于周一良,学术史最好讨论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毕竟是书生》。
不过话说回来,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身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本“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瞠目不知时已变”。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且不说帝制王朝与共和政体的交替,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冲突,民族本位与世界主义的抉择,就是业已习惯的旧传统与汹涌而来的新潮流,赖以自负的旧学问与需要追逐的新知识,习惯面对的旧朋友和不得不面对的新贵胄,也已经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
因此,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20 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1927 年6 月2 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6月14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
马分道而驰,则宓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挽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
★ 这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会是学术史上的绝响吗?——20世纪上半叶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人,这个时局动荡的时期,却成了学术的黄金时代。借由一个个知识人的片断,重新审视大时代下的个体生命。
★ “国学”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如今被视为“国学大师”的民国人物,在当时都是利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开了新风气的现代学者,返视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转型,观照现在的“国学”,我们或许会发现“国”与“学”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 在东西文化、新旧学术的十字路口,知识人该如何选择?——可以是通往现代世界的大道,也可能会带人坠入“背叛传统”的深渊。有的人手足无措、痛苦绝望,也有人徘徊犹豫、摸索前进。数十篇“学术史的别页”,刻画出那一代学人的的挣扎和探索历程。
最是文人不自由
——读《陈寅恪诗集》
书桌上摆着《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的校样,看了两天,续续断断,全没有先睹为快、一气读完的兴奋。并不是陈寅恪的诗不好读,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公子费尽心力广为搜罗编年辑成的诗集,比当年出版的《寅恪先生诗存》多出百余首,并附有唐筼存诗,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不少可琢磨玩味的意思,可偏偏读不下去。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97 页),我全然没有想到,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我想,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学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107 页),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不知为什么,读《陈寅恪诗集》时我想到的都是一个意象:啼血。
一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在《吾侪所学关天意》那篇文章里我曾提到,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只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的陈寅恪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有另一种情结。袁世凯当大总统,他写诗讥讽如巴黎选花魁,“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6页);张群组阁,他讥讽他装模作样,“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53 页);共产党打过长江,他又写诗嘲讽国民党,“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57页)。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21 页),三用“食蛤那知天下事”(27页、51页、9页),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这也难怪,中国士大夫大多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实和李白“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尽管一个含蓄一个狂放,一个正儿八经一个志得意满,想干预政治这一点上,却是半斤八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诗集》里陈寅恪用陆机作《辩亡论》的典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欲著《辩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19 页)、“《辩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22 页),其实已说尽了他心里的意思。“栏杆拍遍,何人会,登临意”,他觉得自己有一肚皮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学术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负他生”,当他以十年精力写完那本后人再四击节的《钱柳因缘诗笺证》时,他竟想到了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年”的话,全然没有文稿杀青的欢欣和轻松,却长叹“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21 页)。
可能是真的,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跌宕翻滚的恶浪?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
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但这实在只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只是当他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掩饰着,因此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18 页)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二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文章存佚关兴废”(80 页),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王观堂先生挽诗序》中,他反复申论的“文化”与“精神”,正是他极自负处,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的,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在他的诗里,我们能看到他对学术生涯的自讽自嘲,但也能看到他对学术论著的自珍自爱。尽管他“无才可去补苍天”,但他觉得,毕竟可以用他的论著存文化精神血脉一线于不坠,所以他对自己的著作始终倾注了极多的心血,尤其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命运越发清醒的时候。1956 年除夕,他写下一首诗,感慨地说道(98 页):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
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虫鱼。
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
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盘虚。
在“有命注虫鱼”的无可奈何中,他把自己的怀抱化成学术论著,1957 年,他又作诗,写下这样两句:“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愁什么?愁的正是“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因为这论著是他的精神血脉,他处在寂寞之中,除了论著刊布,又能有什么别的形式来显示他的存在?“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105 页)于是1962 年陶铸和胡乔木到中山大学去看他时,他说的就是这八个字:“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当他不得不用这种暗示性的说法请求要人援手时,我们知道,这论著已是他最后牵肠挂肚的心事了,正是“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80 页)。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应该说,这两部书尤其是后者,立论上是明显有感情偏颇的,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绕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67 页,“白头宫女”又作“白头学究”);对那些趋时者,他实在难以按捺心头的怒气,“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63 页),对那些附势者他实在不能掩饰心中的轻蔑。但他依然知音难觅,孤独中只好自嘲自责,“旧学渐荒新不进,自编平话戏儿童”(44 页),“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99 页)。可是,透过这些自嘲自责的诗句,我们又可以明白,其实他是多么渴望被理解,哪怕是身后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才一面怨艾“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116 页),一面哀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140 页),一面自嘲“千秋有命存残稿,六载无端咏旧题”(116 页),一面满怀期望地感慨“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121 页)。可惜的是,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78 页)
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他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他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才发现真的只剩下孤独与寂寞。时下流行歌曲唱得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为什么要那么清醒?既然他明白“闭门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62 页),他为什么要期望那么殷切?
多病与盲目也许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 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47页),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51 页),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我总觉得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总是在互相对抗,即所谓“身与心仇”,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 年写的《癸未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 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表面看来是哀叹身为心累,若没有这个臭皮囊,我还有什么生老病死的忧患,其实不然,有人一眼就窥见老子心底,欧阳修说这是“道家贪生之论”,朱熹说老子实际上“爱身之至”。陈寅恪也是如此,似乎他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他对白居易有极深的研究,也最爱读白居易诗,这一点他也很像白居易,白居易虽信佛教道教,觉得“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毕竟共虚空,何须夸岁月”,觉得“彭觞徒自
异,生死终无别,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赠王山人》),但总是十分爱惜生命,长了一根白发就再四感叹,惊慌失措地说“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初见白发》),洗澡时看见自己羸弱又再四感叹,唉声叹气地说“四十已如此,七十复如何”(《沐浴》),掉了一个牙齿时又再四感叹,愁眉苦脸地说“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自觉二首》之一),所以大凡表示对自己躯体满不在乎甚至觉得躯体为累赘的人,其实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陈寅恪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盲目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61 页),“残废何堪比古贤,昭琴虽鼓等无弦”(72页),“衰残敢议千秋事,剩咏崔徽画里真”(102 页),“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118 页),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57 页),“故老空余后死悲”(58 页),“老去应逃后死羞”(108 页),“自信此生无几日”(120 页),盲目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在他预先给夫人唐筼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其实,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悲剧人物。我这里说的不是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我这里说的也不是他曾得到国共两党政府要人的殷勤探望和多方关顾,这点恩德对于陈寅恪这样自负的人来说虽然能使他一时感激,却不能抚平他心底深深的遗憾。我要说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其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二是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1951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筼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惟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67 页)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筼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24 页)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93 页)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湜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但是,在陈寅恪身上还是演出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究其原委,一半儿在外一半儿在内,他精研韩愈,却没有注意韩愈《感春四首》之四中“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霜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这样的箴言,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青山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82 页),他自知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他写道:“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131 页)这种悲哀横亘在心头,又纠结成绝望盘旋在诗中,于是他的诗集里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生涩。当年吴宓曾说他“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答寅恪》),又说他“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1],的确,我们从陈寅恪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陈寅恪,而从陈寅恪的诗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个陈寅恪,而后一个心灵中充满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也许更为真实,自从文人的真实情感从“文”中逐渐退却到“诗”,“诗言志”的说法又把心底情怀大半逐出诗歌领域以来,“诗”已经不那么让人感动了。可是,《陈寅恪诗集》却写下了这个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深处有一种无计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25 页),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
1993 年2 月28 日于京西寓所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