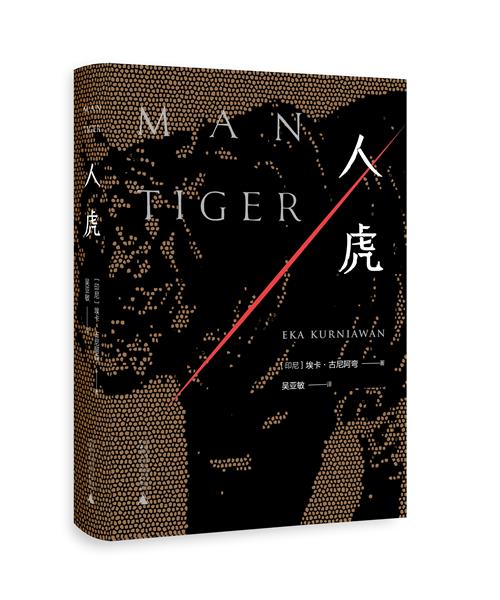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7-10-01
定 价:39.80
作 者:[印尼]埃卡·古尼阿弯 著 吴亚敏 译
责 编:罗财勇 唐俊轩
图书分类: 外国小说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外国文学及小说爱好者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小说
开本: 32
字数: 100 (千字)
页数: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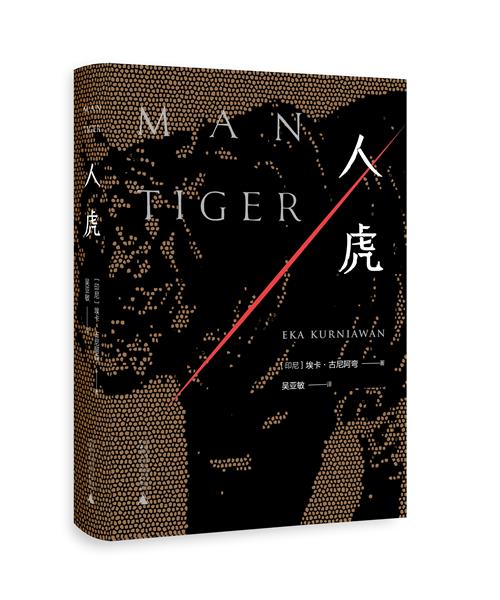
这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海滨小镇里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马吉欧,无论怎么看都与常人无异的少年,却声称自己体内住着一头白色的雌虎——这源于印度尼西亚古老的传说。生活的困苦与家人的背叛折磨着这个不幸的少年,彻底被激怒的他无法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或者如他所说,身体内的白虎一跃而出——咬死了自己心爱女孩的父亲。随着故事发展,这次暴力事件背后隐藏的令人心碎的原因才被一一揭开。
埃卡•古尼阿弯,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平面设计师,1975年生于印尼西爪哇省打横市,毕业于印尼日惹加札•马达大学哲学系。他的作品已被译作24种不同语言,小说代表作《美丽是一种伤痛》被《纽约时报》列入“百部值得关注的图书”。2016年,古尼阿弯凭借小说《人虎》成为印度尼西亚首位入围布克国际奖的作家。古尼阿弯擅长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因此文学评论家经常将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较,称赞古尼阿弯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
2015年,因“将印尼文学介绍给世界”,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全球思想家”荣誉
2015年,《人虎》获印度尼西亚出版协会年度最佳图书奖
2016年,《美丽是一种伤痛》获美国“世界读者奖”
2016年,《美丽是一种伤痛》获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
2016年,凭借《人虎》入围布克国际奖长名单,印尼首位入围该奖项作家
2016年,《人虎》获英国《金融时报》奥本海默基金“新兴之声”小说奖
2015年,《人虎》获美国Flavorwire网站年度最佳小说奖
无
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文学史上最令人振奋的事件往往是文学新人的崛起,它并没有什么目的性,也不被历史的车轮所驱使。最具原创性的作家有如突现的流星,谁能预见到索福克勒斯、维吉尔、紫式部、塞万提斯、梅尔维尔、鲁迅、莎士比亚、普鲁斯特、果戈理、易卜生、马尔克斯或乔伊斯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又是哺育其成长的本土语言的产物。然而,无数人和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讲相同的语言,却写不出什么值得纪念的作品。论阶级出身和教育背景也都无法解释他们的出现,因为在他们家族的先辈和后裔中极少有人显示出同样杰出的文学才华。
埃卡•古尼阿弯无疑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最具原创性的小说家,一颗出乎意料的文学新星。他出生于1975年11月28日,那一天东帝汶宣布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独立。1975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34周年纪念日那天,美国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到访印度尼西亚,为独裁者苏哈托发起吞并东帝汶的战争(使用美国生产的武器)而喝彩。埃卡一直以他的生日为豪,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东帝汶人民坚持了长达22年的不懈抵抗,最终迫使雅加达放弃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十岁前,埃卡基本上是和外公外婆生活在西爪哇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他的出生地,靠近印度洋,地势崎岖,与世隔绝(没有路通到村里)。外公外婆识字,但简陋的家里没有书籍,小埃卡通过村里的两个女人和一个“隐身人”接触“文学”。他的外婆喜欢讲民间传说、童话故事和村庄的历史。另一个寡居的老妇人(也是他家的远亲)更是讲故事的能手,几乎每天晚上,人们在当地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她就让村里的孩子们聚在她家的廊台上听各种神奇的故事,这让孩子们开心不已。“隐身人”则是一个电台的故事播音员,他能把主要住着巽他人的西爪哇(当时中爪哇和东爪哇受爪哇人统治)当地民间传说中的各种人物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
1984年小埃卡回到父母身边,在庞岸达兰读小学。庞岸达兰位于中爪哇和西爪哇之间,是一个人种混杂的商业小镇,通用语言是爪哇土语和巽他语。小镇里没有书店和公共图书馆,但他的父亲会从学校简陋的图书室里带几本书回家给孩子们看。他的父亲是一名裁缝,也偶尔为游客做几件T恤。他还像是埃卡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原型,身兼两种迥然不同的身份:既是当地穆斯林的领袖,教不会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儿童背诵《古兰经》,又在一所学校兼职当英语老师。父亲年轻时曾在一所师范学校读过书,但没毕业。正因为有这样的教育背景,他晚上才能抽空为附近的清真寺写布道词,为各种穆斯林刊物写一些宗教文章(埃卡说他从不看这些文章!)。对埃卡来说,更重要是他很小就发现了两个所谓的“书园”,一个在汽车站,另一个在海边小旅馆的后面。小摊贩在那两个“书园”里出售或出租印尼本土的恐怖和格斗漫画,还有胡乱翻译过来的尼克•卡特的侦探系列小说和芭芭拉•卡特兰的爱情小说。有时小贩也会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兜售或出租类似的书刊。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11岁的埃卡开始写诗、小故事和小说梗概。
埃卡在庞岸达兰读高中时肯定是个成绩拔尖的学生,所以17岁时就被日惹的加札·马达大学录取。1945-1949年,在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战争期间,日惹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大学时,埃卡只能选择他并不是很感兴趣的哲学系,但他在管理混乱的哲学系图书馆里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一本小说——《大地的成长》的英译本,这令他兴奋不已。后来他又在大学附近的跳蚤市场上的旧书堆中寻到同一作者的另一本更著名的小说——《饥饿》。有意思的是,加札·马达大学图书馆里有一间美国大使馆捐助的美国研究图书室,他惊奇地在里面找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塞万提斯和博尔赫斯的小说的英译本,还有俄国的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当时苏联已经解体)。毫无疑问,这间美国研究图书室里自然少不了福克纳、海明威、韦尔蒂、斯坦贝克、托尼·莫里森和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等名家的作品。
据埃卡回忆,他当时很少读印尼本土的文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加札·马达大学容纳了来自印尼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的宗教信仰、种族、语言、风俗习惯和理想抱负千差万别,作为一个“乡下人”,埃卡在日惹这座大都市中切身感受到了文化冲击。而在美国研究图书室里,他可以把这种文化冲击置于脑后,集中精力研究世界文学。而且,精通英文的印尼人很少,所以能在这个领域超越他的人不多。二是因为轻视文化的独裁者苏哈托屠杀了数十万所谓的“共产党人”,并在全国设立一系列集中营囚禁政治犯,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时期(1966-1998年),其间各种左派作家和所谓的“颠覆分子”的书籍都被查禁。印尼杰出的小说家和著名的评论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未经审判,就在偏远的布鲁岛上的监狱里被关了14年,出狱后他的所有作品仍被列为禁书。直到现在,苏哈托的禁令实际上已形同虚设,但仍然没有被废除。
20世纪90年代的加札·马达大学虽主张变革,但仍是一所旧式大学,也还没有那么商业化、美国化和学术化。学生可以一直留在学校里读书,不会被退学,毕业论文也不必按照严格的学科划分撰写。直到1998年,埃卡都一直在那里读大学,在此期间他在雅加达的《星期天报》上发表了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
尽管如此,1997年埃卡还是决定写一篇关于普拉姆迪亚的“哲学”毕业论文。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题?因为自1996年以来,印尼各种报刊上开始提到一个半地下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民主党”,它吸引那些积极反对苏哈托政权的年轻大学生,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埃卡回忆说,他和系里一些人民民主党学生有密切联系,但对参加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并不感兴趣。人民民主党在日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偷偷散发普拉姆迪亚在狱中创作的《布鲁岛四部曲》,这部鸿篇巨制讲述了在20世纪的前25年中,印尼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埃卡从一个人民民主党的朋友那里得到了几本,读后深受影响,兴奋不已。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9月席卷印度尼西亚。几星期内印尼卢比大幅贬值,从2500卢比兑换1美元降至17000卢比兑换1美元。银行和企业纷纷破产,人民失业,经济几乎崩溃。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其中一些活动就是由人民民主党组织的,旨在推翻苏哈托政权。埃卡在日惹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那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苏哈托政权用残酷的手段极力镇压,很多主要的活动积极分子被绑架、拷打,甚至失踪。“我在1998年初向系里那些被吓坏了的老师们提交了关于普拉姆迪亚的毕业论文,但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雅加达‘五月暴动’后不久,苏哈托被迫辞职,其政权垮台,我又把论文提交上去,这次自然很轻松地就通过了。”其后,埃卡的一些人民民主党朋友找到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毕业论文《普拉姆迪亚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
几年后,埃卡在书面回答一个关于哪些印尼作家对他影响最深的问题时,谈到三位忧郁的印尼作家:第一位是印尼最为杰出和主张独立的诗人、北苏门答腊贵族阿米尔•哈姆扎,他在1945至1949年的革命中被伪装成革命者的匪徒处死;第二位是普拉姆迪亚;第三位是勇敢、激进、主张革新的爪哇诗人威基·杜库,他后来失踪了,也许是遭到苏哈托野心勃勃的女婿普拉博沃将军指派的杀手暗害(庆幸的是,普拉博沃在2014年的印尼全国大选中被深受人民爱戴的雅加达年轻州长、第一个没有受苏哈托政权影响的总统候选人佐科·维多多击败)。
原创性作家和他们结交的圈内人通常都有些自负,因此对这些作家和他们作品的研究主要落在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身上。这种情况在印尼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一样,但年轻的埃卡是个少有的例外。他在书中由衷赞赏普拉姆迪亚的政治勇气和对印尼文学的创新,但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过时的文学形式。可惜的是,他的研究几乎全部以《布鲁岛四部曲》为基础。当时他看不到普拉姆迪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的多卷本短篇小说集,那些短篇小说全然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是带有早期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2000年埃卡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大胆地取名为《厕所中的涂鸦》,两年后他出版了大部头小说《美丽是一种伤痛》。他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在很多方面风格迥异,使他立即成为印尼文学界的一颗新星。埃卡的短篇小说集显示了他作为黑色幽默和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家所具备的写作技巧,他讥讽同时代的人(包括人民民主党领袖,因为他们很快就成为追逐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同时也显示出他将童年时期在小山村里听到的故事与苏哈托政权垮台后的都市资产阶级文化相结合的娴熟的写作技巧。相反,《美丽是一种伤痛》虽然是一部带有历史性质的长篇小说,描写的内容跨越印尼的荷兰殖民统治晚期、日本侵略时期、1945至1949年的革命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叛乱时期、印尼共产党兴起到最后被血腥镇压等历史时期,以及早期的苏哈托统治时期,但小说的背景并不是全国性的,甚至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印度洋沿海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镇。小说中的故事都不见经传,充满了魔幻风格,融合了传统或新编的民间传说以及混乱不清的口述历史。
埃卡曾经对我说,《美丽是一种伤痛》源于三本早期的小说,后来他决定克服重重困难,把那三本小说合并为一部巨著。读者可以想象,这部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于他对普拉姆迪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甚至也许是对那位老先生著名的、已被译为多种语言的四部曲发起的挑战。
2004年他创作了小说《人虎》。和《美丽是一种伤痛》一样,故事的背景依然是印度洋沿海的一个无名小镇及其乡村环境,小说的篇幅相对较短,但构思更为严谨和讲究,主要描写发生在相互交织的两个家庭的两代人之间充满痛苦的悲剧故事。主人公马吉欧是一个生活在城镇和乡村接合部的普通青年,体内有一头从他敬爱的爷爷那里继承的超自然的白色雌虎。在印尼,很多地方都流传着一些代代相传的神话,说神奇的雄虎保卫着村庄和善良的人家。但这些雄虎是具象的,住在丛林里。埃卡借鉴了这些古老的神话,将他笔下的虎改成雌虎,并让它潜伏在马吉欧体内,他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能力控制它。本人无意在此叙述《人虎》的更多故事情节,希望给读者留个悬念。
我想更多地评述埃卡写作风格演变的重要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他不同于任何其他同时代的印尼小说家。一是他的文笔十分唯美并使用了海量的词汇进行创作,其中包括当代的新兴词汇和许多仍然在边远村庄中使用却已经在现在的都市用语中消失了的意义晦涩的词。二是他的小说往往以“讲故事者”的口吻展开叙述,人物之间的对话很少,如果有,也只是短短几句。这个“讲故事者”是个完全不存在的人物,读者根本不知道他的性别、年龄、职业或住所。三是埃卡逐步尝试运用超自然的写作手法。在小说《美丽是一种伤痛》中,魔幻无处不在,现在仍然在印尼流行的传统木偶戏场景也极多。这种木偶戏以在当地流传的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为基础,因而戏中有一大批男神、女神、高贵的勇士、魔鬼、国王、巨人、小丑、鬼魂、公主,等等。所有这些人物都被高度地符号化了,比如公主和女王都美艳无比,而女丑角则长得奇形怪状,相貌平平却又令人着迷的女人并不存在。在埃卡早期的两部小说中,女人总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或“奇丑无比”。但在小说《人虎》中却只有一个超自然的东西,为人物性格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发展的普通女人留出了空间。四是他更好地把握了时间顺序。《人虎》中的章节随着时间的转换进行了巧妙的布局,没有突然的闪回,小说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描述的场景几乎同时发生。《美丽是一种伤痛》中有许多时间转换,但往往显得随心所欲和毫无必要的混乱。五是性。《美丽是一种伤痛》中有大量的性描写,但这些场景被以皮影戏方式出现的过多的超自然主义所淡化。而在《人虎》中,性往往是野蛮和带有欺诈性的,这些悲怆的场景与小说情节息息相关。埃卡创造出一头超自然的白色雌虎并将它放在男人身边,这是一项创新,使整个故事成为三维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维,进而可以让读者对小说产生不同的理解。评述埃卡这些成熟的写作风格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他的创作能完美地融合新与旧,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原创性。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最喜欢的两位作家是果戈理和梅尔维尔。
大胆、老辣、幽默,埃卡•古尼阿弯可能是当代东南亚最雄心勃勃的作家。他逐渐成长为印度尼西亚的村上春树,其作品运用大量的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侧面揭露了社会百态。——《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古尼阿弯创作的世界既熟悉又令人意想不到,其中融合了魔法、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传说。——《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故事紧凑、主题明确、内容让人毛骨悚然。像所有成功的犯罪小说一样,《人虎》非常适合一口气读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一个结合了谋杀和欲望的超自然故事,一本迷人的颠覆传统的犯罪小说。——《卫报》(The Guardian)
不容错过,值得一读!——《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埃卡•古尼阿弯无疑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
毫无疑问,埃卡•古尼阿弯是如今印度尼西亚最具原创性和想象力的小说家,他优雅、明亮,就像一颗令人意想不到的陨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人虎》写一桩离奇的少年杀人案,由此描述了印尼的乡镇生活、家庭纠葛、男女爱情,以及人性的复杂。受印尼口述故事的传统形式影响,小说开篇便交代了杀人案的凶手和遇害者,之后才层层剥茧,道出酿成这起悲剧的原因。这使得整个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下去。
在小说中,作者埃卡•古尼阿弯完美呈现了印尼村镇的自然及人文风貌,并将魔幻现实主义和印尼民间传说融入其中,碰撞出精彩的火花。读完《人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文学批评家会将埃卡•古尼阿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本书责编
大胆、老辣、幽默,埃卡•古尼阿弯可能是当代东南亚最雄心勃勃的作家。其小说《人虎》围绕一个谋杀之谜展开。尽管开篇第一句话就揭露了凶手和遇害者,凶手的杀人动机也并不神秘,然而整个故事仍让读者感到痴迷。这证明了埃卡•古尼阿弯极高的写作天赋,特别是他制造悬念和紧张故事情节的技巧。小说的主人公,少年马吉欧,其实可以看作是生活在爪哇岛上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只不过他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一切都是住在他体内的那只白色的雌虎干的。
埃卡•古尼阿弯称《人虎》中有他自己的影子,他说:“我和马吉欧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在印度尼西亚,我们保持愤怒,也压制愤怒。但最后,心中的猛虎往往会挣脱牢笼,一跃而出,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种对“个体”而非“政治”的关心,以及小说中体现的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抗拒,使埃卡•古尼阿弯摆脱了印尼大作家普兰莫迪亚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束缚。在荷兰殖民统治的末期,普兰莫迪亚希望通过写作唤醒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因此被誉为印尼的爱弥尔•左拉。而埃卡•古尼阿弯正逐渐成长为印尼的村上春树:其作品运用大量的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侧面揭露了印尼的社会百态。——《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编辑
那头雌虎和天鹅一样白,比豺狗更凶猛。玛梅曾经看见过一次,雌虎如影子一般从马吉欧体内冒出来,稍纵即逝。此后,她就没再看见过。可以看得出雌虎仍然潜伏在马吉欧体内,但是玛梅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发现那是什么。黑暗中一双虎眼在马吉欧的瞳孔中闪烁着黄色的光芒。最初玛梅被吓得不敢直视那双眼睛,害怕雌虎真的会从里面再跳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玛梅见多了,对那双在黑暗中闪烁的眼睛已经习以为常,也就不再为此感到忧虑了。雌虎不是她的敌人,也不会伤害她,也许它是在那儿保护他们所有人。
马吉欧离家出走的几星期前偶然看到了它。那是一个清晨,当时他独自一人在礼拜室里睡觉,雌虎舞动的尾巴轻轻拂着他的一双赤脚,把他弄醒了。他以为那是马·索马在拍他,叫他起来和自己一起做礼拜。他睁开眼睛,没看到托盘上有热气腾腾的咖啡,饭盘里也没有炒米饭,却看到一头白虎卧在他身边舔着虎爪。已是拂晓时分,天色明亮,空气湿润。显然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雨,这时还没有人来做礼拜。马吉欧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能做的只是敬畏地盯着那头正在满心欢喜地打扮着自己的壮硕的野兽。
他知道这野兽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星球上活着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在小镇郊外的丛林中游荡,但从来没看过这种野兽。他见过野猪、身上斑斑点点的小猎豹和豺狗,却从来没见过几乎像牛那么大的白虎。他流下了泪水,慢慢伸出一只手摸着雌虎的前爪。那似乎又是真的老虎,虎毛柔软得有如鸡毛掸。雌虎将爪子缩回去向他示好。就在虎爪抬起来时马吉欧再次把手伸过去,雌虎有意与他玩笑,像猫那样用虎爪轻拍了他一下。马吉欧试着去抓雌虎的爪子,但它躲开了,翻身爬起,伏身到另一边做出准备发起攻击的样子。马吉欧还没来得及躲闪,雌虎就扑过来了,和他扭成一团。他累得平躺在地上,气喘吁吁。雌虎这才往后退开,卧在他身边又开始舔舐虎爪。马吉欧轻柔地拍了拍虎肩。
“爷爷?”马吉欧说。
爷爷住的村子离马吉欧家很远。他先要搭载客的摩托车到丛林边缘,那里有一排叫“星期五集市”的小商店,是各种交通工具的终点站。再往前就是山林间蜿蜒崎岖的泥巴小道,如果有辆牛车也许可以继续往山上走,但摩托车就很难再开进去了,载客的摩托车车主根本就不愿意去。去看爷爷时,马吉欧得在合欢树林和三叶草丛中跋涉,再穿过红木树林,深入只有猎人才认得路的丛林深处。接着他要在一片山地间走一个小时,那儿只有他和那些可能在某一天会成为他的猎物的野猪才熟悉。山的后面是一个小村庄,稻田和鱼塘环绕着一所伊斯兰学校。爷爷并不住在那里,而是住在一个可以使马吉欧身心放松的地方。多次从小村庄走过之后,他在路上也认识了一些当地人,但他不能在那里逗留太久,得在夜色降临、渡筏停摆之前赶到小河边。渡筏是用一排竹子做成的,系在一条穿越小河两岸的缆绳上。摆渡工站在竹筏前拽着缆绳,慢慢拉着竹筏往对岸走,水流湍急的时候还得用一根竹竿撑筏。小河不浅,水流缓慢。河里没有鳄鱼,但有能掀起巨浪的水怪,尽管谁也没见过,孩子们却都很害怕。过河只要花十分钱,渡筏一次可以运十几个人,以及他们的牛羊、一袋袋稻谷和其他农产品。下了竹筏后马吉欧还得继续往前赶路,沿着一条滑溜溜的小道爬上另一座山。在山顶上他可以看到下面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广阔的原野中央是另一个小村庄,好似沙漠中的绿洲,草木葳蕤,房屋密布,椰子树高耸入云。
马吉欧八岁时第一次自己走这条路。其后他只要有机会就去那里看爷爷,尽管他得走半天。他总是玩得十分高兴,也总会带一大串香蕉或者一篮子兰撒和榴莲回家,让玛梅和父母高兴一下。有时如果他特别想去爷爷家但又没钱搭摩托车,他就走到“星期五集市”,然后再继续赶路,虽然会累得半死,但仍觉得快乐无比。有时他也走不同的路线,因此很快就和村民以及住在丛林里的妖精交上了朋友。从此以后,只要他在,一起捕野猪的伙伴们就再也不担心迷路了。
爷爷虽已白发苍苍,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无疾而终,去世后人们才在他的床上发现他的尸体。他每天都在一块稻田和一个种植园里劳作,但后来这一整块地被马吉欧的父亲卖掉,再也不是他们的了。马吉欧真心爱他爷爷。老人会带这孩子去一条小河,他说那里是妖精们的王国。他总是说,不要调戏女妖精,但如果某个妖精爱上你了,那就把她带走,因为那是件好事。爷爷还说女妖精都非常漂亮。马吉欧总是期望有一天他能遇到一个爱上他的女妖精,但无论他去过多少次那条小河,那种艳遇的可能性总是挂在天边遥遥无期。
更令他心迷神驰的是有关爷爷的雌虎的故事。据村里的讲故事人马·姆哈说,村里的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雌虎。有些人娶了雌虎,有些人则是继承了祖先的雌虎。爷爷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头,而这一头以前又属于他父亲的父亲,一直往上追溯到他们的远祖。没人记得谁最先娶了雌虎。
在温暖的夜里,马·姆哈会坐在她家的廊台上讲故事。孩子们蜷伏在她脚边,女孩们轮流按摩她的后背。如果她在纺纱织布,女孩们就认真翻她的头发找虱子。她总是有新故事,也不必编什么故事,她说,她讲的都是真人真事。和雌虎的故事一样,许多故事都是通过一代代讲故事人的传述才流传了下来。但有些现在发生的故事只有一些特定的人才能听得懂,马·姆哈当然就是那个能听得懂故事的老奶奶。
马吉欧记得马·姆哈既没有丈夫和孩子,也没什么事可做,她只是没完没了地讲故事。她可以走进任何人的厨房,在里面吃饭,也有人会带些吃的到她的木棚里给她。人们爱她,孩子们尤其喜欢她。她讲过一个瞎眼女人的故事,那女人只吃紫莎草茎,头发里有蛇和蝎子,但没有虱子。她还讲过关于妖精公主们的故事,专门诱拐英俊小伙子去她们的王国。但如果人们不闯进她们住的地方,她们也不会有什么恶意。后来马吉欧才知道那些地方是清泉里、河塘里、山顶上和大树上。然而,最能唤起马吉欧的好奇心的是关于保护神白色雌虎的故事。
据马·姆哈说,白虎和主人住在一起保护主人平安。她说他爷爷也是那些有白虎的人之一。但爷爷从来不对孙子讲白虎的事,他说马吉欧还太小,没法驯服这样凶猛的野兽。白虎比斑豹大得多,比人们在动物园、马戏团或者学校课本里看到的老虎大得多。如果有人无法控制住他的野兽,一旦它跑出来,就会变得非常凶狠,没法制服。
“但我只是想看看它。”马吉欧说。
“以后吧!也许你会拥有它呢。”
他经常听人说他爷爷孔武有力,也听说过村里其他老一辈人的故事:他们抵抗荷兰人,让入侵者怎么都没办法把最出色的年轻人拐骗到德里国;子弹打不死他们,后来入侵的日本人的武士刀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发怒时体内的白虎就会冲出来发起进攻;他们还赶走了在丛林里游荡的“伊斯兰之家”游击队。马·姆哈说,这都是因为那些老一辈的人从小和雌虎结下了情谊,雌虎通过结姻成为家族的成员。
马吉欧从来都弄不懂这类婚姻是什么意思。他无法想象婚礼上有个男人坐在一只头戴流苏、虎颊抹粉、虎唇擦着口红的雌虎身边,婚礼主持人祈求安拉保佑某某先生和这只雌虎。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觉得一个男人和他的老虎妻子性交是非常奇怪的事,他不知道通过这种结合而生下来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每次他对马·姆哈说起这种关于人类和老虎的婚姻的想法时,她就会露出掉光了牙齿的牙床咯咯大笑起来。
“只有男人才和老虎结婚,”马·姆哈说,“但也不是所有老虎都是雌的。”
爷爷当然有个妻子,一个女人。所以很清楚,那头雌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爷爷的妾。爷爷从来没有和雌虎结过婚,因为他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对于这个家来说,雌虎仍然是爷爷的另一个配偶,受到爱戴和尊重,有时甚至甚于人妻。马吉欧的奶奶先过世了,死于支气管炎。这种病使他们整夜听着她的咳嗽声而无法入睡,也使她在死前不时发烧,身体萎缩。爷爷从此鳏居孑然,或许有头雌虎陪着,他便觉得足够了。但他也没再活多久,妻子的去世所带给他的沉重的打击,很快就夺走了他的性命。
马吉欧在爷爷生前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有一天晚上老人明确地说:“那头虎白得像天鹅。”
如果雌虎出现在马吉欧面前,爷爷希望他认出它来。爷爷又说,如果雌虎愿意的话,它可以去找马吉欧的父亲成为他的妻子。这样马吉欧就得等他父亲死后才能得到雌虎。但是如果它不喜欢他父亲,就会在某一天去找马吉欧,当他的妻子。
“如果它也不喜欢我呢?”马吉欧急切地问。
“那它会去找你的儿子或你的孙子,或者如果我们家的人把它忘记了,它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现在这雌虎来找他了,在外面的世界还是一片寒冷时,静静地卧在礼拜室里他身边温暖的地垫上。和爷爷说的一样,雌虎白得像天鹅,像天上的白云,像棉花。他兴奋莫名,因为这头雌虎比他所拥有的其他一切都宝贵。他想象着它会怎样和自己一起去捕野猪,帮助他把毁坏稻田的野猪赶进兽栏;而且如果有一两头野猪攻击他而他又无力抵抗时,它就会保护他免受伤害。马吉欧从没想到雌虎会在这么一个寒冷的清晨出现,像姑娘一样把自己奉献给他,有一阵子它看上去又像只家猫。马吉欧深情地凝视那张对他来说是如此可爱的脸,这小伙子觉得自己深深陷入情网了。
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它的脖子,抱着它,感受着贴在他身上的虎皮所带来的温暖。这种感觉就像在寒冷的清晨赤裸裸地和一个姑娘在床上相拥,享受历尽整夜缱绻之后的柔情蜜意。马吉欧闭上眼睛,感受历经长期等待后的心醉神迷,他从此不再渴望,确信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都是真的。然而,他突然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他的挚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它所带来的温暖消失了。马吉欧睁开眼睛,雌虎不见了。
这使他比刚看到雌虎时还吃惊。小伙子站起来寻找,礼拜室很小,他确信雌虎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根虎毛都没留下。大雨依然哗啦哗啦下着,路上上学的孩子们的抱怨声传了进来。下这样的滂沱大雨时,人们会去割香蕉叶来当随时可以扔弃的雨伞,但马吉欧没心思想这事。他心里除了那头雌虎以外什么都不想。他茫然地站在那里张嘴呼唤,却得不到回音。他不知道要怎样称呼那头雌虎。爷爷从来没有告诉他它叫什么,马·姆哈也没说。或许他们觉得他得给它起个名字。但是,如果没地方去找这家伙,给它起名字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或许他会因曾经失去他所挚爱的姑娘们而心碎无数次,但现在他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所有失恋带来的痛苦的总和。他抑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不,这不是在做梦,他告诉自己。它来找他,因为它属于他。他感受到它那皮毛的温暖,他们曾在一起嬉戏。这太真实了,绝对不是一个在清晨所做的寂静的梦。他一次次寻找,感觉到它真的离开他了之后,他的心痛转为怨恨。他颤抖着紧握十指。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冷酷而渴望报复的狂怒。他没法消除这种狂怒,只能强忍痛苦。雌虎使他陷入情网,让他感受到了多年来一直渴望的幸福的高潮,它不应当这样离他而去。
他在门上敲打着,用指头刮擦着,直到绿色的油漆脱落显露出赤褐色的木板,他嘴里发出令空气都为之震颤的号叫。门上深深的刮痕令他感到震惊。马吉欧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愤怒随之慢慢消退。他瞪着门上三道平行的刮痕,如果刮在某个人的背上,那会是三道极深的伤口。然后他仔细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指甲不长,他把指甲都剪得短短的,不然在捕野猪时手持长矛很不方便。照理说他不可能把门板弄成这样,可他短短的指甲里还是塞满了油漆和木屑。马吉欧蒙了一阵,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些感到敬畏又困惑不解,但他马上想明白了。它没有离开他。雌虎仍在那里,已变成他的一部分,至死也不会和他分离。他倚靠在墙上摸着肚脐,感到雌虎现在就盘踞在他的肚脐之下。它根本不是一头容易驯服的老虎。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