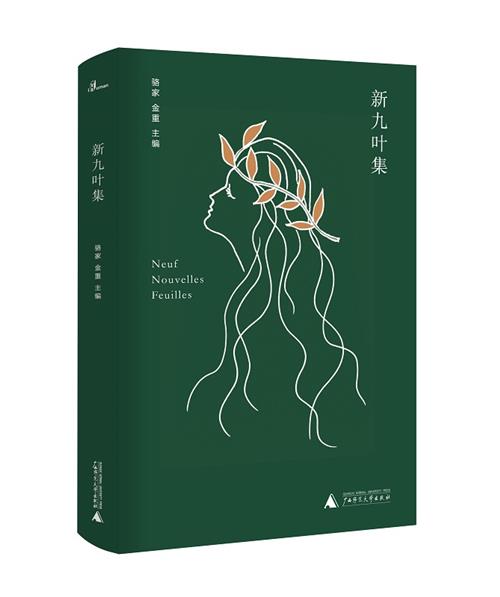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9-03-01
定 价:49.00
作 者:骆家 金重 主编
责 编:柏欲江 多加 张小彩
图书分类: 中国现当代诗歌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当代诗集
开本: 32
字数: 230 (千字)
页数: 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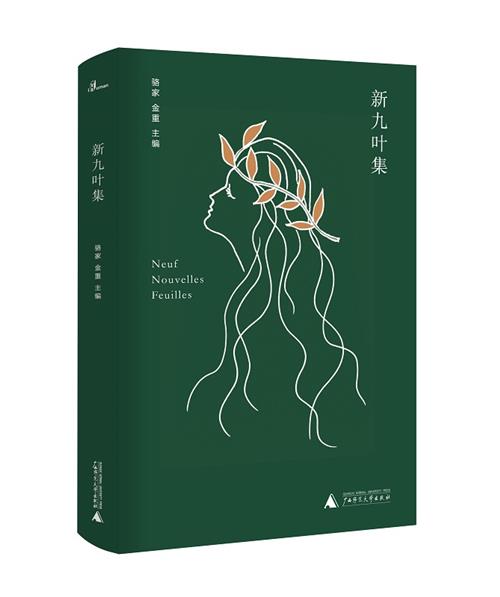
“九叶诗派”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现代诗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力。《新九叶集》是诗人、译者骆家和金重以中国新诗和当代西方现代诗为大背景,在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坚持诗文创作兼翻译工作的诸位诗友中细筛出九家,精心编选其作品而成的一本诗文集。
本诗集在选题上颇有特色和新意,编选者有意向20世纪40年代令人瞩目的“九叶诗派”靠拢,并致敬。王家新先生建议“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入选诗集的“新九叶”诗人,因其同时为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瑞典语等语种的知名文学翻译家,所以他们的诗作呈现出与其他新诗诗人截然不同的特质,他们这些“喝唐诗的母乳和西方现代诗的‘洋奶’”而生、而成的诗作是新诗重要的精神资源和诗学皈依。
中国新诗发展百年之际,重提九叶诗人,是一种对“文化记忆”的重拾和尊重,也是“新九叶”诗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出的新鲜声音。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新诗爱好者,本书的出版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骆家,本名刘红青,诗人,译者。1983年至1988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出版有诗集《驿》《青皮林》《学会爱再死去》,译著《奥尔皮里的秋天》等。
金重,原名郭钟,1986年至1989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中国诗人作品,2017年在美国编辑翻译出版The Carav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大篷车:中国当代诗选》),收录29位中国当代诗人作品。
收入本诗集九位诗人分别是:李笠、金重、高兴、少况、树才、黄康益、骆家、姜山、李金佳。
李笠
自画像 003
特朗斯特罗姆在故宫 004
纪念 005
圆月 006
波兰之恋 008
病中想到父亲 011
为花园的积雪而写 013
关闭与敞开的门 015
死海 017
九华山遇雾 019
悼张枣 020
七彩鸟之死 023
梦中与中国知识分子相遇 024
我的混血孩子 025
腊八 026
黄梅天赏雨 027
拱宸桥的 18 种译法 029
爱情 036
理发 037
雪豹 038
金重
年龄肖像 041
悲哀星期五 042
在绿色的季节 043
紫丁香 044
献给你的歌 045
夜宿 047
颐和园 049
旷古的忧伤 051
安妮·塞克斯顿 053
木头 055
艺术家肖像(组诗) 057
给王家新的太平洋明信片 064
雕琢 066
铁锚 067
凡·高的饥饿 069
拍照 072
一百行的雨 073
给子薇的诗 075
今夜我把忧伤藏起 076
向我走来 078
高兴
歌 唱 083
沉 默 084
夏 天 085
雨,或鱼 086
与冬天有关,与冬天无关 087
雨,滴在地上 088
十一月 089
南京,或南浔 091
母亲 093
高 原 095
独白 097
光线 099
你是如此美好…… 101
远处 103
风景背后 105
虚空:哥哥 107
句号 109
记 忆 110
岳阳楼 112
豆豆没了 113
少况
纸盒子 117
秋水堂印象 119
安迪·沃霍尔的四方联 121
循环放映 123
路上的书 125
散句 127
只是你的说明 129
展开,然后是事物的状态 131
被禁止的游戏 133
平行的词 135
疏离之离 137
丑时的折子戏 139
新十四行(三首) 141
突然的中断 144
你确实是知道的 146
另一种告别 148
如何欣赏蒙德里安 150
偶成 152
我们来这里的理由 154
像冬天那样了解我 156
树才
荒诞 161
永远的海子 163
母亲 165
莲花 167
单独者 168
马甸桥 170
怎样的未来 172
过去 174
刀削面 176
虚无也结束不了 179
拆 181
按一下 183
哭不够啊,命运 187
这枯瘦肉身 188
月光 190
钟表停下来的时候 191
妈妈 193
写于斯德哥儿摩 194
此刻 196
然后呢 197
黄康益
忆 201
致—— 203
清明 205
最后的假日 206
玛丽亚 207
过程 209
故乡 211
四合院·春天 213
内相的形成(节选) 214
太极拳 220
旧报纸 222
梦 224
从一个地方出发 226
一分为二 228
今天晚上 231
马德林港 233
真人之息以踵 235
北京 237
留言簿 239
黑子 240
骆家
当心,拐弯的地方总是危险 245
林中,一个寒冷的黄昏 249
黄昏雪 250
心底吟唱的歌不要标点 253
我就变成了自己残缺的阴影 255
雪终于把树压得更低 257
最温柔的不是脚印,是湖面 259
“冬日黎明灰色的窗棂” 260
静物写生 262
没有出口的窗 263
灯光鱼 265
青皮 267
第五个夏天 268
那些死去的时光非亲非故 269
我们都曾有过美好的往日 270
莲(给姐姐) 273
短歌 274
死亡自拍像 276
虚构的破绽 278
南海滨墓园 280
姜山
在暮色中 285
置上 286
万物沉默 288
致巴黎 289
八月巴黎村庄 295
Le Bateau Lavoir 298
云生活 299
当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 300
外滩,二○一四 302
Quarrel with Qiu Tian 304
溺亡者 307
Casta Diva 309
A Long-winded Autumn 311
你认出击中你的一颗子弹 313
Prélude à la nuit 315
纽约时报书评系列(二) 317
Artist of the Void 320
鱼缸 323
二次元 325
时间终于逃不过 326
李金佳
盛夏的废墟 331
楚王 332
巷伯 333
朝鲜津 334
河间 335
铁屋的汉末 336
庞德公 338
草字头 339
扬州 340
关汉卿 341
混乱的信使 343
豪杰 344
冒充者们 346
白马 348
盈满 350
河梁 351
泥屋 352
巨像之谜 353
大方里 354
黄昏的狗 356
编后记 “明亮的捕捞”与被隐匿的 358
序一 巴别塔的儿女
王家新
在中国新诗史上,我最认同的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传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里,这个“诗人群”,无论是“师长一代”(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前辈诗人),还是新锐的“学生一代”(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不仅坚守了“五四”新诗的传统,还以其对“现代性”的锐意追求,把中国新诗推向了一个新的更令人瞩目、也更富有生机的阶段。纵观百年新诗,“西南联大诗人群”不仅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奇观”,而且他们对此后的新诗发展——尤其是自《九叶集》出版以来,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的确,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氛围中推出的《九叶集》(1981),堪称新诗史上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它不仅发现了九位“被埋葬”的优秀诗人,而且将那个年代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艺术成就令人惊异地展现出来。当然,在《九叶集》刚出版的那些年月,人们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那一代诗人的追求和贡献的,而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中国新诗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把他们的翻译包括进来。《九叶集》中的穆旦、陈敬容、郑敏、袁可嘉等人,以及未收入《九叶集》、但同样是西南联大出身的王佐良,不仅是诗人,还都是各有成就的优秀译者。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求索和建设,而且合力塑造了“诗人作为译者”这一“现代传统”。他们富有创造性的译作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和读者,构成了百年新诗最有价值和光彩的一部分,成为留给我们的重要资源和遗产。
我一再感到,这一传统——“诗人作为译者”——的重建,不仅对于诗人们自己的创作十分有益,而且对于继续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也至关重要。
而这一传统的重建,在我看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主要就是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的王佐良先生所推进和承担的。可以说,他堪称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作为一个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诗人,王佐良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完全转向了诗歌翻译和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而在“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早年的爱”,并以其诗人的敏感和责任感,延续和拓展着“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现代性”的追求。他在80年代初期对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美国“新超现实主义”或“深度意象”诗人的发现性译介,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年轻诗人,在诗坛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他后来对奥登等诗人的翻译,则带着他的全部敏感和多年的译诗经验,透出了一种高超的技艺和语言功力,真正体现了如卞之琳先生所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不仅如此,王佐良先生还肩起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对中国新诗“诗人译诗”这一传统进行回顾、总结和阐发。他的诗歌观、翻译观,他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他对语言的特殊关注,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重新塑造,都一再地激励和启迪着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代诗人和译者无不受惠于王佐良先生。
正因为如此,我和许多中国诗人一样,在那时会常常把目光投向“北外”,因为那里有这样一位为我们所高度认同的诗歌前辈和翻译大家。我们不仅关注王佐良先生自己的著译,还关注北外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很多中国诗人都订阅有这份杂志)。我就是在这种“认同感”的作用下,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不仅关注北外的诗歌活动和学生文学社团,也先后认识了像王伟庆(少况)、李笠、树才、金重、高兴、黄康益、骆家、李金佳、姜山等年轻的北外诗人和译者们。
的确,我对他们感到亲近,不仅是因为他们热情,满怀着80年代特有的诗歌理想,还在于他们大都是王佐良先生的学生;不仅在于他们投身于诗歌,还在于在他们身上都“携带着一个译者”。我们在一起可以谈论我们所热爱或感兴趣的那些诗人,如夏尔,如特朗斯特罗姆,如安妮·塞克斯顿。诗人多多当年就很看重王伟庆、金重、树才的翻译,在笔记本上抄满了他们的译作。我自己最愿接近的,也正是这一类诗人兼译者的年轻同道。或者用策兰的一个说法,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从两个杯子喝酒”的人。我难忘和他们在一起日夜谈诗、日夜从两个杯子“畅饮”的那些时光!
也不知为什么,我会经常把诗和诗人与学外语联系在一起,比如穆旦等西南联大那一批年轻诗人,大都是“外语系出身”,卞之琳、冯至、戴望舒,也都是“外语系出身”,台湾地区的一些诗人如余光中、杨牧和后来的陈黎、陈育虹等人,也都是“外语系出身”。我自己曾一再后悔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而不是外语系,那就只得靠“自学”了。我这样讲,并非因为对我们自己的母语“没有感情”,而是正如我翻译的英籍德语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所说:“语言发现它的青春源泉,在另一种语言中。”这些,我自己在阅读、翻译和写作的过程中都一再地体会到了。因此,我一直对外语学院怀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在我看来,比起中文系,那里更有可能成为一个“诗的摇篮”(当然,最好是有王佐良、叶公超这样的老师!王佐良且不说,叶公超当年在清华外语系任教,就带出了卞之琳、赵萝蕤这样的学生诗人译者)。两三年前北外的学生文学社团采访我,我还称他们是“巴别塔的儿女”(这里借用了乔治·斯坦纳的一个说法:“我们的文学是巴别塔的儿女”)。北外,作为一个拥有那么多外语学科的学校,它本来就是一座“诗歌巴别塔”,从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如李笠(瑞典语),树才、李金佳(法语),少况、金重(英语),高兴(罗马尼亚语),骆家(俄语),就是一个例证(其实,从北外出来的诗人译者还有现居澳门的姚风,他学的是葡萄牙语)。而我之所以用“巴别塔的儿女”做这篇序文的题目,也在于其更普遍层面上的意义:所谓“全球化”时代也好,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时代也好,都是穿越巴别塔的时代;在现在,在将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我们也只有在穿越“巴别塔语言变乱”中才能练就一种更敏锐的诗歌听力。
这些年来,虽然王佐良先生早已离去,当年的年轻诗友也已星散,但北外的文脉还在,诗脉还在。我任教的人大和北外挨得很近,我也和北外的李雪涛教授,阿多尼斯、达维什的译者薛庆国教授多有交流。北外聘请著名汉学家、诗人顾彬做了特聘教授后,他在北外也组办了许多诗歌活动(包括去年他组办的“王家新和他的译者们”多语朗诵对话会)。诗人翻译家汪剑钊教授调入北外后,北外的诗歌气氛更浓厚了。我只是希望在北外能再次涌现更多像收入本集的诗人一样的年轻诗人,重现20世纪80年代它曾有的诗歌荣光,或者说,再次成为一座“诗歌巴别塔”!
就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他们中的不少都以翻译和创作成名,如李笠、树才、高兴等,在诗坛和译坛都有着广泛影响;有的仍在“潜行”,但已展现出他们的潜力;有的厚积薄发,如骆家,近年的诗和翻译都让人乐见;有的远离故国,但仍孜孜于诗,和他的缪斯守在一起,如美国圣地亚哥“幸存者村庄”里的金重。这些年,北大、复旦和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诗友校友,都纷纷打出了各自诗派的招牌,或是出版有各种校园诗选。我也衷心希望已分散在各地的“北外诗人”们能重新聚集起来,因此在与他们聚会时提出了出书的建议。我倒没有直接称呼他们为“新九叶诗人”,只是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在我看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无论从文脉上看,还是从他们的写作本身所体现的独立、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视野和精神上看,他们也都有充分的条件赓续“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个传统——当然,传统的赓续、拓展和刷新不单是靠哪几个人,而是靠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那就让我们都为之努力吧。
七八年前,我曾写有一文,专门介绍和评论王佐良先生翻译的洛厄尔的《渔网》一诗。它并未收在王佐良先生的译著中,我只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见到。但是,仅仅这一首译诗,已足以让人难忘了。它不仅展现了洛厄尔的优异诗质,也透出了王佐良先生自己的敏锐眼光和精湛、高超的翻译诗艺。读他这首极富创造性的译作,并对照原文,我不能不惊异译诗艺术已被推向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因为骆家在其《编后记》中全文引用了该译文,我就不再引用了。我最后想说的是:王佐良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的这首译作,几乎也就是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光辉写照。他们满怀着理想和责任,把自己献给“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在写诗和译诗中度过了一生。他们也许“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但他们撒下的渔网并没有落空。他们不仅给中国新诗和语言文化做出了最可宝贵的奉献,他们也带出了、滋养了新的一代(这本《新九叶集》就是证明)。他们留下的遗产,正如那磨损的挂在墙上的渔网,难以辨认而又令人起敬。它已被牢牢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之上。实际上,它也不需要别的“未来”;它自身就在昭示着一种语言和诗歌的光辉的未来。
2017.9.29 人大林园
序二
我这根火柴成了灰,
点燃的诗灯却长明
——致敬神奇的20世纪80年代
张桦
这事儿很有些神奇,本身就像一首诗。
九个相差十二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男生,既不同系,又不同级——相隔十一个年级:79级—90级——却因为诗歌而相识相知,走到一起。
毕业后他们凭借自己学到的语言技能,走进不同的世界。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如法语83级的树才,分到国家进出口公司当项目经理,号称挣钱多得发傻,可就这么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几年后却被他换成了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坐冷板凳,只因他想写诗,译诗,研究诗。不仅他,其他八位,二十多年来也都大同小异,他们最终被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王家新教授发现提携,仿效20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的“九叶诗派”命名为“新九叶”。
“新九叶”诗作合集要付梓了,辗转找到我,称我为“老师”,令我惭愧不已。他们记得我,按说原因很简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确实当过北外的老师,鼓动同学们成立了“尝试”文学社,当顾问,出期刊,请作家们来校讲座,向报刊推荐学生习作——居然在一年多时间里,从《人民文学》到《北京晚报》,发表了上百篇作品。一时间,人们刮目相看:北外文学社兵强马壮,风风火火,而“新九叶”中好几位正是当年文学社的骨干。
但是不简单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这根据说点燃了他们心中爝火的火柴,早已在碌碌无为中成了灰,他们这九盏诗灯却依然闪烁在文学星空,照亮并温暖着我已不年轻的心。
为什么会如此?他们有什么魔法,从青葱年华倏忽间穿越到了今天,出现在我面前,依然是九茎新绿、九缕清光、九瓣心香?
探究这神奇的原因,我首先想到,必须要归结于那个神奇的年代。
是的,我说的就是80年代。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远没有当今人的钱包满满,但是人人幸福满满希望满满信心满满。我记得,我请过几十位作家到北外来给文学社做讲座,他们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天下谁人不识君”,各种各样桂冠戴了一脑袋,但已在文坛上才华逼人、声名鹊起。请陈建功时,他说,要么车接车送,要么就什么别管,结果是他自己骑车来了,我唯一的款待,是在筒子楼烟熏火燎的走廊里,为他准备了三个菜的“感谢宴”。到请莫言时,连这顿饭都免了,我只负责到公共汽车站接送。请北岛时,原来安排的三百人的大教室突然变得拥挤不堪,临时改到一千二百多人的大礼堂依然座无虚席。请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两个作家班来校座谈时,就更富戏剧性了,我只对两位班长说:人人都说北外女生漂亮,你们不想见识见识吗?——这擦了“色诱”的边吧!二十多位得过全国文学奖的名作家结队走进北外,这事儿,甚至惊动了北外当时的院长王福祥,他马上命令学校招待所开席三桌,全程亲自作陪,给了我和文学社一个很大的面子。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我记得,我夹着一叠一叠的学生习作,去过很多报刊编辑部。我这个“推销员”与编辑们并无深交,最多只是一支烟一杯水的交情,而且往往是他们递给我。可我从未受过冷眼怠慢,这些青涩却纯真的作品得到他们的青睐,后来还有刊物定期上门来征稿。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我记得,文学社自办的是双月刊,每次临近出刊,都是十几位同学到学生会搬来大捆的新闻纸,架起油印机(“90后”们肯定没见过那种老古董),贴上熬夜刻好的蜡纸,抄起油滚子,一页一滚地让习作呱呱坠地,每次最少要印三百份——文学社有三百个社员,现如今到哪儿去寻找如此庞大的文学社团(多年后我惊异地发现一位女生仅仅因为一位文学社男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就嫁给了他,禁不住问其感受,她淡淡回我:上当受骗了呗)。
很多年来我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神奇,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上,余韵绵长!尤其是在我商海挣扎游泳的艰辛过程中,那些有形无形的帮助和鼓励,支撑我全身而退,否则我不是呛水溺亡,就是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当我对老友高伐林(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谈起“新九叶”这个神奇的故事,并将奥秘归之于那个神奇的年代时,这位老友却没有轻易苟同我的看法:归功于80年代?我们都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啊,除了“90后”“00后”这些晚出生者,谁没有经历过80年代?为什么大多数人如你所说“碌碌无为”甚至火柴燃尽,却没有“新九叶”这样的坚守、这样的追求?
这让我陷入沉思。是啊,80年代那种百废待兴、狂飙突进的氛围,无疑熏陶、激励了包括“新九叶”在内的所有人。但是后来呢,三十多年,大家都经历了时代的颠簸、生活的磕碰,“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语),而他们却不改初衷。更深刻的原因,恐怕还得要从他们灵魂深处寻找:他们内心本就蕴藏了这样的能量、具备了这样的潜力,才能在80年代被一支火柴点燃之后,与那个年代呼应共振;而且在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之后,他们仍然能激情燃烧,长明至今。
但我还是要致敬80年代。“新九叶”是80年代孕育的骄子,他们也是构成80年代的杰出一员(不,九员),他们更是、更应该是我们民族超越80年代、贯串于所有时代的宝贵元素和精神结晶!
“新九叶”的诗歌造诣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要说,读这些诗,让我回到了那个神奇的年代,让我惊悟那种纯洁的感受和沉静的思索,与当今世间的浮躁、喧嚣,形成何等巨大的落差;让我重新唤醒并梳理许多已经麻木的思绪,关于母亲、爱人、孩子、理想……“新九叶”这个群体,三十年前他们是我的学生,而今天,我向他们学习。对这九片在阳光下绿油油的诗叶,我衷心地祝愿他们继续跋涉在诗的路上。
2017.8 纽约近郊家中
序三 自由的困境
——《新九叶集》序
高 尚
命名:“新九叶”
伟庆来兰州出差与我小聚时,谈及骆家、金重受诸位诗友之托,主编一本北外当代诗人诗选,且名字也已经取好:《新九叶集》。这令我瞬间开心!因其中大多诗人(包括伟庆本人)都是故交,且多为我所熟悉和喜欢的翻译家。我俩立刻电话联系到多年未见的朋友骆家,向他在南方的炎热酷暑中挥汗编书致敬,我同时表明希望自己是这本诗集的第一个读者。骆家仁厚,热诚地允诺了。
“新九叶”这名字,细思十分诡异,一定出自一个吊诡的头脑。经向树才、伟庆、骆家诸友求证,始知它的议定与命名与王家新兄有关。他去美国顺道到金重那儿,俩人在小聚闲聊中,这一诗集选题连同它的名字便无中生有了。想想时下生态,深感此举已足具《过故人庄》式的超拔清新了。
说“新九叶”这名字诡异,是因这“新”会强烈引发对“旧”的联想和记忆,其间弥散着一层走光的暧昧。说它“走光”,是因为这暧昧中油然升起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九叶诗人”。
“九叶诗人”中,我有幸认识唐祈和袁可嘉二位前辈。1979年,我刚进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大)校园,唐祈先生作为在校老师,不问出处也不加区别地为一批热爱诗歌的学子办起了诗歌讲堂。他用一本本即时油印成册、散发浓郁油墨气息的汉译西方现代派诗歌做教材,用庞德、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叶芝、布勒东、艾吕雅给大家做诗歌启蒙,其间偶尔辅之以他所亲历的中国现代诗歌。他是一位文气、儒雅的诗人,又是一位热忱、执着的诗歌教父。我时常会这样想:那个时代,在大学这块园子里,每个爱诗的学子最当得遇的,当是唐祈这样的先生。
1988年初至1989年底,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修习文化人类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期间,因兼在外国文学所图书馆做勤杂,又得遇袁可嘉先生。当他得知我是唐祈先生学生时,颇有几分愉悦;再当我告知他当年唐先生给我们讲叶芝那几首名作,采用的均是他的译文时,他边用手摸着自己头发稀疏、熠熠生辉的脑门,边爽声哈哈大笑,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他告诉我,他对叶芝那几首名诗的翻译,严格说来还没有彻底竣工,总是隔些年月会根据语感和气息重新调整其中一些语词,因此在不同版本里对同一首诗的翻译会有不同之处。
九叶中的两叶。这就是诗人。那暖意,那性情,虽已阴阳两隔多年,于今却仍然清晰可感、明白如话,是毋需翻译的。
会两种以上语言的人,灵魂具有两种以上颜色。他们用母语求爱时灵魂通常呈浅灰色;反之当他们用非母语求爱,灵魂则显示为青紫色。进厨房取水我突然想到这一点。
至于“新九叶”,我与其中几位就算不青梅,也比较竹马。他们不仅是诗人,且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重要的翻译家。今天,当我们谈论北欧诗歌——譬如索德格朗、特朗斯特罗姆时,就不能不谈到李笠的贡献;当我们表达对东欧文学——譬如布拉加、索莱斯库等人——的敬意时,就不能不同时向高兴致敬;金重是最早给我们带来布罗茨基诗歌汉语面孔的译者,同时又择优向国外译介中国诗人;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汉语中被勒韦尔迪的超现实具象和勒内·夏尔的神秘意象所击穿,那最初一击很可能来自树才;王伟庆对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和布朗蒂甘《在西瓜糖里》等后现代佳篇的翻译,常令我有拍案惊奇之感;骆家在译介俄罗斯新生代诗人之余,近期又倾力推出格鲁吉亚诗人塔比泽的《奥尔皮里的秋天》……率先列举这几位,是因为除李笠、金重,我与其中好几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相濡以文学和诗歌了。
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诗人汪剑钊戏称“译诗是一次冒险的恋爱”。其中险情,恐怕就来自于两者身心的契合度。我深信,那些优秀/伟大作者的作品和它的译者之间,在精神和心灵上有种神秘乃至宿命的呼应。一个译者和一个作者及其作品之间,或一个作者及其作品和他的译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相遇、发现这类陈词滥调的关系,无论其缘起为何,终是一种前定,是和一种命运赴约。由此,我恍然觉得自己和数位新旧“九叶”诗人之间,不是相遇,更不是相识,而是重逢。
在成都,壹都锦公寓虽然称得上舒适,可一出门就立刻被阵阵热浪裹严。下午去武侯祠。豁然顿悟:蜀国是被热死的。
这些王朝的可怜虫运筹帷幄,却挂一漏万,让帝都坐落在炎热上。
新旧“九叶”:新诗的译和写
细究起来,新旧“九叶”两者之间还确能抽绎出两项显著共性:都是诗人,大都有诗歌翻译。汉语对世界诗歌的翻译,深嵌于汉语新诗百年的历史肌体之中。你可以尽情延展现代汉语对世界诗歌翻译的想象边界,但你不能想象没有翻译诗歌的汉语新诗百年史。大多时候,这二者在发生学上是重合的。写下现代汉语最初重要诗行的手,也是翻译世界之诗的手。新诗发端之初的那些重要诗人,胡适、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徐志摩等等,莫不如此。
但他们的诗歌,又无一例外地存有对自己所译诗歌的临摹/模仿。显著的例子,像戴望舒那些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如《雨巷》《我的记忆》等,便充满了对魏尔伦、波德莱尔、耶麦(今译雅姆)的临摹与仿写。这一临摹/模仿本身又进而被二度、三度临摹/模仿,由此构成了今日汉诗的前史——中国现代诗歌史。
我毋需暗示汉语新诗在独创/创造性上存在缺陷——这本是事实——而是着眼于它与生俱来的与翻译诗歌无法割裂的关系。从新诗发生到今天,它似乎宿命地与翻译诗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胞生关系,在自身历史中,它实际上表现为一个主体虚弱的殖民化陈述,而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语言共和国。
“白话”新诗:历史的断裂和“拿来”的过剩
从汉语新诗诞生/发育角度看,翻译诗歌/文学的确赋予了一种它不曾具备的气质、不曾经验的经验。然而,在今天,如果气定神闲地观望其百岁之躯,会发现有两道伤口赫然显现——历史的断裂和“拿来”的过剩。
在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过度的那一瞬,当所有既定的书写与表达体系突然开始了它的转型与转向,汉语诗歌在此形成了它与历史的骤然断裂。我坚信汉诗由此经历了它史无前例的虚脱和休克。当它再度言说,已是汉诗在言说/表达经验意义上一片空白的白话/现代文。这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历史积累的爆发,更不是某种后果,而是断裂。它就是断裂本身,是对白话文的当下需求带来的一个断裂,这种需求并不考虑诗歌/文学的命运,而着眼于整个当下史的即时性命运。只有当新文化运动从一个思想/精神事件成为一个已然的历史事实时,新诗/新文学的头几个分行才被战战兢兢地写下。
新诗的生成,本应是那个从作为即将来临之存在的存在,成为本有;但它却无可奈何地成为异己的存在。应该说,历史给了汉语诗人一个自唐宋以后可救汉诗于不振的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但在那一刻,几乎所有的汉语诗人瞬间便陷入了无法被指认和识辨的集体“无名”状,瞬间成为这个世界上荒谬的存在者。他们显然既没有准备好如何成为一个新诗人,更没有能力发明或生成一个新的自我。然而关于这一点,也许已经是某种“基因学”的课题了。
假设草草地写下也算是永恒,那么时至今日,这一书写本身已沉积为新诗自身一派狼藉的历史。但这一历史和整个汉语诗歌史在概念、定义、形式等诸多端面上,呈现异质不能同构状,这使得汉语新诗在语言形式意义上——而这正是全部人类诗歌是其所是的本质——几乎失去了所有可被指称的构件要素。换句话说,汉语新诗事实上并不真正拥有“诗歌”这一名字。这正是历史断裂给汉语诗歌带来的深度创伤性事实,即使已历时百年,我们也仍然未能将它修复。
从成都回来,兰州温度居然比成都高4℃。擦,真是温度界的奇葩。
另一方面,对西方/国外诗歌的翻译,在汉语新诗的形成过程中,又总是给人带来关于“拿来”的观想。这一观想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引发的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思维危机,非常值得关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百年之间,大多数中国诗人对“拿来”所采取的基本是膜拜、顺从态度。但荒谬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汉诗“拿来”这一主宾/受施关系中,随着宾格“拿来”的东西愈多,主格“我们”却愈来愈少了!或者说,这一受施关系始终处在一种失衡、倒置的结构中,彰显出一种结构性的“拿来”过剩。汉语新诗对拿来、接受与完成、输出这一受施关系缺乏配平能力,始终居于弱势。这一状况至今也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它被大量给予性的成分,要比在母语环境下自我生成/创造的成分多得多,形成显而易见的殖民/自殖民处境。多年以后,汉诗语言“翻译体”的滥觞,汉语诗人对西方/国外诗歌方式的过度倚重和仿写,对汉语/母语诗歌实验/书写难度的回避,都无不印证着这一判断。德国汉学家、诗人、当代中国汉语诗歌重要的德语翻译者顾彬,当他在十多年前直言中国当代文学为“垃圾”时——虽然他又在相对意义上以略好于小说的说法安慰了当代汉诗——这一他者视角也映现了这一主格弱化的情势。
当我们试图从汉语/母语立场来看待新诗这一形式,包括它的独创性乃至对它进行某种影响研究时,相较于汉语古典诗歌,会发现一种汉语表达的主体性弱化。说到底,汉语新诗事实上正日益承受着这一伤害,同时伤及的还有作为汉语诗人的自尊——假如他需要持有母语立场的话。
这是深渊性的汉诗之夜,当代汉诗也因此深陷于“无我”的黑暗之中。这使汉语诗歌在文化创造、文化选择、身份选择以及母语立场等各种向度中溃退了。“拿来”的要旨本是举起他者的诗歌之光,使汉语新诗得度当下的即时性黑暗;如果它是光,那“拿来”一定是点燃/点亮,最终使让汉语诗歌发出自身的光芒,而不是相反:令母语在他者的光芒中眩晕,使自身处于永久的黑暗;更不是为了消除自身之黑,连主体也一并消除掉。
嘿,MU6221次航班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农用拖拉机,正浑身颠簸着从上海至兰州的夜空中穿越云层。我抓紧在一只餐盒纸盖上写下上面这段文字。
当然,当一个汉语诗人保持一个置身于世界的姿势时,他需要这一基于汉语/母语立场的观察和期待。
这不能不让人回忆起鲁迅。当是之时,他提出了对“拿来”的两条规避性原则,一条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另一条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假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在场者,他所提供的这两条原则具有某种当下针对性,那么,纵观汉语新诗这百年的两端——它在漫长的中时段上再度陷入了虚脱和荒诞——我们会证得这样一个事实:它的“采用外国良规”,在体量上远胜于“择取中国遗产”,二者之间也并不构成等量/对等关系,而是一种畸形的单边扩张。这也许是自信丧失的表征,也许是“择取”本国遗产难度更大!我们被打开的世界刺激出过度的对世界的欲求/渴望,但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应该作为完整/自足主体的“我们”,事实上只是影子般的存在。这是否是因“拿来”太多但自我创造匮乏所导致的“诗”之罪呢?
“拿来”所表征的,正是一种无力达成、不能自足、主体贫弱的书写境遇。这一境遇中,它意味着拯救和超度。但这需要主体拥有把握“良机”的能力,拥有对自身的虔诚,对母语的信念、觉悟,在自身困境中起义。
当代汉语诗歌:没有定义就是它的定义
上承白话文新诗,当代汉语诗歌已是一种覆水难收的语言形式。它虽然沉积为百年历史,但始终未能解决诗学第一问题:什么是诗歌?
当代汉诗已经站在这一事实面前:在“拿来主义”背景下,它实际上已经从诸多元素、定义中彻底逸出了汉语诗歌史,成为陌生的存在者。你可以继续称之为“诗歌”,但它与汉语两千多年来所言说的“诗歌”,从特征、元素和定义等方面已几无可相认之处。也就是说,汉语诗歌史两千多年来对于诗歌的定义、认知,在形式上已无一可适用于当代汉诗。
可在此之前,尽管往世诗歌也曾经历巨大的形式变革,例如从诗经到乐府和楚辞、再到近体诗和唐律诗、再到宋词和元曲——但无论其形式如何演变,每一变革中却始终积淀了在源头即已形成和可识辨的诗之为诗的基本构成要素,譬如韵律、格律以及节奏,包括后世所谓诗歌的“音乐性”。而在当代汉诗中,这种一眼即可识辨的诗歌形式元素、特性已经荡然无存,以致当一些诗人偶尔忆及并谈论格律、节奏和韵律这类关涉诗歌形式主体的元素时,总是伴随着一种荒谬感。
正因为如此,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汉诗写作,可视为人类诗歌史上一种罕见的、最无边界的诗歌实验。如果说新诗伊始,它还试图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语言转变中持存/传承汉语诗歌源头、诗歌史所形成、积淀的那些诗歌要素——譬如胡适、闻一多在创作中所做的努力,那么到了当下,它早已模糊甚至消除了不同文体间的界限,在很多诗歌中,“诗文分野”不复存在。这不禁令人回想起白话诗肇始之时,俞平伯先生曾貌似淡然地指出的:“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还是有的。”然而今天,已有为数甚众的汉语诗人,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成功爬过“诗”和“话”之间那堵高高耸立的墙,安处一隅,尽情于无难度的“白话”盛宴了。
同样,在当代整个文化/文学/诗歌场域中,对“诗歌”的定义也始终依托于种种单面、单向的表达,因为你所能见到的任何一种关于诗歌的定义,无论多么精辟、深刻,都面临着无法还原的窘境:任何一种定义的给予和特征的提取,都无法成为它(诗歌)的自足项,因为它总是荒谬地同时适用并涣散于其他非诗关系。这正如我们今天辨认一首诗是否是诗歌,唯一不争的形式依据,似乎十分难堪、窘迫地只剩下“分行”了。但是,若反向地对许多诗歌文本加以不分行实验,便可得知:在不分行条件下,这些文本与非诗歌文本毫无二致;而“分行”这一机械性,并不构成诗歌是其所是、有别于其他文本形式的形式要素。这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能还原的风险,因为你绝对不能说只要对任何一种文本进行分行(而这也正是一些当代诗人赖以存在的法宝),便是诗歌。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新诗之前的中国古典诗歌,反而是毋庸刻意分行而诗行自现的——任何读者凭借对诗歌形式的认知,即可迅速断得一首往世之诗或同代诗作的诗行。这即是说,当代汉语诗歌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不能分行、难以分行,或在形式上濒临解体的状况。在诗歌中,很多诗人要么不能用母语的样子言说事物和自己,要么不具备以可定义、可指称的汉语诗歌的方式为人和事物赋形的能力。也许有诗人会像通常所见那样,说不是其中还有“诗意”吗?OK!诗意同样不能构成表达诗歌形式的自足项,很多非诗的自在存在一样可以具备“诗意”,但是在诗歌为它们赋形之前,它们也还仅仅是事物自体,而不是诗歌本尊。
深夜。上海闵行区吴泾。一道炫目闪电,接着一声巨雷,在窗前断然炸裂。楼下、街边的车辆报警器顿时此起彼伏,尖叫起来。顿感莫名惊恐:雷,果然是震卦。我裸身写稿,这会儿从电脑旁起身,离开。暴雨像簇簇利箭,朝大地倾射。
这炸雷、闪电和雨箭,已深深揳进了这页文字。冒着泡的雨水,正在各行距间哗哗漫流。
今天的汉语“诗歌”,是一个不具自足内涵的概念,很明显,要理解它的内涵,需要不断从其外部进行给予/输入,因此具有一种显著的寄生性和依附性形态;很大程度上,它也丧失了在自身历史中形成的形式感和新的赋形能力。这便凸显出这样一幅危机图景:我们可以真诚而又雄辩地谈论诗歌,但关于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却是缺席的。与此相应,当代那些汗牛充栋的中西诗学研究、诗歌理论、诗歌课题……在这一处境中也是瞬间苍白,形同虚设。戏仿美国当代作家卡佛一个短篇标题来表达,即“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我们(究竟)在谈论着什么?”这表明:新诗以来的汉语诗歌,是一种最悬疑的诗歌存在。仿佛出自一种幽暗的集体无意识,诗人们正在倾其全力,心照不宣地制造着一种巨大的文字事实,但不知道如何指称它。
也许没有定义就是它的定义,没有形式便是它的形式。
自由的困境
这一切征候,都指向一种诗学困境。更深刻的困境,还包括由此而引发的诗人的困境:“诗人”这一称谓事实上已经被这一诗歌定义/内涵的缺席所彻底悬置,只是更多诗人在自我的语言劳作/狂欢中并不自知,或聊以自慰而已。
我们当然记得,当新诗借新文化运动之力从文言诗歌中挣脱而出时,它响亮的诉求之一,便是自由:自由抒发,自由表达。它为此冲破重重藩篱,且赢得了另一个名字:自由诗。如今,它新生时的种种阻力和羁绊早已消除,它如愿以偿,而且在形式意义上已达“无边的自由”。
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从新诗到当代汉诗为“无边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无边”意味着本体概念性的无内涵,莫可名状。诗人可以写诗,但没有能力叫出诗歌的名字,因此在事实层面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定义/界定诗歌的能力。
自由植根于否定:否定一切异己、异质的存在,甚至包括否定自我。它使“否定一切”合法化,至少披着合法的外衣。“自由诗”在寻求其合法性时屏蔽了两个重大危机:首先是诗人在瞬间成为母语诗歌、母语表达方式的孤儿,彻底出离于汉语诗歌传统,在古典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白话文表达方式的断裂处,成为语言的分裂症患者,在语言表达中丧失了可辨认的自足的自我,也使新诗运动发轫之时,大量的汉语诗人彻底丧失了诗歌能力(即使在白话诗/新诗初期几乎所有的作品中,这种分裂也完整地存留于其中)。这一分裂源于传统表达的彻底缺席,也只有凭借传统的在场才能有效治愈。其次对于两千多年的传统诗歌而言,新诗的发生并非是艺术、文化意义上的创生,而更像是一场末日审判,一个暴力性的终止。但在它行使对传统的审判时,应该觉悟到自身也将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可能也将面临同样的审判。我们不禁会问:新诗(或每一个现代汉语诗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无期许或渴望?如果有,会不会是一个暴力性的终止?
愈往后,“自由”带来的这种危机性后果便愈加彰显。当我们意欲完整地表述、定义汉语/母语诗歌时,我们事实上已经陷入了主体性的分裂;一个自觉意义上的当代汉语诗人,如果站在母语诗学立场发言,那么他必定会在传统、现在、东方、西方、自我、他者等诸多概念意指中失重、眩晕。
缘于此境,在当代中国,谈论诗歌实际上是件捕风捉影之事。这是个人人皆知的概念的幻影,它在广漠的汉语中穿行来去,浮游无根。作为一个共知概念,它并没有可以抽绎、通约的内涵之根。如果引入一种有效的方法论,譬如当代法国哲人巴迪欧所倡导的数元“集空”思维来解析它,便无法通约出一种主体形式的存有,它只是一个“溢出”,是一个使诗歌消散的“事件”,因为其主体早已被“自由”溺毙。
诗人,请说出诗歌的名字
只要历史还将继续,诗人的写作也将继续。已经一百年了。今天,该到诗人说出诗歌名字的时候了。谁能道出她的芳名,谁就和她心心相印。这是天赋诗人的权力。诗人需要调动自己的认知、理解、想象甚至直觉,在对汉语诗歌前史的澄明中,缀合百年之间可见的残片,给当下“诗歌”这一概念注入/输入新的内涵,还汉语新诗一个定义,一个可识辨的概念,让创造意志不断构建、解构、重构它。否则,当代汉语诗歌在认知、逻辑上始终呈塌陷、无名状,不能自立其身。作为形式艺术,它最终会自噬、消弭于自身之中,尤其当它自身也终归会成为汉语诗歌历史与传统的一部分时,情形更是如此。
这需要清晰的觉悟。汉语诗歌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任何对于诗歌一劳永逸的定义必定是愚蠢的——《诗经》便不能永久定义唐诗宋词——但没有定义的诗歌更加愚蠢。无概念、无定义的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的只是习惯而不是创造;而真正的创造则需要一个坚实有效的逻辑起点。如何定义汉语新诗,已作为当代汉语诗歌的第一问题,摆在诗人面前。如果不能要求一个汉语诗人在实验性的晦暗地带为汉诗寻找到某种新的形式可能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要求他认识诗歌,书写自己认识的诗歌。
和才旺瑙乳约好见面的时间到了。
在一个拥有丰厚诗歌遗产的国度,汉语诗人有能力和定力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诗歌。诗人的基本角色之一,是“诗歌”这一概念意指的真正拯救者和解放者。中国当代汉诗作为最悬疑的诗歌存在,在这个“拿来过剩”的时代,最终能够让它在母语文化中落地生根的,必是具有人类诗歌视野的汉语诗人无疑。
2017.9.16 成都—兰州—上海
2017.11.15 改于兰州金地
我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在我看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无论从文脉上看,还是从他们的写作本身所体现的独立、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视野和精神上看,他们也都有充分的条件赓续“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个传统。当然,传统的赓续、拓展和刷新不单是靠哪几个人,而是靠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那就让我们都为之努力吧。——王家新(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九叶”是80年代孕育的骄子,他们也是构成80年代的杰出一员(不,九员),他们更是、更应该是我们民族**80年代、贯串于所有时代的宝贵元素和精神结晶! ——张桦(作家、诗人)
我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
在我看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无论从文脉上看,还是从他们的写作本身所体现的独立、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视野和精神上看,他们也都有充分的条件赓续“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个传统——当然,传统的赓续、拓展和刷新不单是靠哪几个人,而是靠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那就让我们都为之努力吧。
——王家新(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九叶”是80年代孕育的骄子,他们也是构成80年代的杰出一员(不,九员),他们更是、更应该是我们民族超越80年代、贯串于所有时代的宝贵元素和精神结晶!
——张桦(作家、诗人)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