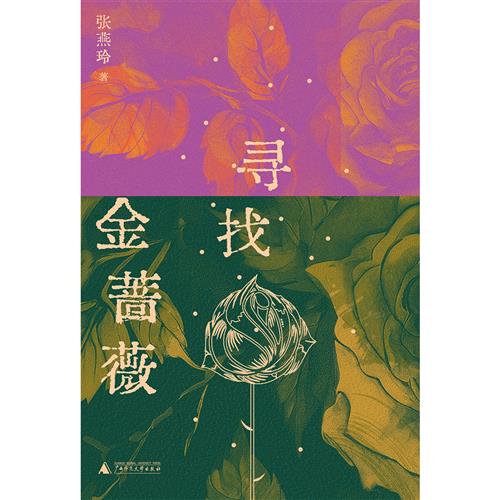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9-01
定 价:65.00
作 者:张燕玲 著
责 编:梁文春,黎金飞
图书分类: 文学理论
读者对象: 文学爱好者
上架建议: 文学/文学理论
开本: 32
字数: 380 (千字)
页数: 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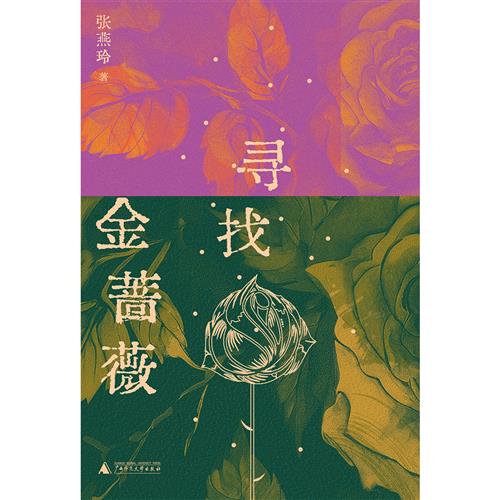
本书是著名文学批评家张燕玲的批评文章结集,全书以敏锐的学术洞察与开阔的理论视野,勾勒出当代文学批评的生动图景。 本书共分四辑:“白心读札”聚焦作家作品,深入陈建功、东西、陈彦、钟求是、雷平阳、蔡崇达等作家的文本,呈现作者立足文学现场的解读;“寻找金蔷薇”则为作者的理论探索,探讨文学的当代意义,探讨“新南方写作”的多样可能;“玫瑰花开”发出女性写作的独特声音,关注林白、蔡东、迟子建、叶弥、潘向黎、黄咏梅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地缘文象”则从地方性叙事出发,剖析广西、广东、浙江等地丰富多元的文学地理。
张燕玲,著名文艺评论家,编审。现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西文联原副主席、《南方文坛》杂志原主编。系广西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和散文创作,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百余万字,一批作品入选年度排行榜。出版论著《有我之境》《批评的本色》《玛拉沁夫论》等5部、散文集《淡妆与浓抹》《好水如风》《此岸彼岸》等5部;主编有《南方批评书系》《我的批评观》等30余部。著述曾获中国女性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丁玲文学奖、欧阳山文学奖、“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一辑 ·白心读札
3 谁解这嬉笑下的悲欣
—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读札
18 不断破界的理想主义者
—关于钟求是的文学创作
34 人生的光影与人性的回响
—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
42 以人间喜剧为时代立传
—陈彦的《喜剧》及其“舞台三部曲”
48 所有人的家乡与硬币的两面
—蔡崇达的《草民》及其“故乡三部曲”
59 广阔的多样性与深刻的当代性
—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为例
67 新乡土叙事之新
—凡一平的《四季书》及其上岭村系列
76 为劳动精神“戴花”
—水运宪《戴花》小札
80 写鸟界,更是写人类
—光盘《傍晚的告别》及其南方写作
87 艺术触觉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疯长—顾骨的青春书写
96 人神世界的别样文本
—关于雷平阳的《乌蒙山记》
102 以自己的腔调,书写人间消息—李约热近期作品读札
114 历史缝隙间的家国情怀
—读赵本夫的长篇新著《天漏邑》
119 以修身来修文 以修文来修身
—关于李修文的《山河袈裟》
二辑 ·寻找金蔷薇
127 “新南方写作”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136 文艺评论如何面对智能时代的挑战
140 新乡土叙事的返乡者形象
152 新南方写作: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一个新的生长点
159 讲真话,更要讲道理
163 建构儿童文学更丰富的可能
168 共同抒写璀璨的民族画卷
171 文论期刊的时代表达
179 寻找文学的立足点
186 建构日益丰富阔达的文学批评格局—近年文学批评的一种观察
191 文艺批评与剜烂苹果及苹果之关系
198 文学批评三人行
207 文学史视野的批评向度—谈谈刘杨
211 公元 1999
—怀念张钧
215 一棵精神之树
218 今日批评家 20 年
225 《南方文坛》与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
241 寻找《金蔷薇》
三辑·玫瑰花开
249 女性写作: 冲突与和解
258 女性的自我和解与相互和解
—关于蔡东的近年写作
264 一次抒情变奏
—重读迟子建的《零作坊》
270 偏偏喜欢你: 人与文的人间烟火—黄咏梅印象
278 《烟霞里》:以普通人的历史见证时代变迁
282 在漫游中狂想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
288 《神圣的婚姻》:徐坤声音的肖像
292 虚实之间
—以梁鸿的《神圣家族》为例
298 向阳而生:城乡现实中的女性之光
—陶丽群新作《正午》及其他
306 苗寨女孩的五彩世界
—王勇英的《蓝靛布 花衣裳》《蓝花山 白森林》
314 片面的深刻
—阎真长篇小说《因为女人》的性别悲剧
320 穿心而过,女性的疼痛
—读潘向黎的长篇小说《穿心莲》
325 李欣伦的《重绘劳动者的身影》
328 静水深流
—范小青的短篇小说
332 女性的精神牧场
—梅卓的中短篇小说集《麝香之爱》
338 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
—读旧海棠作品有感
346 玫瑰花开
—广西女作家札记
四辑·地缘文象
357 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
—关于近期广西长篇小说的一种描述
371 地缘气质与文脉新质
—以《江南》讨论“文学新浙派”为中心
380 南方的文学想象
—以广西及西南部分作品为坐标
396 在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寻求文学个性
—朱山坡新书《萨赫勒荒原》及其创作
403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南方文学想象
—关于陈崇正的《美人城手记》
410 为百年广西文学写真、审美与铭史
—关于《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 1919— 2019 》
417 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深圳维度
422 广西文学经典化的新收获
— 《对话桂西南文学》出版随评
426 淡妆与浓抹
—关于浙江青年文学的一种描述
436 文学桂军的一种释读
446 充满时代感与丰富性的新的文学板块
—对世纪之交广东文学的一种解读
453 海南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463 山里山外
— 《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468 风生水起
—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482 从“鬼门关”出发
—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
491 这方水土
—广西签约作家作品札记
501 南方的果实
附 录
511 素履而行
—文学评论家张燕玲访谈录
528 后 记
无
在张燕玲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和知识女性的那种对于天下、对于艺术等各方面的情怀。
——施战军
张燕玲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样是出色的,她的散文和批评文字会让人过目难忘。她的文笔精细,对事物有特殊的敏感,总是写出人物的内心,写出一种生活的撕裂感,写出自己诚挚的情感世界。
——陈晓明
张燕玲如果不办刊物,她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觉得她即便是业余时间写的散文都是非常漂亮的,文笔非常好。
——王彬彬
张燕玲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开放的理论视野和独特的批评风格,在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中形成了鲜明特色。
谁解这嬉笑下的悲欣—《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读札
我们对作家陈建功的期待实在太久了,尽管时见其随笔短章,但他的小说却一直在许多读者的期盼中。熟悉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读者,无不熟知和深爱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以及广获好评的中篇小说《鬈毛》 《找乐》和《前科》等。至今,与小说界暌违近三十年的陈建功携长篇非虚构小说《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归来。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 是罕见的素朴与粗犷, 却又以内敛与苍凉, 抒写了属于一个荒诞时代的郁闷与探求。作家时而回望时而沉浸, 把十八岁至二十八岁的青春走窑生活、情感历程、心路沧桑展示于我们面前。在作家笔下,我们读出了鲜活深刻的人物群像与个人面孔、时代变迁与社会缩影、人性写真与人生感喟。作家把这悲怆悲凉深沉地隐入其底层叙事里,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风,那种含泪之笑的悲欣悲悯,那种从蓬蒿中生长的草根人间与山河沧桑,令人不断被震撼和感动。这部“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语)的赤诚之作, 如此扎实、真切和优秀,必将给当下文坛注入文学活力,为 2025 年的中国文学带
一辑 · 白心读札 ‖ 3
来冲击和启迪。
初读《我们脏的时候》(《北京文学》 2024 年第 6 期),题目之刺眼,令人耳目震惊,更重重冲击着习惯于岁月静好的我们,急切翻开扉页,文前所引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戏剧版中的名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瞬间击中心灵,我隐隐就觉出了沉郁与悲凉。倘若再深入读解其出处, 即“可怜虫”列比亚德金的全句—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干净的时候, 倒无需关注, 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 是人皆赐爱的。”便豁然开悟,陈建功是要以个人化之笔触,展示沉甸甸的时代心象,追寻苍莽的历史回响,或沉潜或闪动于其文的嬉笑与哀伤、沉郁与犀利、自嘲与自省、反讽与悲怆, 这些就不只属于陈建功本人了,而明明与所有曾经或多或少“脏”过的我们有关,与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有关。而今《花城》首发的, 是《我们脏的时候》的下部,为了更切合“结尾”陈建功所说“其实我是如此地爱他们”,以及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惨烈遭遇心怀悲悯、切肤疼痛的理解。再次修订时, 他直接借用金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为这整部非虚构小说的书名,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并在《花城》首刊。于此, 我们不难体悟出陈建功创作的初衷,也已感受到这一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分量。
法国作家萨特曾预言非虚构文学“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几十年过去,谁都毋庸置疑世界范围内的非虚构文本发展的速度惊人,尤其在当下中国,非虚构文体已经深入人
心,好的令人共情共鸣的非虚构作品,很容易就在公共空间自由传播, 并成了一个个文学热点。当然,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特征、叙事特质和艺术风貌, 写作者还在不断探索与丰富中。可见,文体的边界是由作家与理论批评家们共同完成的。而且,非虚构文体的可能性,更多取决于作家在实践中的拓展。书写 18 岁到 28 岁的矿工生活,这一愿望应在陈建功迎来命运的转机,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 77 级大学生后愈发炽烈,艰苦的青春磨炼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深嵌在骨髓里不变的矿工情缘,早已相互交融又永续向前地激荡在陈建功的心扉数十年, 甚至用什么形式予以表达, 都已不重要了。他自称断断续续写了几年,就这样让一个个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脉络像南方的野生植物,自由生长又芒刺在背,忽然他顿悟如此内容只能是部非虚构长篇小说,犹如美国 J.D. 万斯著的非虚构长篇小说《乡下人的悲歌》。之所以是非虚构,因为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人事;之所以是小说,因为不仅改了不少人物原型的名字,而且秉持了太史公的春秋笔法,描摹往事时不免有小说的虚实之道。然而, 当我们读完作品, 会发现这部作品中内核的血肉骨骼和精气神才是最打动读者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其笔下呈现的一切, 都与现实和时代, 与人的世界紧密契合, 更与青年陈建功血肉相连。正如后记所说:“不管非虚构写作者和研究者对这一文体有过何种定义,我只能秉持自己对这一文体的理解,去书写我的心路历程。”于是,无论是“无悔”,还是“有悔”都不能释怀尘埃中青春的陈建功, 在《我们脏的时候》
中的第 1 节,“‘人模狗样儿’话当年”这一开篇,即展现了全书嬉谑自嘲的腔调。
全书 48 节,《北京文学》发了上部 24 节,《花城》首先启用最终决定的书名 —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叙事从第25 节(在《花城》发的下部改为第 1 节)“‘屎盆子’又被扣到头上”开始。
内心的大悲欣,谁解
心怀几十年的悲欣,小说家陈建功激活了自己对非虚构和自传体小说的想象,以当下的观照与过去的再现相交织,灵动鲜活地将读者引入他的“人世间”。全书 48 节。哪怕没读过《北京文学》发的上部的 24 节,从《花城》第 25 节阅读,也能感受到迷人的叙事魅力。因为故事处处是入口,从任何 一节、任何一段开始, 都随时可以进入悲喜相悦的阅读境界—去回望历史现场那些毛茸茸的细节,你会慨叹那些喜剧里深藏着何等的悲辛,而那些悲剧里又深藏着何等的戏谑。作家找到了诉说特殊年代历史的绝妙“腔调”,它以艺术形象溢出和胀破了观念的历史,铭记了我们正在遗忘的过去。作者在书写中每每叩问人物与自我追问,而且笔下的人物一一对应自己的文学创作,在自我回望中厘清自己的文学之路,在自嘲反讽中反省特殊时代的激情与荒诞。这种历史书写的锋利,主体介入和渗透的历史书写,便有了文学史家和近乎历史学家的眼光。尤
其扉页题词“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的点题, 与结尾“我是如此地爱他们, 欣赏他们。即便是书中提及的、曾对我有所伤害的个别人,我也早已原谅,并对他们曾经的局限抱以深切的同情, 因为那年月, 我也如此可悲地被局限着”相呼应。这样深情的独白, 是以个体的叙事抵达历史, 抵达人道与慈悲, 也彰显了作者追溯并记述个人成长关联民族历史的创作旨归。他将自己 18 岁至 28 岁—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那些破碎的、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时光一点点拼合起来,那段被屏蔽掉的身体内外都被脏污的生活,以及一个个人物被时代巨轮席卷的命运轨迹,像拼图一样,越来越完整,便有了充满美学力量的 48节《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丹凤眼》及《飘逝的花头巾》的书写中,我们看到北京大学的学生陈建功对文学正典的致敬, 而在《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中, 我们却惊喜看到老年陈建功已把《辘轳把儿胡同 9 号》《皇城根》《鬈毛》的“京味”推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陈建功融会了自己从矿井、胡同、书房所有的生活与艺术滋养,汲取民间文艺活力,并浸透社会学、民俗学的观照, 以充满生命力的、接地气的甚至时而“粗俗”的民间口语, 书写这矿山、胡同的俚俗万象。其中绘声绘色的描摹,嬉笑怒骂的神气,几可令人感知一股 “艺术叛徒”的胆气。不难读出,这位作家不仅经历过精神的涅槃,磨炼出阅历沧桑的豁达,而且也找到了艺术地“重铸一个世界”的出口。
在此书上部我们看到, 陈建功 8 岁初到北京时从当地腔
调里体验到了隔阂,生发出自卑。那个不会普通话的孤独少年, 经历了中小学、矿山、恋爱的北京胡同时期, 步步深入体验北京文化的“本味”,尤其“当年是女友,后来是妻子” 一章,不禁令我们恍悟南方北海人陈建功何以理解“京味”,何以如此与作为编辑家的妻子隋老师恩爱一辈子。他青葱岁月最温馨的日子是在胡同里的女友家中欢喜度过的。经年日久的浸染, 使他融入“老北京”的日常与节庆, 那种或夸饰或平和的京腔京韵和北京的文化性格就一点一滴融入他几十年的岁月,并深深烙入他的骨髓, 使他笔下的北京, 皇城根下的声威, 升斗小民的心事, 要里要面儿地找乐儿, 耗财买脸的硬撑……在他的笔下, 风俗民情、文化生态生动传神, 烟火人间一地鸡毛又有滋有味,乃至胡同里闾的深处都呈现着生机与活力。读者常常在哑然失笑中会意陈建功作品中那份变中有常的北京文化特质。无论时代如何更替,与赫赫于庙堂的北京大礼堂相对应的,那些深潜于七拐八弯胡同人家的老规矩,依然代代相传。至今, 胡同的京韵京腔, 邻里街坊的客客气气, 公园廊子里提笼架鸟的老人的闲散,大妈们结伴去郊外游乐的喧闹,那份人间烟火气息是不能不令人产生扎根于北京文化的归属感的。不难想象,老北京风俗和日常如何温暖和熏染了这个来自南方并曾经居住在高校大院的青年。 8 岁才被父母接来又入住大学校园的陈建功,初入北京即陷入知识分子家庭氛围,当然会奋不顾身地扑向热气腾腾、温暖如春的老北京日常生活,使北京文化在不动声色之中潜移默化地温暖着他,神往与自觉化入、认
同, 可见北京文化的同化力量。为此, 我们也找到了陈建功写作腔调的人生来路。
是的,在第 36 节“慎终追远的膜拜”里,我们看到“当年是女友,后来是妻子”家的人间烟火如何铸就了他京味小说的底色。我曾经一直纳闷着,高校大院的孩子何以如此富有京味,读之豁然开朗:父亲回北海接我们全家到北京团圆时,我们姐弟两个,无论是与父亲还是母亲,似乎未曾有过亲昵和嬉闹。过去我以为,其他人家都和我家一样:白天,爸妈上班,我们上学;晚上回来,各自在自己的桌前看书,写作业……在北京,我家缺乏那种因血脉亲情而焕发的活力……女友家那个小院儿,似乎天天都那么热闹。
于青年陈建功, 世界为他打开了多扇窗, 他很快欢喜融入,直到成名后的自我叩问:有一次陡然问自己,你是喜欢这里的热热闹闹,还是喜欢人民大学院里那宁静的独处……在那“四合院”里,我确实能感到一种传统的温情和愉悦,可是也感到落伍于时代的郁闷。在那“高层建筑”里, 我确实能感到一种开创的活力和充实,可是也感到被冷冰冰的水泥墙挤在写字台前的孤独。幸好在我看来,两难、矛盾、纠缠不清,也可以成为文学的魅力所在。
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标本,有着慎终追远的膜拜,有着一种深植于心的传承,更有着北京文化的同化力量,也有了今天陈建功对二者融合而得的京味叙事。用作者的描述是:混迹于北京的胡同里闾, 应从 1973 年开始, 这就是 8 年后陆续写出《辘
轳把儿胡同 9 号》《鬈毛》《放生》等所谓“新京味小说”的准备期。
自嘲为“人模狗样儿”话当年, 谁解
这种以粗粝的非正典的叙事方式抵达正典,除了上述作者的文化基因,也是当下文学泛化与蔓延的一个新现象。商品时代大众文化的滥觞与民间文化的糅合,使得王朔们、赵本山和相声,到刀郎歌曲、游戏、脱口秀、微短剧等盛行于世,内在的精神风尚和逻辑,我们可参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见《文艺研究》 2024 年第 3 期)。其实,这也是现实不断地同历史对话的过程,所谓的“高大上”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无处发泄的情绪,便缠绕到民间文艺的自嘲自乐中,大众不约而同地迷上民间文艺传统, 一如被发配到京西矿山的青年陈建功“我渐渐沉迷于把搜集到的俚词俗谚写进我的小说。比如听过的一首民谣《十二郎》”。其实,《十二郎》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版本,“京西”版是母亲对十二个儿子的期盼,江苏版则是一个姑娘找了十二个情郎的梦想。在安徽, 那《十二郎》,竟然是一个已嫁作商人妇的怨艾,这样寄托民间理想的地缘文化开悟了陈建功对文艺的想象。之后, 还有老北京乡村的“地秧歌儿”民俗, 千军台和庄户村幡会等等。于是, 我们看到了中篇小说《前科》里秦有光母亲唱的《十二郎》,那份悲戚与无奈至今令人铭记。因此,在某种
程度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何尝不是陈建功文学版的北京说唱? 只不过他的创作更有美学自觉, 生动传神中, 其艺术世界愈发渗透着某种所谓大俗大雅的基调。知识分子家庭熏染的色彩,煤矿生活磨砺的粗犷,“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的幸运,北大精神滋养的独立与宽容,还不可忘记曾有北京人艺和电影学院艺术家的熏陶,作家浩然、草明等前辈的加持等等,足见其情感准备与文化来路之丰沛,怎不令我们的文学同道羡慕与钦佩?
除了系统的高等教育, 陈建功对草根文化、民间文艺和传统文脉的自觉, 还来自他兼容并包的学习态度。在他“和于是之们啜酒闲聊的日子”,我们知道彼时的北京人艺已经走在话剧领域的前沿。这就使陈建功最近距离地切入京味文化和顶级艺术, 熟知“传统”的保留剧目, 知道表演导演领域焦菊隐对斯坦尼体系的内化与创新,以及林兆华对戏曲美学的吸收与开拓,还接触了于是之等对“心象说”等演剧理论的整理与实践。何其幸运, 也何其及时, 陈建功把握了这些人文机缘, 他在社会熔炉里锻造太久太久了,他求知的心田如干渴的田野,瞬间生长葱翠的知识与百科。于是,他的小说脱胎于北大时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从话剧处女作《良心》,蜕变为颇具“京华风俗戏”腔调的《皇城根》(合作)、《鬈毛》,承接着民间文脉和大众文化的活力,酣畅淋漓地白描和演绎着皇城根下胡同人家的时代之变与人心之变,还有不变的年节与老规矩。我们也明白了这种文学与戏剧的“同系连枝”的人文
格局, 以及“大文学观”的文化视野与“大京派”文学的时代建构,今天不也成了热点吗?莫言、刘恒、潘军、刘心武等名家纷纷创作戏剧,我们又重新进入剧场,观剧热潮此起彼伏, “作家、作品与剧团”的互动关系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性的漫溢或者蔓延常态。回顾四十年前,陈建功就已经把戏曲元素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在京味话剧影响文学生态的当时,就以鲜活的笔触描绘北京百姓的现实人生。《皇城根》《鬈毛》《前科》不仅深层蕴含着“老北京”的文化情结与怀旧意味,更生动记录了时代变迁的人心与人生,并形成了个性独具的文学风格和叙事腔调,北大学生时期创作的剧作《良心》是,《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更是,生动精彩,厚重鲜活,宝刀不仅未老,还十分锋利。可见, 一个优秀作家的美学趣味和叙事腔调, 很难一言以蔽之, 或可说, 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美学特征, 都难以逃脱其直白和浅陋。
我们只看本书各章节的标题,便可读出陈建功的叙述腔调,尤其是他“独领风骚”的“自负”。在笔者看来,这种“自负”,就是一位作家不经意的“人设”。对于一个追求创作个性的作家来说,“不经意的人设”是迷人和独特的,和那种“刻意的人设”不可同日而语。且读它们看似随意涂抹而展示的各小节的回目,只读标题就令人忍俊不禁。那些贴着地面的自嘲,充满生活质感的甚至粗俗的声响,令人边读边会心会意,令你在粗粝的人生里感受到人性的丰富性,可谓一种伟大的粗粝,大俗至雅。诸如:“屎盆子”又被扣到头上、“偷
鸡贼”水灵灵、“故事篓子”、“伟大的啰唆”、“怪不得?怪不得”、“率领老娘儿们筛沙子”、“痞子翻天的快意”、“快乐的走窑汉”、“坐轮椅的窑哥儿”,后者是年轻的自己“让矿车撞折了腰”,如此等等。
方生方死,但“我是如此地爱他们”,谁解
可贵的还在于,《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借助一个个与作者生命休戚与共的人物命运或个人面孔,使作者的自我表述抵达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认知,作品悲喜剧的美学情结和丰富的文学张力,令这些人物群像毫不羞愧地挺立于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作品虽从矿工启笔,但笔下的人生极为丰富,因为彼时的青年矿工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产物,那也是年轻人命运跌宕、思想纷乱的时代, 这十年正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缩影, 而各色人物,也纷纷来自作家的积累宝库。陈建功对自己笔下所有人物都充满理解的同情与同情的理解,他直接引用契诃夫的金句:“……亲爱的苏沃林,请给我一个情节吧,我肚子里有无数个人物,他们纷纷要求出世!”
小说家陈建功是写人物的高手, 他写人的世界, 写人的性格与灵魂。尽管他熟知笔下每个人物,但他更知道孙犁小说的法则“大味必淡,大道低回”,他也明白这些人物被时代所裹挟的生活和过往, 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为此, 他一直
以克制内敛的笔致, 压到尘埃,沉入地心, 引而不发, 点点滴滴地把一个个他钟爱的人物,以及他们含泪笑对人生的艰难生活,哪怕是矿难的方生方死或方死方生都戏剧般地表现出来,可谓深流静水。工段六队他们 15 个从北京中学下来的学生矿工,各有个性;矿上的师傅如令人过嘴瘾的大老曾、撩人的李贯忠、病房里沉默的硅肺工友、“叛徒”老董、工段书记王群栋、与人为善的矿长、葬在京西唐家坟的王大溪, 由研究煤的“地下气化”遭遇嘲笑转而研究京西古道的伊可忠,以及至今时常相聚的洪胜、江宁们, 还有因矿难、硅肺煤肺离世的工友及其寡妇们,是这些至今还令作者的心隐隐作痛的人物,把他从一个胆小瘦弱的大男孩, 变成一个粗粝的矿工。如今, 他以自己的书写疗救悲欣交集的十年青春,并以粗粝的矿山生活和疗伤的民间戏曲,尽写人物的喜怒哀伤与悲怆人生。
是的, 陈建功喜欢戏曲, 喜欢戏曲故事里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乃至人情世故,还有戏曲行头的仪式感,唱腔的高歌、苍茫、哀泣与悲怆。它既可铿锵于戏院, 也可在老北京胡同的茶余饭后。甚至门卫、剃头铺里的老者,通过这些人物,我们认出了一个个有模有样有腔调的形象。这个真实的群体与作者息息相关, 与时代变迁、与社会行进轨迹密切关联, 由此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父辈、同辈甚至自己。作者熟知每个人物的体温, 一个个人物的体温构成了人生的生气、时代的心相和历史的温度, 深刻深厚、生动有趣, 令人想起中国现代叙事的起源,诞生于街头巷尾的话本,作品流淌着这种说书人般的自在
与快意。当然, 更具劲道的是这种充满生活质地的粗俗, 如宝刀般锋利,直刺人物神经。比如“叛徒”老董的隐忍与委屈, “我”被工友揭发遭冷遇等时代的荒诞,作者对所有人物给予理解的同情,包括对自身“红卫兵时代”盲从的反思。
第 31 节“只是为了逃离卑微”中对自己在特殊时代的自我追问,坦诚而犀利,显示了刮骨疗毒般的勇气和力量:“那你为什么还要对这‘革命’报以如此的激情?自忖我没有更大的野心。 一切一切, 都只为改变一个卑微的自己……包括整过我的王群栋,倒也恶不到哪儿去,其实也不过就是见风使舵恐落人后罢了。你又何尝不是?”
作品非常自觉地仿效鲁迅先生, 对“国民性”予以深刻的反思—包括作者在内, 一方面是面对荒诞时代的无奈, 一方面是苟且于窃窃的欣喜;一方面是冷眼面对现实的清醒, 一方面是所谓同仇敌忾的振臂……如此普遍的“平庸之恶”,岂不是每一个亲历者都曾拥有?难得的是,作者在反思一切的时候,绝无高屋建瓴的傲慢,更无居高临下的指点,而处处是反观自身、秉笔直言的愧怍。以自省与自嘲为发端的对“国民性”反思和自我的检讨,应该是巴金先生《随想录》所开创的。而陈建功正是遵循着巴金先生的指引,实践着巴金的文学理想,并以自己的书写“把心交给读者”。这不仅需要思想的敏锐,更需要情感的境界。
有着天生的敏感与痛感的作者,忆起那群在矿井一起生活十年赤膊相见的工友,忆起那些地上井下方生方死的兄弟姐
妹, 他们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一张张巷道里黢黑的脸庞, 医院里工伤工友们的静默,曾经的方死方生却亲如家人,哪怕为蝇头小利加害他的工友, 已是同情的理解, 也念兹在兹。这份过命的深情,作者在叙事中一直内蕴于胸,最大程度地体现着叙述的控制力, 内敛节制, 艺术张力巨大。只有一处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抒写了好友王大溪,深沉的腔调令人心痛,即第 15 节“唐家坟”,写工友王大溪仿杰克 ·伦敦笔下《马丁 ·伊登》般决绝而从容的死,可谓抵达孙犁“大道低回”的艺术境界。
当然这种颇具民间文艺的活力,以及大俗大雅的草根性,只是陈建功文化基因的底色,看得出,这位作家审美意蕴的形成得益于系统的学习和众多学科的涉猎。我们知道世界观影响我们的艺术, 而艺术也可以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这部《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特别是该期《花城》刊出的下半部所展示的、作家自述心灵觉醒以及被文学潮流所推动所造就的历程,堪称是滥觞于 20 世纪 70 —80 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生动写照。
作者叙述了自己文学观念的觉醒过程:如何游走于北展剧场,获取观赏“内部电影”的机会;如何得到北影编辑的关爱,在与戏剧、电影界艺术家坦诚的沟通中领悟到艺术之道;如何幸运地获得写一部“献礼作品”的机会, 这一机会又如何使他面对着 1978 年横空出世的小说《伤痕》的挑战,终于使他弃改剧本而完成了文学观念的涅槃……这一独特经历的书写, 不仅因其具有的戏剧性令人唏嘘,更因其对那一时代文学人观念转
变的典型性而值得赞叹。据查, 这一事实—《伤痕》发表当日,陈建功的确和他的合作者林洪桐住在上影的永福路招待所,而《伤痕》发表的次日,即 1978 年 8 月 12 日陈建功、林洪桐的确放弃了对电影剧本《同龄人》的修改,返回了北京。可见作家所写,即使是这一富于经典性的桥段,也是“非虚构”的。我自认为这一 “调查”证实了作者的专业水准,以及“把心交给读者”的赤诚实践。而本书所述, 不仅是一个青年走窑汉的心路轨迹, 更是一个作家文学成长之路的轨迹。陈建功愈发呈现为一位具有主体性自觉的作家,他为我们提供了文学转型时代的心灵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他之为陈建功的因由和深度。
这种主体性的自觉,并不展示为佶屈聱牙的“哲理”和貌似高深的说教。因为他就想这么把心交出去,就这么贴着人物讲故事,讲“我”的故事,讲身边“我们”与时代的故事,讲故事里的良善与温暖、生趣与哲学。因为“我”是“我们”, “我”又不同于“我们”;因为今天“人模狗样儿”的我,“是如此地爱他们”,“我”心怀悲欣。
后记写道:“我书写的首要原则是:诚实。与之同样重要
的原则是:有趣。”作品入口如此之小,内里格局却阔大。全书筋骨强劲,流畅有力。当我们跟着作者一直隐隐深潜流动的情感, 读完掩卷, 触摸到作者诚实与有趣的灵魂时, 不禁含泪追问:这嬉笑下的悲欣,谁解?!
原载《花城》2025 年第 1 期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