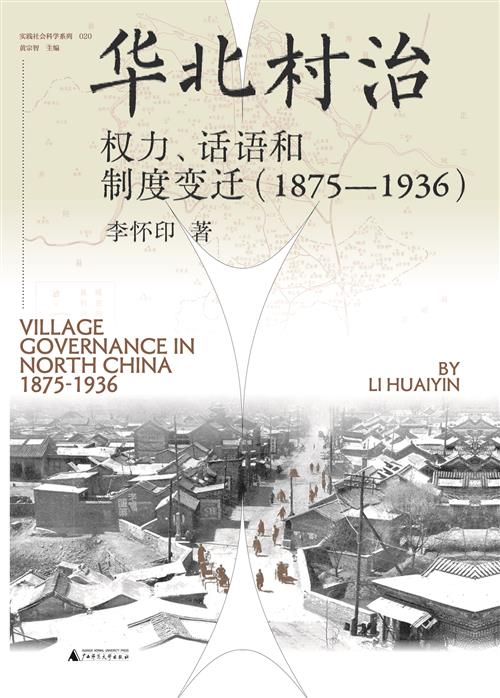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8-01
定 价:89.00
作 者:李怀印 著
责 编:王佳睿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中国史
开本: 32
字数: 260 (千字)
页数: 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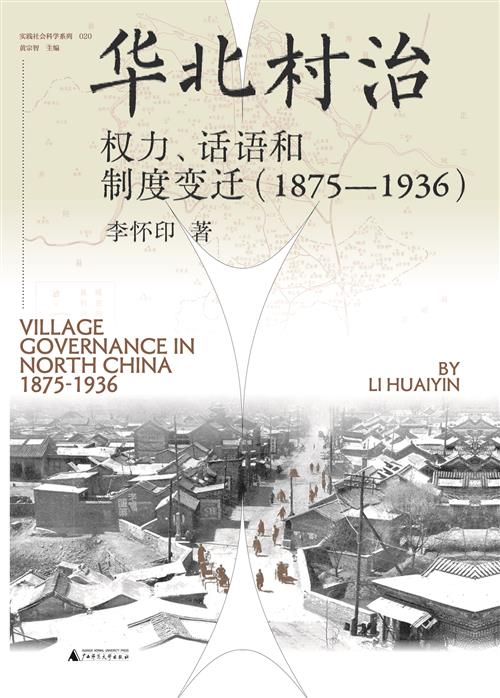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研究晚清民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史学术专著。作者聚焦晚清至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乡村治理,充分利用河北省获鹿县完整丰富的历史档案,对当地村级税收、办学、地方自治以及基层行政人员的选任与日常履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还原最底层的乡村细节。作者把晚清、北洋、国民党时期串连起来加以研究,从而厘清国家政权从皇权时代向近代国家转变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同时,跳出获鹿一隅,由获鹿及华北,由华北及中国,从地方档案的碎片中窥测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书中基于地方民众和精英的合作与博弈,强调普通乡村的基层治理实践,重构了近代中国的乡村叙事。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著有中英文版《华北村治》《乡村中国纪事》《重构近代中国》《现代中国的形成》,以及英文近著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中文再版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地方治理
第一章 背景
第二章 农民社群中的合作与控制——乡地制
第三章 规范、自利和策略——乡地充任纠纷
第四章 征税
第五章 土地和税收管理
第二部分 1900年以后的新变化
第六章 权力、话语和合法性——村正充任纠纷
第七章 兴学上的合作与冲突
第八章 乡村精英的积极作为
第九章 乡村行政重组
第十章 清查“黑地”
第十一章 结论
参考文献
晚清民国的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
这本书的底稿,是我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是黄宗智先生。论文资料的搜集,始于1996年,当时我在利用几个暑假奔走于西南、华东、华北多个档案馆之后,最终确定用收藏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档案馆的获鹿县衙门档案,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税收问题。论文本身前后用了四年时间写完,当中数易其稿。之后我获得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的正式教职,又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增加了两章,分别是民国初期村政权的设立和运作,以及同一时期各村兴办新式学堂的情况。其他各章,尤其是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田赋征收的行政管理以及国民党时期村级政权的改组和运作的章节,也做了实质性的修改、扩充。这样,增补后的书稿内容已经不再只是田赋的征收和管理,而涉及乡村治理的各个主要方面,虽然田赋征收依然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2005年书稿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书名即为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875—1936。中文版《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转眼,距这本书的英文原版行世,已经过去二十年,国内的中文版也早已在市面上脱销。这次为了再版此书,我将原来的中文译稿做了仔细修订。趁此机会,我也想把当初着手写这个题目时所构思的中国乡村史研究路径,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梳理。
过去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中英文著述已有很多,其中关于国家与乡村关系特别是税收和地方治理的论著也有一批,但在1990年代之前,所依据的资料,大多还仅限于官方志书、典籍、族谱、碑刻之类,利用原始档案做研究的风气已开始呈现,但不普遍,而且多限于粗线条的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往往只见制度不见细节。怎样才能做到独树一帜?我在寻找、甄别档案的时候,心中有一个选取标准,就是要有能够反映社会最底层情况的村级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要能展现乡村日常治理,特别是老百姓与官府打交道的活生生的场景,用黄宗智先生的话说,要一竿子插到底。获鹿县的原始档案非常丰富,有相当一批跟税收、办学及村职任免有关的案卷直接来自村民之手,应该说可以满足论文写作的要求。我在1996年暑假第一次到河北省档案馆,便基本收齐了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后来为了修改成书,又在2002年夏天去了一趟。
一头扎入如此丰富的宝藏,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写出来的东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流于所谓碎片化。所以我在谋划整篇布局和具体写作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既要扎到最底层,不放过有价值的细节,又要能够跳出来,看到整片树林,关键是要有纵向和横向的视野。就纵向而言,获鹿档案的珍贵之处,正好在于它的时间跨度有连续性,从清代特别是晚清到北洋和国民党时期,基本上都有足够的案卷能够涵盖,这在国内县级历史档案中并不多见;更为难得的是其中北洋时期的资料特别丰富,而过去对这一时段的乡村史研究相对欠缺,正可以弥补。把晚清、北洋、国民党时期串连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基本上可以看清中国的国家政权从皇权时代的旧体制向近代国家形态的转变给乡村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把获鹿作为这样一种纵深观察的切入点,也再合适不过。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有个时间限定,即1875年(光绪元年,为书中所引获鹿档案的最早年份)到1936年(书中所引档案最晚年份)。(1937年以后,日本全面侵华,20世纪早期以来的近代国家转型过程被打断,获鹿档案也不再具有此前各个时期的系统性。究竟抗战时期以及后来的国共内战时期获鹿乡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希望今后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填补这个空缺。)
本书也很在意横向的对比。书中始终强调获鹿所代表的冀中南与冀东北的对比;大体上可以说,这两个地区分别处于施坚雅(G. W. Skinner)所说的华北“大区”(macroregion)的中心与边缘地带。这两个地区在生态环境、人口密度、经济商品化程度、乡村社会组织构成等各方面相去甚远。过去对华北农村的了解,尤其是基于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研究,多侧重华北大区的边缘地带,对其核心地带的了解不多,至少可以说不系统。除了把冀中南与冀东北加以比较,书中也把华南地区纳入视野。由获鹿及冀中南,由冀中南及华北,由华北及全国,有了横向的视野,再结合纵深的观察,庶可跳出获鹿一隅,从档案研究的碎片中窥测地方史的发现对体认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有何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叙事的建构。获鹿、冀中南,或者说华北大区的核心地带,从晚清、北洋到国民党时期的一系列变迁,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这本书到底要讲怎样一个故事?自从1950年代以来,国内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史研究,基本上都跳不出一个大的叙事框架,即自从19世纪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加上政府的苛捐杂税和严重的地租剥削,导致农村经济走向凋敝,手工业破产,农民的暴动、起义、革命成了乡村社会历史的主旋律。美国同行对华北乡村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叙事,即20世纪的国家政权建设,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也导致渔利型的乡村领导层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保护型村社领袖,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走向解体,从而为外来政治力量所渗透,特别是为共产党的革命动员铺平了道路。这样一种叙事,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它多少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但它也遮蔽了近代中国乡村生活丰富多样的现实,使我们对中国农民(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流于单一。事实上,就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村民的日常社会交往而言,村与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异很大。过去人们所熟悉的阶级对抗和集体暴力的场景,抑或村社解体、土棍恶霸横行乡里的画面,或许在边缘地带的部分村落可以得到印证,但远不足以概括像冀中南这样的中心区域的乡村生活图景,那里更常见的还是村民之间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相互合作的一面。既有合作,又在合作的过程中为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展开竞争和冲突,这是获鹿的村级档案呈现出来的基本图像。总体而言,这本书强调了这样一条主线:从晚清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时期,国家权力在不断向下渗透,地方的非正式权力和乡村内生的惯例,在不断地让位于全国性的正式制度,这一过程在日本侵华之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一步步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普通村民与乡村精英之间,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权之间,既有冲突对抗的一面,又有相互妥协合作的一面。地方治理被逐步纳入全国性的制度化过程,而不是国家渗透压力下地方村社走向崩溃,这是本书要讲的故事。
最后,我就这本书的分析工具讲两句。过去西方学者研究农民,基本上不出两种思路:一种认为农民是理性的、自私的,其社会、政治行为皆受个人经济利益驱使,跟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并无实质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讲村社共同体的生存伦理,并由此形成种种制度安排,确保村社成员的生存权利。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足以解释农民社会政治行为的复杂性。我在书中借用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概念,认为农民的思想行为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个人利益得失的算计,同时还有外界的制度环境、惯例、话语,等等。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使村民们形成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行为倾向”(dispositions),或隐或显地制约每个村民的行动抉择。无论是普通村民还是村社中的精英人物,在卷入村社集体活动、履行个人义务的过程中,都既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又受到社会惯例、公众舆论的约束。其脱轨或滥权行为,都有一定的限度。他们在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不得不考虑维持和再生自己的象征利益或社会资本。因此,本书的意图之一,是在中国农民研究领域,突破西方传统的理性或道义小农非此即彼的看法,尝试提出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综合性的解释。这一方法,贯穿于全书有关乡地选任、税收纠纷、村长选举和开办学堂的各个章节之中。这次再版,我把书名的副标题改为“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便是为了体现这一思路。
李怀印
2025年3月23日
于奥斯汀
本文节选自李怀印《华北村治: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1875—1936)》
2025年8月
《华北村治》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华北乡村治理模式之特性,尤其是其背后政治生态、农民行为、官民互动的复杂肌理,具有突出的思辨风格、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是中国近代史及相关领域不可绕开的经典之作、必读之作。
——李金铮 南开大学教授
李怀印教授的《华北村治》一书使用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认真细致的解读,对华北近代乡村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剖析,锤炼出全新且合理的阐释,饱含大量启迪性的论述。此书为理解华北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马俊亚 南京大学教授
这是一项有关晚清和民国初期村庄与国家关系变化的极具信息量的研究。全书力图重构帝国晚期华北平原的历史图景。现有英文文献几乎都将该地区描绘成旱灾、饥荒与叛乱肆虐之地,进而认为二十世纪初的华北经历了旧制度崩溃、乡绅阶层逃离乡村、土豪劣绅乘机崛起的过程。作者虽不否认这种描述的局部真实性,但指出其仅适用于华北宏观区域的边缘地带。作为此书研究对象的获鹿县则展示了华北核心区的另一幅景观,这里人口稳定、农作常有盈余、宗族势力强大,官民之间维持着协作传统。这为我们重新审视华北平原提供了新视角。如果我们把此书与日益丰富的中国研究放在一起,便更容易看出,不同地域因生态差异以及融入国家体系的不同路径,而形成迥异的发展轨迹。这本书对非专业读者来说可能不是最容易阅读的,但对于希望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任何人来说,它将是必读之作。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牛津大学教授
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
基于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底层的日常生活,
展现地方精英与当地民众的合作与博弈,
探讨权力、话语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晚清至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的历史呈现出多维度与多层次的特征。其间既包含广为人知的村社解体、草根动员与集体暴力,亦存在长期被忽视却对普通村民至关重要的基层治理实践。本书将研究视角从宏大叙事所描绘的波澜壮阔图景,转向乡村底层相对宁静平和的社会生活。作者充分利用直隶省获鹿县(古旧县名,今为石家庄市鹿泉区)所藏异常完整丰富的历史档案,对当地村级税收、办学、地方自治以及基层行政人员的选任与日常履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
书中展示当地民众与精英如何在维护乡邻共同利益方面展开合作,同时又如何为私利而展开争夺,并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权力、话语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作者强调,近现代华北乡村的历史,除却表层的对抗、冲突与断裂,其深层亦存在渐进、连续与稳定的一面。不同区域与不同时期,这两种历史面向各有凸显,然而对于全面理解华北乡村丰富的历史图景,二者均不可或缺。
晚清民国的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
这本书的底稿,是我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是黄宗智先生。论文资料的搜集,始于1996年,当时我在利用几个暑假奔走于西南、华东、华北多个档案馆之后,最终确定用收藏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档案馆的获鹿县衙门档案,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税收问题。论文本身前后用了四年时间写完,当中数易其稿。之后我获得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的正式教职,又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增加了两章,分别是民国初期村政权的设立和运作,以及同一时期各村兴办新式学堂的情况。其他各章,尤其是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田赋征收的行政管理以及国民党时期村级政权的改组和运作的章节,也做了实质性的修改、扩充。这样,增补后的书稿内容已经不再只是田赋的征收和管理,而涉及乡村治理的各个主要方面,虽然田赋征收依然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2005年书稿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书名即为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875—1936。中文版《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转眼,距这本书的英文原版行世,已经过去二十年,国内的中文版也早已在市面上脱销。这次为了再版此书,我将原来的中文译稿做了仔细修订。趁此机会,我也想把当初着手写这个题目时所构思的中国乡村史研究路径,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梳理。
过去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中英文著述已有很多,其中关于国家与乡村关系特别是税收和地方治理的论著也有一批,但在1990年代之前,所依据的资料,大多还仅限于官方志书、典籍、族谱、碑刻之类,利用原始档案做研究的风气已开始呈现,但不普遍,而且多限于粗线条的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往往只见制度不见细节。怎样才能做到独树一帜?我在寻找、甄别档案的时候,心中有一个选取标准,就是要有能够反映社会最底层情况的村级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要能展现乡村日常治理,特别是老百姓与官府打交道的活生生的场景,用黄宗智先生的话说,要一竿子插到底。获鹿县的原始档案非常丰富,有相当一批跟税收、办学及村职任免有关的案卷直接来自村民之手,应该说可以满足论文写作的要求。我在1996年暑假第一次到河北省档案馆,便基本收齐了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后来为了修改成书,又在2002年夏天去了一趟。
一头扎入如此丰富的宝藏,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写出来的东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流于所谓碎片化。所以我在谋划整篇布局和具体写作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既要扎到最底层,不放过有价值的细节,又要能够跳出来,看到整片树林,关键是要有纵向和横向的视野。就纵向而言,获鹿档案的珍贵之处,正好在于它的时间跨度有连续性,从清代特别是晚清到北洋和国民党时期,基本上都有足够的案卷能够涵盖,这在国内县级历史档案中并不多见;更为难得的是其中北洋时期的资料特别丰富,而过去对这一时段的乡村史研究相对欠缺,正可以弥补。把晚清、北洋、国民党时期串连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基本上可以看清中国的国家政权从皇权时代的旧体制向近代国家形态的转变给乡村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把获鹿作为这样一种纵深观察的切入点,也再合适不过。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有个时间限定,即1875年(光绪元年,为书中所引获鹿档案的最早年份)到1936年(书中所引档案最晚年份)。(1937年以后,日本全面侵华,20世纪早期以来的近代国家转型过程被打断,获鹿档案也不再具有此前各个时期的系统性。究竟抗战时期以及后来的国共内战时期获鹿乡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希望今后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填补这个空缺。)
本书也很在意横向的对比。书中始终强调获鹿所代表的冀中南与冀东北的对比;大体上可以说,这两个地区分别处于施坚雅(G. W. Skinner)所说的华北“大区”(macroregion)的中心与边缘地带。这两个地区在生态环境、人口密度、经济商品化程度、乡村社会组织构成等各方面相去甚远。过去对华北农村的了解,尤其是基于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研究,多侧重华北大区的边缘地带,对其核心地带的了解不多,至少可以说不系统。除了把冀中南与冀东北加以比较,书中也把华南地区纳入视野。由获鹿及冀中南,由冀中南及华北,由华北及全国,有了横向的视野,再结合纵深的观察,庶可跳出获鹿一隅,从档案研究的碎片中窥测地方史的发现对体认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有何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叙事的建构。获鹿、冀中南,或者说华北大区的核心地带,从晚清、北洋到国民党时期的一系列变迁,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这本书到底要讲怎样一个故事?自从1950年代以来,国内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史研究,基本上都跳不出一个大的叙事框架,即自从19世纪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加上政府的苛捐杂税和严重的地租剥削,导致农村经济走向凋敝,手工业破产,农民的暴动、起义、革命成了乡村社会历史的主旋律。美国同行对华北乡村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叙事,即20世纪的国家政权建设,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也导致渔利型的乡村领导层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保护型村社领袖,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走向解体,从而为外来政治力量所渗透,特别是为共产党的革命动员铺平了道路。这样一种叙事,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它多少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但它也遮蔽了近代中国乡村生活丰富多样的现实,使我们对中国农民(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流于单一。事实上,就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村民的日常社会交往而言,村与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异很大。过去人们所熟悉的阶级对抗和集体暴力的场景,抑或村社解体、土棍恶霸横行乡里的画面,或许在边缘地带的部分村落可以得到印证,但远不足以概括像冀中南这样的中心区域的乡村生活图景,那里更常见的还是村民之间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相互合作的一面。既有合作,又在合作的过程中为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展开竞争和冲突,这是获鹿的村级档案呈现出来的基本图像。总体而言,这本书强调了这样一条主线:从晚清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时期,国家权力在不断向下渗透,地方的非正式权力和乡村内生的惯例,在不断地让位于全国性的正式制度,这一过程在日本侵华之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一步步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普通村民与乡村精英之间,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权之间,既有冲突对抗的一面,又有相互妥协合作的一面。地方治理被逐步纳入全国性的制度化过程,而不是国家渗透压力下地方村社走向崩溃,这是本书要讲的故事。
最后,我就这本书的分析工具讲两句。过去西方学者研究农民,基本上不出两种思路:一种认为农民是理性的、自私的,其社会、政治行为皆受个人经济利益驱使,跟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并无实质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讲村社共同体的生存伦理,并由此形成种种制度安排,确保村社成员的生存权利。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足以解释农民社会政治行为的复杂性。我在书中借用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概念,认为农民的思想行为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个人利益得失的算计,同时还有外界的制度环境、惯例、话语,等等。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使村民们形成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行为倾向”(dispositions),或隐或显地制约每个村民的行动抉择。无论是普通村民还是村社中的精英人物,在卷入村社集体活动、履行个人义务的过程中,都既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又受到社会惯例、公众舆论的约束。其脱轨或滥权行为,都有一定的限度。他们在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不得不考虑维持和再生自己的象征利益或社会资本。因此,本书的意图之一,是在中国农民研究领域,突破西方传统的理性或道义小农非此即彼的看法,尝试提出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综合性的解释。这一方法,贯穿于全书有关乡地选任、税收纠纷、村长选举和开办学堂的各个章节之中。这次再版,我把书名的副标题改为“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便是为了体现这一思路。
李怀印
2025年3月23日
于奥斯汀
本文节选自李怀印《华北村治: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1875—1936)》
2025年8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