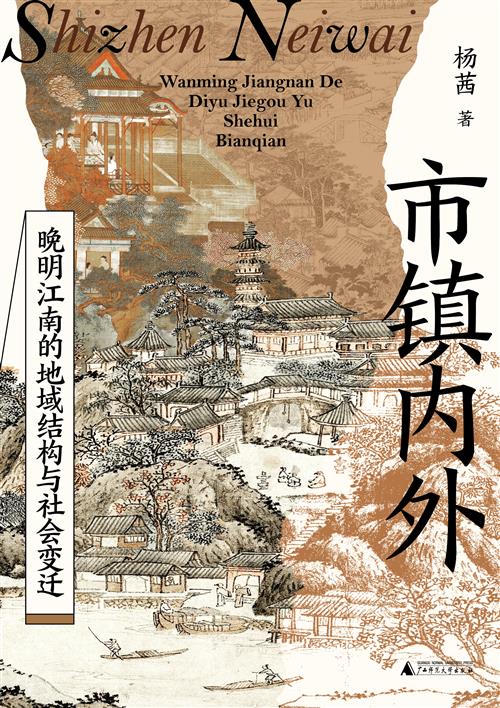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8-01
定 价:78.00
作 者:杨茜 著
责 编:倪小捷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中国史
开本: 32
字数: 280 (千字)
页数: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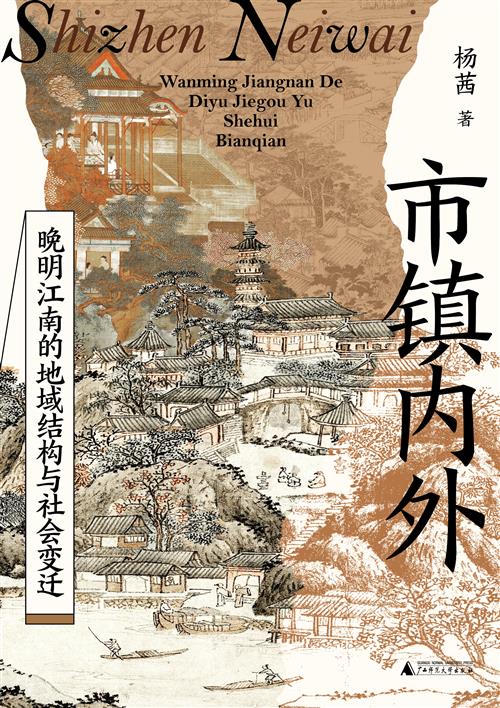
一部聚焦晚明江南市镇的区域社会史著作,从家族兴替、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角度展开,生动再现晚明江南市镇社会的立体图景。书中以权势阶层为切入点,深入市镇内部,揭示在带有明显人为“创市”痕迹的市镇中,权势群体的形成与变化,其中,地方力量的“士绅化”是一项关键节点;又从外部环境的视角,分析市镇这一大规模发育的聚落形态对晚明江南地区原有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与变动。本书将市镇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创新性地关注了地方力量在市镇发展中的作用,揭示特定时空下江南社会历史演进的内涵与特征,为理解江南市镇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杨茜,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东华大学副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明清史及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已主持完成三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在《历史研究》《史林》《历史档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丁宾传》。
绪论 晚明江南的开发:地域、市镇与士绅
一、江南地区的开发
二、地域结构变化:市镇
三、地方社会力量:士绅与家族
四、本书的研究范围与主旨
第一章 家族与市镇
第一节 “创市”现象
一、因人成市
二、“创市”概况
第二节 创市者的形象
一、“主姓”形象建构
二、家族背景与经营渠道
三、人为力量的凸显
第三节 家族扩张与新市镇
第二章 市镇权势的士绅化
第一节 从“赀郎”到“制科官”
第二节 经营与困境
一、睦族与义行
二、赋役之困
三、家族内外冲突
第三节 士绅化历程
一、定居与荐举
二、压力与发展
三、徭役与竞争的危机
四、科举策略的成功
第三章 市镇权势的家族兴替
第一节 长泾市
一、从三泾里到长泾市
二、“主姓”的兴衰
三、新“市主”的崛起与纷争
第二节 诸翟镇
一、聚落环境
二、著族兴替
三、侯氏动向与影响
四、家族活动印记
五、王朝鼎革下的紫堤村
六、余韵
第四章 园林与市镇文化
第一节 市镇园林景观
一、市镇之园林
二、园林区位与分布
三、园林景观与市镇风貌
第二节 园林文化活动
一、园林雅集与市镇文化空间
二、李流芳与南翔镇园林
三、檀园宴集与南翔风雅
四、园、地相传
第五章 市镇与州县治理
第一节 失治的堰坝
一、澉浦镇环境与永安湖水系
二、明代湖堰失治
三、澉浦士绅的谋划
四、治湖困境与现实
五、利益选择
第二节 城、乡之间
一、市镇河道的功能与环境
二、市镇水利的主持者
三、“亲和”于城市的水利实践
四、管理张力
第六章 市镇与基层秩序
第一节 城、镇之序
一、水利形势与主次之序
二、历次疏浚分析
三、区域利益与施政偏向
第二节 市镇之争
一、耿橘治水
二、抵制与平衡
三、地域认同与影响
余 论
主要参考文献
一、地方史志类
二、其他史籍类
三、近人研究著作类
四、今人研究论文类
后 记
自序
明万历二十九年,常熟知县赵国琦主持县内的河道浚治,其中包含一条重要的地域性河道——横沥塘。该塘东接太仓七浦河,西抵白茆河,并流经常熟县内的何家市。何家市在明嘉靖年间即已出现,市镇中的商贾对外交通多依赖这条河道。赵知县在处理横沥塘疏浚工程时,对不同流经区域的役力安排做出明确区分,涉及人群除了惯例中的士大夫和农民,还特意提到了何家市中的“市民”:
白茆口迤至何家市,上区任之,市民向舟楫之利者佐之;由赤沙塘口迤至晋贤泾口,下区任之,别区如四十都、二十三都有田相续者佐之。……士大夫不得借优免之名,巧为规避;市商贾不得概诿为农氓之事,而坐享其嬴。 (《邑侯赵公议浚横沥塘碑记》)
几年之后,另一位常熟知县耿橘再次开启水利工作。在浚治县中另一市镇(归家市)附近的河道时,镇中市民一度遭到奸豪大户的“仗役鲸吞”,耿橘为此发布公示,申明“止开市镇之河,略借市廛之民力耳”,强调“除市河之外,并不用市民开浚尺寸”。(《禁大户科派市民开河示》)
通过上面两则事例,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在市镇中生活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已经是签派水利力役时的一个固定群体。与此同时,乡绅大户会像科派小农一样,向市镇“市民”转嫁劳役,但“市民”也有推诿逃役的情形。在乡绅大户和村落民众之外,市镇“市民”形成一方新的利益主体,而市镇本身也成为官府在牧民理政时必须予以单独考虑的一类聚落空间。
本书正是在诸多如上述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
16世纪之后,长江三角洲的商业市镇获得快速发展,不仅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功能和规模也同步增长 其中一小部分市镇今天已被开发成为旅游区,如乌镇、南浔、周庄、同里、西塘、朱家角、枫泾等。这些热门旅游古镇,在明清时代都是具有重要市场功能的商品集散地,用著名学者施坚雅的话说,它们是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的出售地,也是家庭需用但不自产物品的购买地,换句话讲,商业市镇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所谓“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在江南地区以棉布和丝织品为大宗,它们从三角洲广大乡村生产者的手中汇集到一个个市镇,又从市镇店铺中卖出,随着无数客商“向上流动”进入全国乃至海外市场。
商业市镇的繁荣,是明清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突出表现。正因此,江南市镇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市镇的经济面貌是最受关注的层面。 不过,当我于2012年前后开始接触江南市镇的研究话题时,却一直未打算在经济层面致力。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创作一份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市镇经济领域丰厚的研究成果令我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对历史中具体的人及他们的行动更感兴趣,尤其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看到许多冠以姓氏的市镇以及类似开篇的案例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其实,广布的市镇,在备受关注的经济领域之外,仍然对江南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这样的思路下,本书的内容有两个锚点,一是生活于江南市镇中的“权势阶层”,二是将市镇作为一类聚落形态置于江南社会中展开讨论。
“权势阶层”,主要指豪强地主和乡绅大户,他们无论在明清时代还是现代学术研究中都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地方行政的完成有赖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同时,在相当一部分市镇的发育过程中,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反映着一系列变迁。这是本书标题“内外”中“内”的部分。
将市镇作为一类聚落形态来讨论,前提在于江南市镇乃自然生长而成,但并不具有建制性,所拥有的地理空间又往往地跨若干基层政区,且数量和功能都有相当的规模。 本书主要选择以水利为主的州县治理工作,分析市镇作为这一时期大规模发育的聚落形态,对晚明江南地区原有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与变动。此时,市镇内普遍存在的权势阶层仍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本书标题“内外”中“外”的部分。
本书讨论的主题,缘起于申请攻读博士时的研究计划,之后经历了博士论文的初步搭建,以及毕业后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思考与修订,最终形成现在的文本。 虽仍不见得成熟,但作为一个阶段的研究心得与见证,愿借此次出版的机会,求教于方家。
——节选自杨茜《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这是一本晚明江南市镇列传,通过书写市镇中权势阶层的创业、科举、治水、夺庙等故事,展现晚明江南社会的历史变迁。这些故事中,有的家族曾富甲一方,以自己的姓氏命名市镇,然而在短短数十年间,却因战乱、赋役、科举失意或资源争夺而走向衰败。这些充满戏剧性冲突与转折的故事,不仅揭示了家族命运的起伏,也映射出市镇对地方社会的深刻重塑。
夏氏捐金凿河而开市、顾氏控制城隍庙“神迹显灵”来夺取权力、何氏因科名断层被新兴杨氏逐出何家市,这些地方世家大族摸爬滚打的创市历程和家业衰败、市镇易名的无常命运,不仅深入人心,更揭示了市民、市镇、地方社会的缠斗和共生。本书以理性的笔触反映了那些主导个人与家族兴衰背后的命运之手: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镇的繁荣,地方治理措施、国家科考选才制度、经济内卷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地方的权力结构。
本书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还让我们感受到了个体与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以及他们与市镇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本文聚焦晚明江南市镇开发过程中家族冲突的现象。通过三个具有戏剧冲突性的历史事件(何氏因科名断层,被新兴杨氏借命案逐出何家市;钱氏屡遭“诬告”,凭财势与暴力完成横塘河圈地;徐氏内部嫡庶相残,兄弟阋墙,最终血脉凋零、市镇易名三大事件)将赋役重压、棉业勃兴、人口迁徙与资源争夺编织成理解晚明基层社会的“冲突模型”,揭示家族矛盾既是地方权力重构的导火索,也是江南三角洲开发史的微观注脚。
——编者按
虎斗蛟腾:晚明江南的家族纷争与权力结构洗牌
除了来自州县的赋役重担,区域间的家族矛盾和家族内讧也是常见的挑战。这些冲突会影响家族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能反映地域社会的历史进程。
何家市的何氏家族,在明末遭遇了其他家族的冲击。何氏最兴盛的时期为何钫、何矿兄弟中举入仕的嘉靖、万历年间,此后,子弟科名不继,家族呈衰落之态。至何矿的孙辈,只有何君立一人,他性格骄纵,少习举业未有成。 何家市中此时有杨氏家族崛起,家资日渐雄厚,已经与何家不相上下。“一山难容二虎”,两大家族互相“不悦”,恰逢杨氏中一名役夫因故死去,这名役夫恰好曾经是何家的奴仆,这一渊源被有心人利用,制造谣言,故意激怒何君立。何君立果然一激即起,“集人娖队执械往”,抢砸了杨家。杨氏诉诸官府,何君立最终“不胜,走四千里”。
钱氏的家乘中常可以看到族人被“诬”的记载。如第二十二世钱校,即“尝为仇家所中,被逮,榜笞惨毒,见者股栗”。第二十三世、钱泮的三弟钱洽,也曾被“里中少年”诬告,但告状之人很快得病而死,便没有了下文。
嘉靖年间,钱岱的祖父钱昇,因为支持县令捕盗,得罪了豪宗,而遭陷害致死:
嘉靖中,濒江之里盗窃发,而依豪宗为城社,里中噤莫敢谁何。 邑大夫孟公白之当道,请诘盗而以属公。公抗言曰:“治盗易耳,奈盗主何?”孟公曰:“主为谁。” 公曰:“不意今者近出巨族。”孟公始难之,既而张目向公曰:“子不庇奸而我何容纵冠。”公于是廉盗之主使、羽翼,及出入往来,悉籍记之以上孟公。 孟公披籍索盗,盗无脱者,而豪卒腐心于公,思有中公矣。 会奸民负租者,公往征之,而与其子溺,会豪曰:“此足以死公也。”遂以诬公。
不久,钱昇的季弟钱庶,中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遂为兄长“倾身求解”。也许因为刚刚考中,且举人的资格尚不够强大,所以并没有将兄长解救出来。四年后,钱庶考中进士,力图再次斡旋鸣冤,但钱昇忽然去世。
这些“诬陷”的记载,均出自钱氏一方的记录,很遗憾另一方的资料如今已难以获得。 暂且搁置“诬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些记载确已提示了一个事实,即在明代中叶之后的地方社会中,相邻、相近区域间不同家族之间常常存在各种矛盾、冲突。
中岛乐章曾研究过明代徽州地区茗洲吴氏宗族遭遇的诉讼纠纷,其中发现吴氏与其他家族的纠纷频繁起来是在16世纪以后,嘉靖年间尤为显著。中岛认为“明代后期乡村秩序的全盘性混乱之中,宗族间的对立,恐怕也因而日趋深刻化了吧”。除了成化、弘治以降整体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秩序的混乱,江南三角洲开发的历史进程,应当也影响了钱氏的生存环境。 如前所述,相关研究已经指出,15世纪中叶之后,江南三角洲的开发重心向东部高乡转移,人口也有向这一区域迁徙的趋势。虽然有蓬勃发展的棉业经济为基础,但集中的开发情势下,环境资源、生活空间的争夺当是不可避免的。 如第二十二世、禄园支钱祀,意图从祖居的奚浦市向南发展,至横塘河一带,置办土地、扩大经营,却引发居住在横塘一带的大族的不满和抵制,令钱祀不得不强行开垦:
横塘诸豪禁诸疆,以不得相籍,力以持公(指钱祀),公暮夜抵诸父兄所,语之故,期旦会横塘。 明日耦耕千人,耰锄棘镢千具,牛百头,一朝而原隰释释。 豪乃咋舌罢去。
尽管借助父兄的力量,很快完成了土地的垦殖,但横塘的大族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合谋不支持钱祀的粮长工作,双方一度械斗:
公(指钱祀)为田赋长,豪相约不输一钱。 公乃悉召会父兄襜衣大帽,乘怒马,人持银铛,收捕诸不偿国赋者。 豪闻之,亦集里中暴子弟以御我。 我数行数止,豪不支,日醵饮。 费意小懈,公袭而驰之,缚渠魁六人诣郡县。 六人向公叩头,约请输为众先, 愿勿系送郡县吏。 公乃罢, 遣之。 余豪尽戢输恐后。
生活在横塘的大族极力排斥新迁入的家族力量,很大可能便是出于维护自身生存空间的目的。 所幸钱氏人丁、财力雄厚,才最终帮助钱祀站稳脚跟。
区域间的家族矛盾,有不同的导火线和表现形式,其中的原因自然多样复杂,但这一时期三角洲高乡地域的密集开发背景,不应被忽视。濑川昌久便有研究指出,宗族间的对立或纠纷,毋宁说是起因于开发已经有一定程度进展的地区,围绕有限资源展开的社会性竞争的激化。
家族内讧方面,最为严重和戏剧性的,当属徐氏家族中徐昌祚、徐鼎祚兄弟。 这一家族悲剧还被徐复祚写进自己的戏曲中,更平添了知名度。学界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已有基本的梳理。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老徐市的“市主”徐栻,与同邑望族瞿氏关系密切,遂将女儿嫁给了瞿景淳的长子汝稷。 不料,女儿在瞿家行为不检。 隆庆三年(1569),瞿景淳去世,在汝稷为父亲守丧期间,瞿徐氏与汝稷之弟汝夔发生了叔嫂不伦之事,几年后被瞿家休,返回徐家 因祖母的疼爱,被休的瞿徐氏,在徐家别院而居,且颇有私财。徐栻只有一子尚德,尚德共生六子,其中徐昌祚、复祚为妾周氏所生,鼎祚最幼,为继室安氏所生。徐复祚有言:“吾母以宽,安母以严,性行既若冰炭,而宵小辈复各诪张其闲,以幸博笑,由是而嫌隙稍开矣。”可见,嫡庶之分、正妾之别,早已埋下了兄弟之间攻讦的根由。
昌祚年纪最长,又独得祖父的恩荫,入仕为官,但他性情不善,“为人忮懻多欲,而又狎匪人。每对人辄盛气,稜稜岳岳,锋利而岸削,即处卑幼,未尝不凌轹其长上,及小便利则又含垢以趋之,以故都不得宗族乡党誉”。 万历十九年(1591),昌祚夫妇贪图被休姑母瞿徐氏的财产,以另立媒约相骗,制造姑母私奔的假象,并残忍地命人将姑母沉河淹死。 此丑事一出,民间便传言纷纷,甚至有人撰写《徐姑传》《杀姑传》《沉姑传》等文,四散于乡里。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昌祚已罢官居乡约五年之久,其时逢分家析产,异母弟鼎祚为争夺家产,欲陷害长兄,于是“借口于杀姑,又罗致十二大罪,揭之当道”。
至此,徐家兄弟的同室操戈开始愈演愈烈:“鼎祚欲重兄罪,乃摭第三兄杀父隐恶,并证入昌祚案中。昌祚称冤不服。鼎祚与诸族人怨家交相诬引,构成大狱。”同年八月,昌祚被逮入狱。鼎祚又派人到狱中行刺,昌祚最后自刎。复祚为替同母兄报仇,“有书讦鼎祚,刻送通邑”,用舆论的力量和因果报应的说辞反讦。鼎祚不胜压力,精神恍惚,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亦死。
徐家的这一桩兄弟相煎,给家族声誉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民国年间昆山藏书家赵诒琛在刊刻徐复祚的《家儿私语》时,仍然微词于徐氏家族:“复祚之兄弟,其行如此。当时之戚族亦凶人多,而善人少。成人之恶,唯恐不力。此三子者,实为无德行之人耳。”万历末年徐昌祚死在狱中后,徐姓家人也逐渐搬离新徐市,到清代前期,连“徐”姓也被从市中抹去,更多的时候以旧有的“董浜”为名,称董浜新市。
——节选自杨茜《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