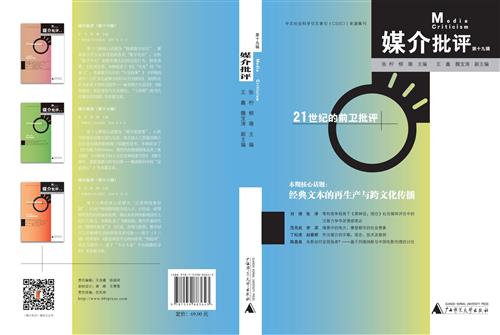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8-01
定 价:69.00
作 者:张柠,柳珊 主编
责 编:王佳睿,陈焯玥
图书分类: 新闻传播出版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出版
开本: 16
字数: 335 (千字)
页数: 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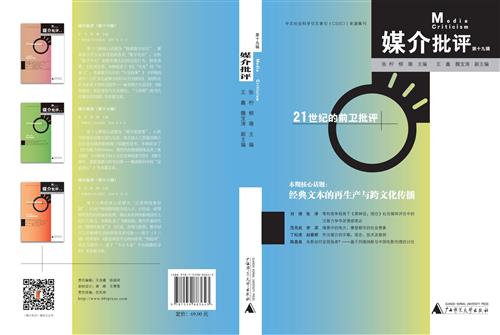
本书的核心话题为经典文本的再生产。经典文本再生产指的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通过现代媒介和艺术形式重新创作和呈现的过程。这种再生产在继承原作精神内核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和创新,使其在新的文化和媒介环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本书通过分析近期的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在技术应用、叙事设计、跨媒介传播等方面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对经典作品进行创新转化的问题。本书关注的其他话题还包括艺术批评、图像与视觉文化、新媒介学理研究、新媒介实证研究等,内容丰富,论说精彩。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学术著作有《叙事的智慧》等。
柳珊,同济大学艺术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媒介文化,出版专著《在历史缝隙中挣扎》《当代新闻评论》等。
核心话题:经典文本的再生产与跨文化传播
/《黑神话:悟空》:一种新的文化记忆形式的可能性∕康春华
/零和竞争视角下《黑神话:悟空》社交媒体评论中的注意力争夺及情感表达∕刘倩张津
/“紧箍”与“王冠”:文化传播视域中的《黑神话:悟空》∕罗建森
/作为经典的《白蛇传》:传统性、当代性和世界性∕高凯朱科
新媒介学理
/作为媒介的字幕:观念、技术及修辞∕丁松虎赵春辉
/幽灵的回返:档案艺术中的“媒介艺术”问题∕陈汉
/跨媒介宇宙:数字时代的跨媒介理论及研究转向∕李斌刘紫源
/数智时代父母自主学习如何助力青少年媒介监管∕战泓玮曾秀芹
/中国脱口秀及其媒介转换的困境
——以《脱口秀大会》等热播节目为例∕杨世全
一种描述
/解构“经典”:晚清报刊中的“水浒”叙述∕潘伟斌
/晚清“报学”知识谱系建构中的话语实践及权力分配∕叶璐
/“在地化”与“有机化”:陕甘宁边区地方党报在乡村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机制∕许加彪刘强
/空间疗愈中人工智能情感识别技术赋能研究∕李麟学金堇惠
/隔膜与破壁:高校美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协同发展的机制与功能研究
——以校史剧为例∕张艳丽曾琢
西洋经
/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与文学研究的范式革新——基于叙事形式的当代演进∕\[意\]埃莱娜·兰贝蒂著李姣译李勇校
影像批评
/电影如何呈现他者?
——基于列维纳斯与中国电影伦理的讨论∕陈嘉美
/电影何以思考哲学?
——巴迪欧电影批评的创发与转向∕李诚婧
/译制电影配音艺术的审美特性
——以1980年代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电影为例∕邱乙哲
/《漫长的季节》:东北衰落及其伦理文化的转型∕王成珊
图像与视觉文化
/是游戏性的扮演,还是性别的颠覆?
——朱迪斯·巴特勒后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扮装Cosplay”现象探析∕赵雯睿
/数字藏品驱动的跨文化传播新路径:基于《中国日报》的考察∕张建中
/艺术乡建:乡村空间生产实践及其社会逻辑∕鲍海波王利民
/嗅景中的地方:摩登都市的社会想象∕范双武李滨
无
本书的核心话题为经典文本的再生产,其亮点之一在于从媒介传播学的角度审视《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对《西游记》经典文本的创新改编,更在于其充分发挥游戏媒介的传播特性,构建起全新的传播模式与受众参与机制。通过媒介的赋能,经典文本得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数字时代实现了跨媒介、跨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传播范本。此外,本书还通过对动画影视作品《白蛇》的技术应用、叙事设计、跨媒介传播等进行分析,探讨了如何对经典作品进行创新转化的问题。
《黑神话:悟空》:一种新的文化记忆形式的可能性
康春华
摘要:《黑神话:悟空》不单是一种电子世代的游戏媒介,更是一种具有交互性、沉浸式和融合性的文化媒介。它基于《西游记》原著世代累积型的文本风格和与时俱进的跨媒介衍生特性,将大量民族艺术和民间文艺形式通过数字技术重新“编码”“转译”,在玩家互动过程中生成动态的文化符号体系,继而生成包含知识、观念、美学的“符号意义”系统。作为文化媒介的《黑神话:悟空》揭示了新的游戏民族审美范式形成的可能性,并重构了年轻受众关于“西游故事”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黑神话:悟空》;跨媒介改编;媒介传播;文化记忆
2024年8月20日,中国首款国产3A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面世。问世至今,玩家、游戏产业、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界对这款游戏的讨论异常热烈。可以说,《黑神话:悟空》构成了2024年度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游戏(本文中的游戏,一般指电子游戏)领域,“3A”指高成本(A lot of money)、高质量(A grade quality)、高期待(A lot of anticipation),即游戏设计者和制作商家花费大量金钱、技术打造的高品质游戏作品。《黑神话:悟空》的诞生不仅为国产“3A”标准建立提供了参照,也向大众揭示了游戏在娱乐产品属性之外,作为文化工业产品在符号和意义价值层面的多重含义。
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游戏叙事、游戏美学、游戏理论批评、文化产业发展等维度对《黑神话:悟空》进行研究,认为该游戏在中国游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改善电子游戏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电子海洛因”的污名化境遇,其鲜明的电子游戏叙事与美学风格也进一步论证了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独立艺术地位。此外,《黑神话:悟空》尤其彰显了在新的互联网技术条件下,游戏这种媒介形态在当代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更为丰富的蕴涵,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一点。
一、游戏作为文化媒介
“游戏”在中西方社会均古已有之,包含了非常宽泛的人类社会娱乐项目。早期的游戏研究主要来自人类学、行为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传播学的诞生,游戏研究对象逐渐特指数字(Digital)领域中的游戏产品。数字游戏是依托于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设备开展的数字化的游戏活动,包含街机游戏、单机游戏、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等。来自曹书乐:《作为劳动的游戏:数字游戏玩家的创造、生产与被利用》,《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2期。20世纪末21世纪初,游戏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方向。2001年创刊的《游戏研究》杂志卷首语《计算机游戏研究:第一年》将数字游戏与媒体(Media)分离,游戏研究正式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气质、兼顾本体与周边的跨学科学术阵地。转引自冯应谦:《游戏研究的国际新近趋势》,何威、刘梦霏主编:《游戏研究读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随着游戏类型、载体、技术和玩法的日趋多样,不同游戏的技术手段、游戏机制和呈现出的媒介形态也更为复杂。因此,游戏研究逐渐形成两种研究对象的分野:操作层面的游戏和作为文化现象的游戏,即“作为技术和手段的游戏”(Play)和“作为现象的游戏”(Game)。从“作为现象的游戏”的研究视阈看,电子游戏作为一个文化文本,不仅要从叙事学和美学等“大文学”视野进行文本细读,也应当从文化传播理论出发,探讨游戏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文化媒介的媒介运作机制和传播效能,从中窥探在技术时代,人类代际经验、集体记忆和精神价值如何灌注于这一具体的媒介形式之中,如何创造全球化时代年轻人所“共有”的文化史。
20世纪末,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数字媒介的发展将会催生新的叙述类型。学者珍妮特·默里(Janet Murray)从叙事理论角度解读数字媒介,在《全景操作平台上的哈姆雷特:赛博空间叙述的未来》中分析探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诗歌、小说、电影等叙事模式,此后她认为当小说、剧本与故事之类的线性模式向多模态、多形式与参与性转变时,电子空间已经发展出自己的叙事模式。爱尔兰学者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ucklich)认为,玩游戏与阅读小说都是符号阐释和符号交互的过程。电子游戏意义的生产过程是与其所处文化环境符号交互的过程,因此可以将电子游戏文本作为一种虚拟文本,从小说理论、诗学、美学等角度对电子游戏进行阐释研究。吴玲玲:《从文学理论到游戏学、艺术哲学——欧美国家电子游戏审美研究历程综述》,《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就国内本土学者研究成果而言,《游戏研究读本》主编之一何威在《数字游戏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八个维度》中认为:美学、故事、机制、技术、文化、影响、历史、产业是游戏批评研究的八个维度。其中的“美学”包含视听语言与风格,“故事”包含叙事、符号、话语、角色。何威:《数字游戏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八个维度》,《艺术评论》2018年第11期。这八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数字游戏批评的框架,也启示研究者,虽然数字游戏的符号系统以及背后的生成链路是复杂的、跨学科的,但叙事、话语、角色、美学研究依然属于游戏本体论研究范畴,在游戏的媒介融合特征中依然不可或缺,并且在新的媒介转换之中焕发出新的特点和价值。
数字游戏作为一种新媒介,具有新媒体和电子文化所具有的互动性、沉浸式和融合性等媒介特征。此外,数字游戏采用互联网技术营造出一种虚拟世界,引导玩家进行交互式参与。因此,虚拟现实也是游戏重要的媒介特性之一,既包括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以“相互隔绝”的方式在游戏中进行隐秘连接,也包含游戏本身的物质、载体、技术与虚拟角色身份、虚拟社区公约等的复杂结合。游戏的基础设施是物质性的,包括游戏服务器、前沿互联网技术等。同时,游戏也受到网络交往规范与社区条款规定等的约束。游戏的虚拟性不仅体现在玩家的身份角色上,也体现在故事情节、游戏景观的建造等。可以说,游戏主创从现实世界获取必要的物质支持,并提取必要的文化元素,进行媒介“转码”和“再造”,从而生成了游戏幻想世界,即“借助于想象力,游戏生成了一个相对自制独立的游戏世界,但它同时又与一个或多个自身以外的世界相关联”转引自刘梦霏:《游戏入史——作为文化遗产的游戏》,何威、刘梦霏主编:《游戏研究读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81页。。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专章讨论“游戏—人的延伸”。他谈到,传统意义上的游戏(Game)“产生一种使人震颤的神奇和欢快的感觉”\[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9页。,同时指出,游戏中体现“大众”(这种大众并非指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参与的事实)与集体生活、社会之间的关系:游戏是大众艺术,“是集体和社会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主要趋势和运转机制做出的反应”,和制度一样,“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9页。,游戏是“集体和社会对任何一种文化主要趋势和运转机制做出的反应”\[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9页。。
麦克卢汉认为,一个特定文化圈内最受欢迎的游戏往往反映的是这个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价值。作为一种媒介的数字游戏,本身处在虚拟—现实交织的框架下,自然无法脱离整体社会物质发展和文化结构并与其相割裂,反而以其特殊的媒介形式脱离社会环境和大众形成新的联结。当技术和文化、虚拟想象世界与现实实然世界通过“玩家”自主的游戏探索过程,不断相互激发,共同生成带有强烈个人性的游戏互动体验时,游戏就不断改写着玩家/用户的媒介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而整体改变着玩家身处的媒介环境。尤其数字游戏是一种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娱乐方式,其中不仅有作为玩家的“心流”体验与审美经验,更有年轻人尚待发展成熟的知识认知模式,因此当游戏文本中有强烈的文化要素时,这种文化元素将在每一次玩家的玩耍(Play)过程中,不断生成动态的符号系统,继而生成传递知识、观念、意义的价值系统,并通过数字游戏表征的新媒体传播方式,让更多人熟知。有论者就曾指出,《黑神话:悟空》既是一部游戏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包含符号、影像、音乐等在内的游戏机制设定与玩家具身参与的文化媒介作品,它揭示了一种基于游戏机制、动态符号变化和多重叙事方式的文化形态。张曦萍:《从“西游文学”到“游戏文学”:〈黑神话:悟空〉的文学破局》,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24年8月31日。
二、“敞开的文本”:《西游记》的跨媒介改编特性
《黑神话:悟空》的爆火,离不开其“改编原型”《西游记》本身跨媒介改编的特性。《西游记》小说或者“西游故事”早已镶嵌在中国人的文化DNA里,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西游记》问世以来,从古典时期的戏曲、话本、评书、绘画,到20、21世纪的电影、电视剧、动画、连环画、歌舞剧、话剧、网络文学等,其跨媒介的改编始终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为例,1986年《西游记》电视剧、1995年香港电影《大话西游》,新世纪初的网络小说《悟空传》,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每一部作品都构成一个时代的影像留存和文化记忆。学者赵敏在《〈西游记〉跨媒介改编创意研究》中梳理《西游记》的跨媒介改编情况时认为,“《西游记》成为每一种媒介艺术的开路先锋,每一种媒介艺术发展之初,都能看到《西游记》的声影。20世纪《西游记》改编史就是多媒介、跨媒介的发展历史”赵敏:《〈西游记〉跨媒介改编创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174页。,“无论在媒介门类的齐全性、形式的多样性、数量的丰富性还是传播地域的广泛性等方面,《西游记》都可以称之为文学跨媒介改编的典范”。赵敏:《〈西游记〉跨媒介改编创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页。
从《西游记》小说文本到西游题材的数字游戏的相关研究,必然要探讨《西游记》的成书特征,以及主题、思想、内容方面的媒介特性。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提出《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至今,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西游记》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发源于唐代史书记载的取经本事,历经数百年民间的传播演绎,最后由明代吴承恩加工定型。《西游记》研究学者竺洪波考证出《西游记》的成书脉络:《西游记》故事的衍生大致沿“史书记载→《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僧西天取经》队戏→《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西游记》词话本→简易《西游记》小说→百回本长篇巨帙《西游记》”的次序发展。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可见,《西游记》经过传统民间社会世世代代的演绎,到明代吴承恩定型成书,后又经历不同时代、不同媒介的改编,这让西游故事始终处于不断被改写、逐渐丰满的过程,这让故事本身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也具有文本意义上的敞开性或者未完成性。这让每个时代都能与西游故事相遇,衍生出其独属的“西游故事”。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学界已有“政治说”“游戏说”“哲理说”“宗教说”等说法。郭健:《建国以来〈西游记〉主题研究述评》,《江淮论坛》2004年第2期。其中“游戏说”的首倡者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提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后世学者沿着“游戏说”思路深入探讨了世俗羁绊、束缚与人自由天真的本性之间的多重辩证意蕴。而孙悟空个体“纯然天真”的心性与外在规约束缚之间的张力,始终是西游题材游戏改编的核心主题。
此外,神魔小说的斗法场景也为其游戏改编提供了素材。《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游戏笔墨大量集中在神魔斗法场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神魔小说”做了如下定义:“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也就是说,“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等意识形态层面的论争,通过故事情节混杂在一起,但各自又有细致的脉络与区分,这是神魔小说的重要特征。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漫长的故事演化过程中,神魔小说逐渐从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中心转向一种单纯的题材范畴的称谓。也就是说,神魔小说包含儒家、佛教、道教等的义理、思想,但叙事过程已经从意识形态斗争悄然置换为对“斗法”本身的大篇幅书写,尤其是对呼风唤雨、用器使咒、驱神役鬼、变物幻形等斗法过程的渲染,“这些套路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并不鲜见,但只有在典型的神魔故事中,它才被推上至高无上的宝座,成为故事的主体和焦点”赵毓龙:《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可见,神魔小说《西游记》本身就有极其丰富且随时代发展的思想资源。它既包含儒释道传统思想的“内核”,又涉及历险、考验、自我修炼等个体成长的向度,与普通人的人生观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它有世代累积型的文本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跨媒介衍生特性,在历史长河中,又沿着通俗化故事和游戏化情节的道路不断演化。大量的神魔斗法场景被各种媒介反复演绎,在此过程中吸纳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与社会精神,这一切构成了跨文本西游故事的特殊内核,让它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中都能焕新与重生。
无论运用何种艺术形态,《西游记》改编往往集中于一对人物关系、两个核心叙事:前者是孙悟空与唐僧的师徒关系,后者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倒反天罡和“降妖除魔”的打怪之旅。概览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游题材改编作品可以发现,1986年电视剧版本用写实风格影像将《西游记》从20世纪民族救亡和阶级斗争的语境中解放,还原原著本身的魅力;1995年香港电影《大话西游》以“无厘头”的喜剧风格颠覆原著、消解崇高;2000年今何在的网络小说《悟空传》以青春视角高扬孙悟空的“个人英雄主义”。而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及2024年游戏《黑神话:悟空》这两部《西游记》跨媒介改编代表作,探讨的是“大圣”成为“大圣”之后,孙悟空“怎么办”的问题:要么再度与权力结构割席、追求自由(《黑神话:悟空》开篇剧情),要么就是丧失了意义和价值感的“中年境遇”(《大圣归来》)。《大圣归来》以动画电影的叙事方式和影像风格探讨的是,大闹天宫之后,在五指山下被压五百年的孙悟空在正义(江流儿、无辜女童)和反派(妖怪势力)的较量中,再度化身为充满力量和勇气的“斗战胜佛”的故事。而《黑神话:悟空》通过“齐天大圣”的消失,指引玩家闯关打怪升级,寻找孙悟空“六根”,来呼唤“斗战胜佛”的重生。可以看出,电影/游戏的叙事原点和动力都是对英雄(初心或理想)的召唤机制,电影是用完整的影像叙事向观众呈现了一幕“英雄如何再度成为英雄”的故事,而游戏邀请“天命人”(玩家)参与,书写专属于自己的“拯救英雄”“寻找初心”的故事。
三、《黑神话:悟空》的跨媒介改编实践
《黑神话:悟空》作为一款西游题材的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将《西游记》作为“前传”,以取经后孙悟空追求自由、放弃“斗战胜佛”的佛位,再度引发天庭讨伐为故事引子。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天命人”这一角色,寻找孙悟空战败后遗落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其中“五根”被五个妖怪私藏,而第六根须战胜二郎神和大圣残躯后获得。因此“天命人”要凭借自己的实力闯过相应关卡,集齐“六根”成为新一代大圣。如前所述,《黑神话:悟空》不仅仅是一个套着《西游记》之壳的角色扮演和打怪升级类游戏,还是一个寻找、拯救和“复活”英雄的古老原型叙事,而这个原型就是承载无数中国人情感基因和集体记忆的孙悟空。白惠元在《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中认为,“孙悟空正是中国制造的‘中国故事’,他从古典名著中走出,闯入现代,不断‘变形’,并成为激变时代的见证者”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229页。。
将《黑神话:悟空》与原著故事情节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已有很多,在此不进行赘述。笔者更为关注的是:《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世界观架构和视听美学风格,如何在原著文本基础上发挥更大的媒介效用。《黑神话:悟空》游戏分为六个章节:“火照黑云”“风起黄昏”“夜生白露”“曲度紫鸳”“日落红尘”“未竟”。寻找“六根”的探险之路,就是玩家与神魔相遇并展开“斗法”的故事。《黑神话:悟空》隐去孙悟空真身,并且让玩家“失语”(游戏中“天命人”自始至终都是沉默的),仅靠奔跑、打斗等形式推进游戏进程,却极大地丰富了配角人物的故事线,比如金池长老、黄眉、黄风大圣的“前史”,猪八戒与紫蛛儿、高翠兰错位的爱,困守于家庭纠葛的悲情角色牛魔王、铁扇公主和红孩儿,等等。《黑神话:悟空》在《西游记》经典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赋予这些配角人物形象更多的表达空间、展开支线和衍生情节,但并不以奇观化、复杂化的剧情为特色,而是让剧情导向一种哲思境界:妖怪如同人世间的镜像,无论是虔诚的高僧还是命运坎坷的妖怪,都无法轻易摆脱权力、金钱、名望等的诱惑,那么人又如何面对这些欲望的深渊?“闯关”之路,也是面临“诱惑”、接受挑战之路,这让游戏目的——寻找孙悟空的“六根”变得更为迫切。可见,《黑神话:悟空》的人物设定、叙事走向与游戏机制是高度契合的,既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有切身代入感和“心流体验”,也更引发玩家在游戏之外的人生思考。
何威在谈到游戏的美学之维时表示,数字游戏具有独立的艺术语言,其核心在于通过对玩家行为的限制与引导,在事先设计的情境规则与随机发生的玩家参与、表演和互动之中,完成千人千面的艺术表达、叙事和抒情。何威:《数字游戏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八个维度》,《艺术评论》2018年第11期。《黑神话:悟空》用丰富的视听语言为游戏剧情和机制服务,也为玩家服务。从视觉要素来看,《黑神话:悟空》人物形象包括“天命人”(玩家)、各路妖怪(打击对象)、猪八戒(打斗型辅助角色)、狐狸少女(叙事型辅助角色),除此之外还包括游戏技术建构起来的“世界地图”。在《西游记》原著中,空间场景往往是横跨天、地、冥、水四境的世外胜景,具有显著的奇幻色彩。而在游戏中,《黑神话:悟空》将原著中带有玄想奇观色彩的场景转化成更粗犷写实、大气苍凉的视觉形象。主创团队披露,为了展现更为逼真和写实的场景,他们采用了大量数字扫描、建模等技术,对全国30多处古建筑群落进行扫描,以便在游戏中还原高质感、高艺术审美水准的场景,而这也是引发现实层面多地文旅项目走红和公众竞相打卡的原因所在。
从听觉要素来看,《黑神话:悟空》中的对话文白夹杂,包括许多民间俗语、俚语,人物之间的对话符合人物角色调性。民谣、说书等民间曲艺的引入,呼应了西游记故事的“口头文学”传统,既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更赋予电子游戏作为艺术媒介的审美内涵。比如为玩家所津津乐道的第二章开篇“无头僧”唱的《黄风起兮》来自陕北说书,内容、韵调和发音都具备粗犷苍凉的审美特色,与黄风岭篇章的整体美学风格是高度契合的。其他章节也是如此,比如第三章“夜生白露”中小雷音寺、巨大经幢的写实主义造景,大战黄眉、三战赤尻马猴等上天入地的打斗环节,配合有强烈人物风格的台词,构成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艺术整体。西游故事作为游戏故事的前史,也作为玩家意识中的潜文本而存在。而《黑神话:悟空》有许多剧情的“隐藏彩蛋”,尤其是“未竟”篇章隐藏着两种不同的游戏结局,需要游戏玩家凭借技术打怪升级和操作触发,因此六章游戏就是六个过关斩将的“关卡”,也是不同的玩家用自己的方式挖掘和丰富游戏叙事的过程,而这也成为激活西游故事文化价值的重返文本之旅。
游戏的视听形象是媒介符号的表征,而玩家的体验、认知和情感参与是对这些符号的反映。《黑神话:悟空》不单纯是一种电子世代的游戏媒介,通过对其叙事、剧情和视听美学风格的梳理可以看出,它也承担着一种文化媒介的功能:经典文学文本内蕴和现实社会状况的复杂交织通过游戏的视听觉符号,抵达和触发玩家的情感机制,由此玩家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能够与经典文本发生新的作用。“游戏世界中的数字技术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信息’或‘事实’,而是价值,是带有观点的‘脑海中的游戏’。”转引自王喆:《游戏民族主义:网络游戏和民族认同的双向连结》,何威、刘梦霏主编:《游戏研究读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55页。换言之,在《黑神话:悟空》中,玩家通过神魔小说“斗法”情节和“拯救英雄”的游戏互动,在虚拟和现实交互的状况中重新把握真实的世界图景。尤其与其他格斗类、闯关类数字游戏不同的是,《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结构和游戏叙事源自《西游记》经典文本,玩家通过角色扮演、打怪升级和视听觉感知,在这样一种全息的敞开式的包容一切的媒介形式中,获得文化传统、古典审美的熏陶,游戏的审美主体也得以确立。
四、游戏“出海”与文化记忆:新的游戏民族化形式
如前所述,网络游戏是一种虚拟和现实多维交互的文化工业产品,它让个人通过“虚拟化身”在虚拟世界中进行充分的沉浸式和交互性互动。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种文化媒介形式,重新让个人(玩家个体)和集体(作为游戏玩家的整体),以及民族形式(民族化的艺术表达)和国家话语(游戏“出海”召唤的民族情感)之间建立联结。《黑神话:悟空》有完整的层层递进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系统,也有完整的视觉美学风格谱系;而这一切,通过技术系统和游戏机制的“编码”“转译”,将当代中国追求文化自信、彰显大国文明风采的国家、民族话语形式渗透到游戏之中;玩家看似自主、自由的游戏过程,依然为原著文本和游戏内在机制所规约和牵引。成长于互联网语境“数字化蜂巢”(韩炳哲语)中的年轻人,作为一种“原子化个体”,通过《黑神话:悟空》这一游戏体验到一种共通的集体情怀和文化情感。有论者认为,在玩家游戏经验中,“互动”和“认同”作为动词存在。互动及认同是主体接受来自多媒介的信息的过程,“游戏民族主义让我们看到,人们如何挪用和混杂流行的媒介元素,在‘玩’的过程中建构认同,最终让玩家自主地成为媒介世界的一部分”。转引自王喆:《游戏民族主义:网络游戏和民族认同的双向连结》,何威、刘梦霏主编:《游戏研究读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59页。
探讨中国国产游戏的“民族主义”基因,要追溯中国游戏的发展历程。邓剑在《中国当代游戏史的思想谱系:从本土现代化到资本与市场逻辑》中梳理国产游戏发展史时认为,民族主义情绪深刻地融入了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第一代电脑游戏的血液,促使“中国意象”的游戏理想主义风格诞生。所谓“中国意象”,指此时推出或将要推出的大部分国产的电脑游戏为表达中国的“在场”,接受与模仿海外游戏的设计思路,运用隐喻式的程序修辞,在视听表层植入中国元素,使中国游戏具有中国气象,以此试图将玩家询唤为具有爱国意识的精神主体。邓剑:《中国当代游戏史的思想谱系:从本土现代化到资本与市场逻辑》,《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时至今日,拥有一款游戏技术、玩法机制、文化基因、审美表达都基于中国本土的高质量游戏,一直都是中国游戏玩家的夙愿。而《黑神话:悟空》的横空出世,恰恰与这样的期待高度契合,因此游戏甫一面世,就激发了玩家们狂热的购买和“安利”举动。
《黑神话:悟空》的确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其中的人物造型、景观建构、民间艺术形式等尤其被人津津乐道,尤其是第二章“无头僧”的陕北说书《黄风起兮》,无头僧以“无头”形象示人,引起玩家思考“头”在何处,而“无头僧”原型塑像的头在大英博物馆,这就是将游戏人物和叙事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再比如山西隰县“小西天”的3D扫描和建模,还原高精度的逼真场景,助推《黑神话:悟空》成为文化“出海”的代表作,这样的例子在《黑神话:悟空》中不胜枚举,已有许多论文从技术与产业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而这类从游戏符号角度连接玩家民族认同的“设置”,既有国外高品质游戏的“竞品”压力,更有主创团队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黑神话:悟空》之所以“出圈”,一方面是因为主创团队对游戏立意、设计和生产环节的主动披露,激发了游戏从业者和玩家关于国产高质量游戏的期待和理想主义情怀;另一方面是因为以中国游戏“文化出海”的策略高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让其获得了更大层面的舆论曝光量和媒体关注。
如前所述,以小说《西游记》为代表的“孙悟空”形象与“西游故事”已经流传400余年,逐渐形成一种非常具有号召力的“民族共同体”想象媒介,也成为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表达文化自信的强大符号载体。而基于《西游记》跨媒介改编而来的《黑神话:悟空》,包含了“民族性、价值性、时代性、交融性和情趣性”王文革主编:《文化创意十五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页。等创意改编的核心要素,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成为承载民族文化自信的新的话语方式。作为数字游戏,《黑神话:悟空》具有非常强烈而浓郁的民族艺术形式,这进一步论证了其作为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也有助于揭示游戏如何从个人记忆(玩家)和社会记忆(公众传播)层面,建构起年轻一代的文化记忆。
德国著名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他认为,人的大脑存在三种不同的记忆:神经(Neutral)记忆、社会(Social)记忆、文化(Cultural)记忆。稳定和维持人的神经记忆的力量来自三个场域:社会互动、交流场域,以及由媒介和符号支撑的文化互动场景。阿斯曼提出记忆的三要素是载体、环境和支撑物,三个维度是器官、社会和文化。神经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各自有着不同的载体、环境和支撑物系统。\[德\]阿莱达·阿斯曼:《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陶东风编译,《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第48—65页。就文化记忆而言,其载体是可以传播的文化客体,比如符号、媒介、人工制品和社会仪式;其环境是通过这些符号创造出自己身份的群体;其支撑物是参与和使用这些符号的个体。虽然《黑神话:悟空》是作为2024年文化热点事件存在的,但《西游记》早已构成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的文化记忆。因此,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解读《黑神话:悟空》对于年轻玩家及更广阔的游戏受众的影响是合适的。这种“文化记忆”在当下而言,载体就是《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产品,以及其形成的文化符号体系,其环境是玩家通过虚拟现实的游戏世界进行游戏的过程;其支撑物则是一个个具体的玩家。
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最有效之处在于阐释记忆三维之间复杂的互动和建构关系。当人的大脑神经元系统储存了“自我”的独特记忆和关于“人”的整体性记忆时,时代和社会就会成为一种整体框架,文化记忆以语言、图像、符号等媒介形式,通过这一整体框架过滤和重构记忆。从这个阐释体系来看,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通过游戏剧情、打斗设计等让个体玩家拥有丰富而鲜明的游戏体验和记忆,而游戏对《西游记》的衍生改编背后透露的是当下的时代情绪和症候,这种时代情绪与加速社会、功绩主义和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等现状相关,那么玩家对《黑神话:悟空》的沉浸式游戏过程,就是让个体记忆、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进行了强有力的互动与建构。也可以说,文化工业产品《黑神话:悟空》通过游戏媒介的符号“编码”和意义生产模式,在年轻受众中,比之《西游记》原著,可形成更为强烈的文化记忆。
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在中国近现代民族革命时代,抑或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时代,《西游记》都不乏优秀的改编实践,这些改编文本始终与当时的时代精神保持互动,并从多元话语结构中寻找支撑和突破口,表达一种或显在或潜藏的“反抗”“重构”话语力量。《黑神话:悟空》也是如此,其游戏世界观核心在于,英雄成为“英雄”之后,如何反抗权力收编、拥有绝对的自由,如何始终具有一种无畏的革命/反抗精神。从思想史看,这依然是20世纪“启蒙”与“革命”变奏的延长线上的“老问题”,但它以3A单机游戏这种“新媒介”形式出现,召唤了玩家的热烈参与感,也让更年轻一代思考自身与时代、民族与家国命运等宏大话题。此外,《黑神话:悟空》继承着前述《西游记》跨媒介形式改编的精神,在将古典文化资源进行现代表达的过程中,发挥“技术的想象力”精神,让这款国产游戏拥有了更鲜明的民族形式。换言之,对于更广大的普通人而言,《黑神话:悟空》是在对潜藏在中国人记忆之中的“西游故事”以电子媒介的形式重新生产、重新讲述,以此重新召唤“孙悟空”的“英雄情怀”;同时也以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年轻受众中形成更具当下性、年轻态的文化记忆。而且,这种具有特殊民族形式的文化符号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跨语种、跨地域的盛行,让游戏玩家打破国家、种族、地域的局限,通畅地交流、沟通和共享一种来自中国民族文化的叙事模式。
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最终获得9.56亿元票房,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观众之间的“自发安利”。也就是说,观众自发的情感价值让这部电影获得了更多的票房和口碑。《黑神话:悟空》也是如此。截至2024年11月18日,《黑神话:悟空》销量已超过2200万份,游戏总收入超过11亿美元(约79.6亿元人民币),并且在第42届金摇杆奖中获年度最佳游戏大奖和最佳视觉设计奖。观点网:《〈黑神话:悟空〉获得第42届金摇杆奖年度最佳游戏大奖》,2024年11月22日。其销量和口碑很大程度得益于海内外玩家的“自来水安利”。不仅国内许多玩家通过视频解读、讲解和写攻略贴的方式“安利”游戏,许多博主用短视频、播客等方式带领观众深入研读《西游记》原著,不少海外玩家更以各种形式向外国玩家介绍《西游记》文本,以及《黑神话:悟空》中每一帧所蕴含的情节故事、视听美学效果、隐藏“彩蛋”,等等。可见,《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产品以鲜明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形式,与全球化时代的“他者”相区分,凝聚成为具有号召力的文化认同感。从《黑神话:悟空》大众舆论和游戏“出海”对外宣传的传播实践来看,它将大量民族艺术的形式通过数字技术转化,既形成了新的游戏民族主义审美范式,也重构了年轻受众关于“西游故事”的新的文化记忆。
总结而言,《黑神话:悟空》是21世纪20年代对400多年前《西游记》富矿的再开掘和再生产过程,也是不断融合时代科技发展与文化想象的再创造过程。《黑神话:悟空》以游戏为媒介形式,不断完善着新的文艺的“民族形式”,也深刻参与了当代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而这,都是《黑神话:悟空》这款文化工业产品所溢出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媒介传播价值,相关话题仍然值得文化传播研究学界继续深入探讨。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