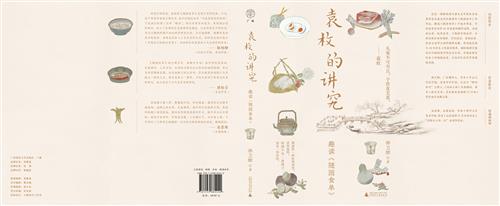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8-01
定 价:68.00
作 者:林卫辉 著
责 编:黎永娥
图书分类: 中国现当代随笔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开本: 32
字数: 200 (千字)
页数: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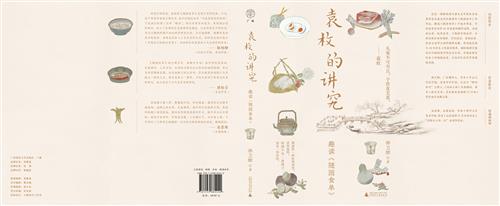
《随园食单》不只是食谱,更是清代文人的雅致生活范本。本书是一部解读清代美食家袁枚及其《随园食单》的作品,精选食单中 40 余道菜肴和茶酒,从粤菜的鲜、官府菜的雅,到武夷山茶、兰陵酒等,呈现一席惊艳无比的随园宴。从食材甄选到烹饪技法,解析袁枚的饮食哲学,看他如何将生活美学融入一饮一食。冒死吃河豚的同窗好友蒋和宁、获康熙御赐豆腐秘方的老宠臣、与之惺惺相惜的郑板桥……全书串连起袁枚与30多位名士的宴饮轶事,描绘他辞官隐居后以随园展开的社交生活,透过名士宴饮看清代官场与民间的社交生活和世相百态。
林卫辉,广东潮州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美食专栏作家,公众号“辉尝好吃”主理人,《风味人间》美食顾问。著有《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寻味》等饮食文化散文集。
序:对《随园食单》中厨者之功夫、食者之心法的首创性解读
前言 做个有趣的人
第一篇 为数不多的几道粤菜
冬瓜燕窝
烤乳猪
端州三种肉
狮子头“杨公圆”
鳝丝羹
剥壳蒸蟹
灌汤饺“颠不棱”
卤鸭
第二篇 官府菜的心思
尹继善家的秘制菜
陶方伯家的葛仙米和十景点心
钱观察家的“神仙肉”
谢太守家的猪里脊肉
蒋御史家的蒋鸡
蒋侍郎豆腐
杨中丞豆腐
王太守豆腐
程立万豆腐
汤西厓猪肺
中秋节的猪头
刘方伯家的月饼
徐兆璜明府家的芋羹
朱分司家的红煨鳗
吴竹屿家的汤煨甲鱼
程泽弓家的蛏干
龚司马家的乌鱼蛋和笋干
章淮树观察家的面筋
高邮咸鸭蛋
运司糕(上)
运司糕(中)
运司糕(下)
孔藩台家的薄饼
春圃方伯萝卜饼
张荷塘明府家的天然饼
唐静涵家的烧鲟鱼、唐鸡、青盐甲鱼
第三篇 谈茶论酒
七碗生风,一杯忘世
袁枚眼中的九大名茶
袁枚至爱——老黄酒
金坛于酒之甜
兰陵酒之厚
药酒之烈
第四篇 袁枚的讲究
吃螃蟹的讲究
美器的讲究
厨师的讲究
请客的讲究
一些美食偏见
吃野味的讲究
后记:探寻袁枚藏在《随园食单》里的小心思
前言:做个有趣的人
写美食,让不少人羡慕,天天谈吃聊喝,很是欢乐。的确,美食令人愉悦,写美食,加上经常接触美食,吃香喝辣的自然少不了,但这不能与有趣画等号,君不见有人把自己吃到肥头大耳一身病,有人“吃人嘴软”,违心地写应酬文章,读来味同嚼蜡吗?在吃吃喝喝中找到乐趣,做个有趣的人,这是我的努力方向,目前还做不到。有人做到了,这个人就是袁枚。
1716年3月,袁枚(字子才,号简斋)生于杭州。袁枚曾说“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袁枚高祖袁槐眉在明崇祯时任侍御史,到了他父亲袁滨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以外出当幕僚养家糊口。好在袁枚的母亲章氏教子有方,“其教枚也,自幼至长,从无笞督,有过必微词婉讽,如恐伤之”。加上家族的读书基因,袁枚五岁开蒙,七岁入私塾,十二岁与其师史玉瓒同中秀才,十八岁时,“受知于浙督程公元章,送入万松书院”,被补为廪生,由公家给以膳食,每年发廪饩银四两。
浙江人才辈出,内卷得厉害,袁枚屡次参加举人考试都不中,他突发奇想,决定去投奔在广西巡抚金鉷幕中当师爷的叔叔袁鸿,父亲给他凑了二两银子,好朋友柴东升又赠送了他十二两银子,走了近两个月,“忍饥受寒”到了桂林。袁鸿把袁枚介绍给金鉷,这改变了袁枚的命运。金鉷特别赏识袁枚,将袁枚的骈文《铜鼓赋》收入《广西省志》,列为 “艺文”首篇,并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送银一百二十两让袁枚赴京。博学鸿词科是普通科举外的“特别科举”,由三品以上官员推荐考生,皇帝亲自出题,偏重文学,考中者可直入翰林院。
出人意料的是,后来成为诗坛领袖的袁枚,参加这次考试时居然名落孙山。袁枚落第后,滞留在京,辗转借住于几位同乡处。大家对袁枚不错,翰林嵇璜聘请袁枚为其子开蒙,就是当家庭教师。袁枚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乾隆三年(1738)年八月,二十三岁的袁枚在京城中举,半年后参加会试,取得二甲第五名。在入翰林院考试时,袁枚又碰到贵人。他的文章因“声疑来禁苑,人似隔天河”,被批“语涉不庄”。
“禁苑”即皇宫内苑,以风吹玉珂之声引发对宫廷禁苑的想象,为僭越之举,但考官之一的名臣尹继善(时任刑部尚书),慧眼识才,为其力争道:“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
袁枚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如通过考试,一般会被留在翰林院。可袁枚不喜欢满文,考试后名列下等。主持翰林院考试的是名臣鄂尔泰,他很欣赏袁枚,但考卷糊名,“故不知系袁枚试卷,据实批为下等。待启糊名,知是袁枚后惋惜之至,但已不可挽回”,袁枚因此被外放为官。
自1742年起,袁枚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四地当了七年县令。任江宁县令时,尹继善是两江总督,联合袁枚的顶头上司江苏布政使王师推荐袁枚任高邮知州,可恰好当年袁枚未完成漕运沿途各县缴钱粮的任务,按例地方官未完成任务“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转,罚俸一年”,受处分期不得升迁,因此吏部否决了提拔袁枚的提议,阻断了袁枚的此次升迁之路。当年冬季,袁枚以侍奉病母为由辞官回乡,两年后因经济拮据,袁枚向吏部提出复职申请,被派到陕西当县令,这比他几年前在富庶的江南可差了一个档次,到陕西仅两个月,袁枚的父亲去世,他借机又辞官了,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袁枚在江宁知县任上时花三百两银子买下了随园,他在《随园诗话》中说:“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他在《随园记》中说:“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他在给友人程晋芳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既然文人不能再走当官发财的常规之路,袁枚决心另辟蹊径,“不受文人之厄”。传统的知识分子以经商聚财为耻,甚至一谈到钱就脸红,袁枚却说:“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他以随园为基地,综合开发利用,开启了他精彩有趣的五十年后半生。袁枚的“生财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随园从私园变为公园,把随园的围墙全拆,免费向游人开放。“放鹤去寻山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随园的池沼楼台,奇峰怪石,外加书画、图章、法帖等各种古玩器具和海量藏书,就是当时的 “活广告”,很多人都由此知道了江宁小仓山有个归隐的大诗人袁枚居住的极妙的去处,于是慕名而来。袁枚一下就“红”了,随园也变成了南京的游览胜地,文人墨客经常聚集在此论诗唱和,而袁枚酷爱交友,在此大摆宴席招待各路名士。各级官员无论出差还是路过,到了南京都会去随园看看,而且当地的地方官会在随园设宴款待来宾。
二是出租经营。据袁枚孙子袁祖志在《随园琐记》中记载,袁枚将随园 “东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户承领种植”。佃户们在随园种植粮菜果木,饲养家禽,袁枚不仅每年可收租利,且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宴客所需,亦可由佃户供给。除此之外,1751年,袁枚在安徽滁州所购田产亦渐有收益。
三是卖文。因袁枚在文坛地位日隆,出高价请他撰写传记、序文、墓志者渐多,许多达官显贵,都以让他为自己的父祖写碑传墓志为荣。扬州有一安姓的巨富,刻了一部书,以两千两银的价格请袁枚题跋。
四是出版畅销书。袁枚自刻其小仓山房各种著作,随园内有“南轩”,即是专门收藏其著作刻板之所。主要传世的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及鬼怪小说《子不语》《续子不语》等,这些书在当时是畅销读物,签名版更是价值千金。五是开学堂办教育,招收学生。他广招学生,尤其女弟子,随园女弟子超五十人,这些女弟子多是江南名士或官吏的妻妾、女儿。收徒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袁枚对自家产业经营有方,晚年时已有“田产万金余,银二万”,而其他书画、图章、法帖等古董藏品亦不少。正因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袁枚才能扩建随园,广邀朋友,宴饮游乐,四处壮游,同时还能安心进行诗文创作,而取得非凡的成就,安心过着潇洒滋润的隐居生活。
随着袁枚的诗《所见》《秋海棠》《推窗》和文《随园后记》《与薛寿鱼书》《黄生借书说》等入选不同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袁枚的不同创作风格更多为今人所接触。在文学创作上,袁枚倡导以真情、个性和诗才为核心的性灵说,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他所谓的“性灵”,是集性情、才情于一体,追求清妙真雅的诗文风格。他的性灵之风,在当时风行海内,蒋子潇《游艺录》中记载了性灵说在当时诗坛的反响:“乾嘉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袁枚认为“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而且 “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他还提到 “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因为“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袁枚在乾隆后期取代沈德潜主盟文坛,成为乾隆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之首。
袁枚可谓著作等身,从乾隆元年(1736)写《鱼塘怀古》开始,到嘉庆二年(1797)去世,六十年辛勤创作,留下古近体诗四千多首,是中国古代诗人中写诗最多的人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袁枚编成《随园全集》六十卷,此外编有《小仓山房外集》四卷,十五年后又补编了一次诗集、文集,各增至三十二卷。最后诗集增至三十七卷,文集增至三十五卷,骈文集增至八卷。此外,加上《随园诗话》二十六卷,《子不语》三十四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袁太史稿》一卷,《牍外余言》一卷,还有《随园食单》一卷。
吃货们了解袁枚,主要是因为他的《随园食单》。这是袁枚数十年美食实践的沉淀。该书以随笔的形式,主要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记述了袁枚认可的三百二十六道南北菜肴,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饮食名著。不仅如此,《随园食单》里还藏有袁枚太多的想法,其中提到数十位人物,提及这些人物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尊重知识产权,哪道菜出自谁之手,他就把那个人记下来,让其“食史留名”;二则是对于不便介绍的朋友,他有意识地以各种云里雾里的称谓将其加入书中,这在文字狱特别严重的乾隆年间,是一种对对方的保护,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袁枚是一个对亲友肝胆相照的人,他奉母至孝,抚养堂弟和外甥,迎养寡姐。袁枚曾说:“御下过严则威亵,训子弟过严则恩衰。”他对待朋友也很好,朋友程晋芳去世后,他焚烧了五千两银子的借据,这件事被写入《清史稿》,他自己却从未提过。朋友沈凤没有儿女,沈凤去世后,他每年都会去镇江为其扫墓,去世前还在遗嘱中将镇江扫墓之事交给儿女。他对仆人都能做到以礼相待,以恩相交,不摆架子。
在四十六岁那年,袁枚请相士胡文炳给自己看相,胡相士说袁枚六十三岁得子,七十六岁寿终。果然,袁枚六十三岁那年老来得子,于是他对七十六岁寿终坚信不疑。七十六岁那年患了腹疾,通达的袁枚给自己做了一首挽诗《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挽,邀好我者同作焉,不拘体,不限韵》,还邀好友们为他写挽诗。那一年除夕,他整好衣冠,与家人一一告别,然后坐以待“毙”,却迟迟等不来死神,于是一连写了七首七绝以示庆贺,命名为《除夕告存戏作七绝句》。看透了生死的袁枚继续其洒脱自在的人生,游山玩水、探亲访友、广收弟子、吟诗作对,好不快活,直到嘉庆二年(1797)九月痢疾加剧,袁枚自知来到了生命的终点,赋诗两首留别故友和随园,并口述遗嘱,十一月十七日从容离世,享年八十二岁。
袁枚坦言自己 “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一个如此有趣、有情有义之人,很值得后人学习。从《随园食单》中读出一个真性情的袁枚,是我的心得,也是写作本书的目的,希望你喜欢!
——选自《袁枚的讲究:趣读<随园食单>》,林卫辉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研究中国饮食,袁枚的《随园食单》是绕不开的经典。不过,高产美食作家林卫辉认为,也不必把这本书“当成美食圣经供奉”,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本“趣读”。他以原著为出发点,系统地分类和研读,加入了宏观的历史地理背景概述,以及作者生平的补充,并且以微观的现代食品科学研究方法,尽可能推断、破解和复原其中的食材及其加工工艺和烹饪方式。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王权政治背景下,百姓的生存智慧和士大夫阶层的审美。
——陈晓卿(纪录片导演、美食作家)
一部《随园食单》,就是从格物中来,亦从自省中来。这是中国古代饮食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之作。或许袁枚的《随园诗话》有言之过滥的弊端,但《随园食单》却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趣的美食经典。而林卫辉先生以一个既有文献修养又深耕厨艺研究的学者之功力,做足形下之功夫,调动形上之参悟,对《随园食单》作了一番现代诠释,其中对有关厨者之功夫、食者之心法、为主之妙方、为客之受用,都作了首创性的解读。
——罗韬(资深媒体人)
《随园食单》风行两百年,谁解其中味?此中有饮食真味、宦海情味、人生况味,全凭林卫辉先生以看似轻松的笔调,首次为读者揭秘发覆。也是他继《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为苏轼立一别传之后,再为袁枚立一别传。不仅大有功于饮食文化史的研究,也大有功于古代文学史的研究。
——周松芳(文史学者)
青瓷碟子摆三样,整蟹敲开壳,膏如凝脂;灌汤饺正在锅中滋滋响;卤鸭已经去骨,另备酱料;掐开刘方伯家的月饼,里馅的核桃仁滚进酒盅。琥珀色的酒里漾着旧年月,园中草木自在荣枯。袁枚写食单时,约莫也这般:三分烟火气,七分故人情。个中讲究三言两语怎能概括?且听林卫辉老师抽丝剥茧,娓娓道来。
——宋思维(水墨画家)
研究中国饮食,袁枚的《随园食单》是绕不开的经典。不过,高产美食作家林卫辉认为,也不必把这本书“当成美食圣经供奉”,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本“趣读”。他以原著为出发点,系统地分类和研读,加入了宏观的历史地理背景概述,以及作者生平的补充,并且以微观的现代食品科学研究方法,尽可能推断、破解和复原其中的食材及其加工工艺和烹饪方式。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王权政治背景下,百姓的生存智慧和士大夫阶层的审美。
——陈晓卿(纪录片导演、美食作家)
一部《随园食单》,就是从格物中来,亦从自省中来。这是中国古代饮食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之作。或许袁枚的《随园诗话》有言之过滥的弊端,但《随园食单》却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趣的美食经典。而林卫辉先生以一个既有文献修养又深耕厨艺研究的学者之功力,做足形下之功夫,调动形上之参悟,对《随园食单》作了一番现代诠释,其中对有关厨者之功夫、食者之心法、为主之妙方、为客之受用,都作了首创性的解读。
——罗韬(资深媒体人)
《随园食单》风行两百年,谁解其中味?此中有饮食真味、宦海情味、人生况味,全凭林卫辉先生以看似轻松的笔调,首次为读者揭秘发覆。也是他继《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为苏轼立一别传之后,再为袁枚立一别传。不仅大有功于饮食文化史的研究,也大有功于古代文学史的研究。
——周松芳(文史学者)
青瓷碟子摆三样,整蟹敲开壳,膏如凝脂;灌汤饺正在锅中滋滋响;卤鸭已经去骨,另备酱料;掐开刘方伯家的月饼,里馅的核桃仁滚进酒盅。琥珀色的酒里漾着旧年月,园中草木自在荣枯。袁枚写食单时,约莫也这般:三分烟火气,七分故人情。个中讲究三言两语怎能概括?且听林卫辉老师抽丝剥茧,娓娓道来。
——宋思维(水墨画家)
“不将就”生活美学的极致实践,传承千年的生活理念,中国饮食文化的巅峰缩影。
人生百味,不过一席随园宴。
乾隆年间的诗坛领袖,也是历史上最会吃的文人;他辞官归隐,却把日子过成了诗。他不仅是美食家,更是生活美学的鼻祖!他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却反对铺张浪费;他追求美味,却更看重饮食背后的情趣与境界。
清代比谁都懂生活的美食家,23岁中进士,没做几年官34岁却辞官归隐,建了一座随园,吃遍江南,写下一本让后世吃货膜拜的《随园食单》。这本书不只是一本菜谱,更写透了中国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
冬瓜燕窝汤讲究“以柔配柔、以清入清”、鳝鱼需“现杀现烹,现熟现吃”、卤鸭必先“去骨”等粤菜做法,从食材选取到搭配均精细得很;豆腐蛏汤之称绝在于蛏子的肥美,风肉的精妙在用盐比例,猪蹄膀神仙肉的关键在两钵合之……官府菜制作也深刻蕴含袁枚的烹饪哲学。从龙井到花雕,从泡好茶先“藏好水”、黄酒讲求“以狠为佳”,袁枚的“茶酒哲学”中呈现的是对风雅生活的极致讲究。
袁枚用一桌菜讲透待客之道,比如“戒耳餐”,批评贪图名贵食材的虚荣行为,认为“豆腐得味,远胜燕窝”,用大碗盛淡而无味的燕窝不如碗中放明珠百粒;“戒目食”,反对量多、讲排场,40余道菜的宴会,回家后仍需煮粥充饥,因菜品粗制滥造。这种对一只碗、一席宴“不将就”的讲究,背后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礼仪与审美。
序:对《随园食单》中厨者之功夫、食者之心法的首创性解读
罗韬
袁随园道广才高,论才性的放旷,世情的洞达,学问的博雅,识见的超卓,诗文的妙趣,都可与苏东坡相颉颃。但他去今日近,声名又一度凌越一世,享不虞之誉,必有求全之毁,故成了后辈诟骂的对象,读过点书的人几乎都借骂袁以自鸣其高;而东坡遭际坎壈,又去今日远,骂东坡之人如朱熹辈,反成被骂之人,东坡污垢尽洗,玉洁珠明,今日教授“名嘴”辄以誉苏为时尚,说得余香满口,其实多属未饮先醉。庸众之所非者未必非,庸众之所是者未必是。
骂袁随园最狠的评语,曰“名教罪人”,略晚于他的几位“文化名人”,一面骂他,一面居然亦步亦趋。毕竟,随园之行为,“不外人情”而已。所以我对史上之“名教罪人”,都多增三分看重。随园诗曰:“有目必好色,有口必好味,戒之使不然,口目成虚器。”就算今日之正人君子、才媛淑女,亦未必敢这样说。他是这样想,就这样写,也这样做的。
庄子说过一句很“不庄子”的话“嗜欲深者天机浅”。但对于随园而言,却往往在嗜欲深处悟天机,他夫子自道“平生品味似评诗,别有酸咸世不知”。所谓“别有酸咸”,正是机微所在。中医有句话,叫 “舌为心之苗”。这话说得真好—舌之妙用,正在格物与自省之间—味之来源是妙用食材,味之领略则存乎一心。他的一部《随园食单》,就是从格物中来,亦从自省中来。这是中国古代饮食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之作。或许他的《随园诗话》有言之过滥的弊端,但《随园食单》却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趣的美食经典。而林卫辉先生以一个既有文献修养又深耕厨艺研究的学者之功力,做足形下之功夫,调动形上之参悟,对《随园食单》作了一番现代诠释,其中对有关厨者之功夫、食者之心法、为主之妙方、为客之受用,都作了首创性的解读。说卫辉是随园功臣,是恰如其分的。
袁随园论食,首重一“品”字。在我看来,品有三义:一曰品格,当然首先要免俗,不能一味好华斗奢;二曰品类,就是味有多方,察类明故,知赏异量之美;三曰品尝,就是以舌为本,切忌“耳餐”。这从他论豆腐之美,可以见其品:“何为耳餐?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这其中包含一个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平等二字,这全方位贯穿于他的谈诗论世待人,乃至品食中。他的诗,有“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而对于食,有“豆腐得味,远胜燕窝”。这就是一个主张去除成见、一切平等的随园之品。
袁随园论食,一反“君子远庖厨”之迂,他为一个“法”字,每问师于庖丁。这时,林卫辉先生经常忍不住“现身”现场“相与谈艺”。如随园谈到 “双钵蒸蹄膀”,蹄膀不小,要一个钵套上另一个钵才盖得严实。但严实不是第一要义,要义在哪?卫辉分析:这种方法,使得外面的水蒸气进不去,但里面的酒精在七十八摄氏度左右开始从两个钵之间的空隙中挥发出来。这个过程也是酒与蹄膀产生酯化反应,生成具有芳香气味的乙酸乙酯的过程。如果用过于严实的盖密封,水蒸气进不去,但酒也出不来,蒸出来的蹄膀酒味过浓。随园只是“道其然”,卫辉是“道其所以然”。此类精彩诠释,书中比比皆是。想随园听了,也要说“后生可畏”。
此外,一个“兴”字,是食家不可或缺的。食,有所谓“文食”,可以品其致;有所谓“武食”,可以尽其兴,这亦是酸咸以外的妙处。袁随园谈到中秋节如何食掉一个五斤重的红焖猪头,如何尽兴享用这凡人眼中的粗物:他请来几位朋友,大中午先“调虎离山”地拉他们出去游山玩水,到天黑月明才回转返家,此时大家饥肠辘辘,以前穷人说 “过午当肉”,饿了吃什么都香,一个大猪头被噍吃殆尽,不在话下。对此卫辉评:中秋佳节,金陵胜景,志趣相投的朋友,居然还有一个猪头“调味”,在袁枚笔下,即便形态粗陋的猪头也上得了台面,一样雅趣盎然。一个猪头得到了最佳的待遇,这就是食之“兴”了。
回味旧食,常生感慨。一个“慨”字,应该是最深沉的味了。当袁随园回忆老友陶易家的十种点心时,生出“自陶方伯亡,而此点心亦成《广陵散》矣。呜呼!”感慨良深,其中着一“亡”字,正是刘知几所谓“用晦”,卫辉没有轻易放过。对这曲笔之意,他调用了《清史稿》《随园诗话》《子不语》等材料,对江苏布政使陶易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遭逢的文字狱作了深入的考察。陶易是随园老友,与其心心相印,且为官清正,其辖内一已故举人的两句诗,被小人深文周纳,检举到朝中,乾隆皇帝断为反诗,要严加追杀。陶易生怕众人蒙此瓜蔓之祸,加以回护,即被解京问斩。随园比之为冤死的三国名士嵇康,于是,借不能再食陶夫人手造的“十景点心”,而发出“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感慨。如果没有卫辉这一番爬梳细考,我们对那“呜呼”二字的深沉感慨,就会一眼滑过,辜负了随园文字背后的苦心。
由此上溯,随园少年科第,但三十四岁即告别官场,自放于江湖,自营一种风流佻达的狂奴意态。此时,不是正逢所谓“康乾盛世”吗?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随园看来,这 “盛世”,是有道乎?抑无道乎?呜呼!
——选自《袁枚的讲究:趣读<随园食单>》,林卫辉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