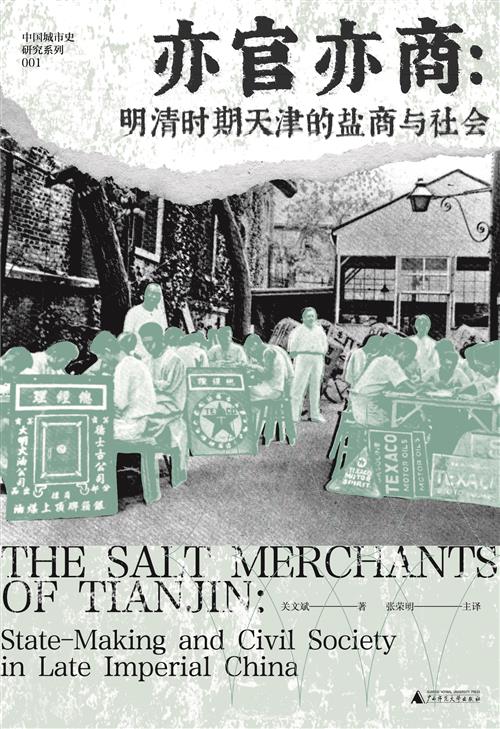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6-01
定 价:88.00
作 者:关文斌 著;张荣明 主译
责 编:陈焯玥
图书分类: 地方史志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地方史志
开本: 32
字数: 284 (千字)
页数: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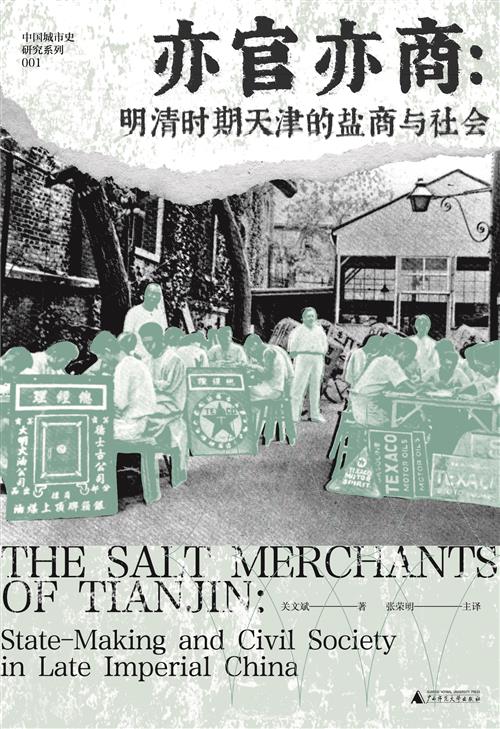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讲述天津盐商群体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史著作,通过盐商的视角,揭示了明清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复杂互动。全书以盐商为核心,立体剖析其在经济发展、家族治理、社会文化网络构建中“亦官亦商”的矛盾性:一方面努力经营社会网络,向朝廷捐输,与士人交游,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其他家族互通有无;另一方面服务桑梓,用心于地方慈善事业,积极参与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业。书中,作者考索了天津大盐商家族的命运沉浮,系统梳理其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从积极参与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数百年历史,还原清代盐税征收、引岸制度运作、民商纠纷等细节,呈现了一段别样的天津明清社会生活史。
关文斌(Kwan Man Bun),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博士,师从黄宗智、施坚雅教授。历任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辛辛那提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荣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荣休),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导言
第一章天津城
天津之军事驻屯
天津与漕运
天津与运河贸易
水文与水灾
1644年之前的屯垦
1644—1911:治水与垦田
天津人
第二章盐榷
清代的盐务管理
长芦盐区的运作
盛清的休养生息
繁荣的代价
国家财政需求的增长
走私、贿赂与利润
第三章家族与情、理、法
家族经济
家长
家族的投资
矛盾与冲突
家族商务的风险
分家与国家
分家的遗产
第四章网络文化
社会网络政治与文化
张氏家族
安氏家族
查氏家族
游园、诗社和书画的世界
第五章社会
骄奢的生活方式
公益和慈善事业
水会
盐商与太平天国运动
地方教育
第六章变革的时代
盐业的发展
投资工业
资金短缺和商务公所
天津商会的成立
天津商务总会的活动
铜元危机
1908年银色风潮与洋货进口危机
严家与橡胶股票风潮
第七章多变的政治
盐商的策略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地方自治与商人
与政府冲突的加剧
君主立宪运动
敌人和朋友
有组织的对抗
第八章危机
借款
灾难
解决
结局
结论
附录一(A)接受长芦盐商养廉银和其他津贴的政府官员清单
附录一(B)各地官员收取盐商的年度规费(1911年)
附录一(C)五月份某盐子店收入和开支情况
附录一(D)长芦盐税年表
附录二清代长芦盐商部分捐输
附录三(A)地方教育
附录三(B)城市的公益与慈善事业
附录四
表1长芦盐商部分贷款清单
表2十名破产盐商及债务情况
表3欠各银行贷款本息情况
地图1黄河的变迁
地图2天津及其郊区
地图3(1)长芦盐区
地图3(2)长芦盐价区
地图4天津城街区
修订版跋
译后记
导论:盐商与天津社会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午后,百余名行商、善堂绅士、村正均着大帽,奔波于天津各个衙门之间。在绅商们的坚持下,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陈夔龙不得不屈尊接见,恭听代表们力陈因长芦盐商拖欠外国银行贷款、清廷介入而酿成的风潮。绅商们一再恳请总督立即开释长芦纲总、天津商会总理、企业家、书法家、慈善家王贤宾——他被视为天津“必不可少”之人,以及其他被牵连抄家的“累商”。
当然,在王朝政权统治下抄家并不罕见,而享有专卖特权的盐商更是一个备受非议的群体:
捐职充商纲总当,一时奢丽众称扬。
吾津富贵无三辈,净洗双眸看后场。
他们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又侵蚀着整个官僚体制,供养一大批贪官污吏。得之既易,挥霍亦不吝惜。饱食终日,附庸风雅,恒为士类所不齿;夸豪竞富,钻营射利,尤招物议。无论身陷囹圄,抑或家业凋零,盐商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可是,沿用对盐商的传统态度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王贤宾及其他“累商”的遭遇,正如《大公报》当日所记载的:“各界绅商,颇具热心,较之同舟其互相倾轧者,大有霄壤之别。”
这个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宋代起,天津从穷乡僻壤逐渐演变为行政中心:县、府、省各级衙门所在地,长芦盐运使、海关道、直隶总督驻节地。但是,这些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能完全控制天津并渗透到基层社会。国家一方面要从经济活动中得到税收,另一方面又得控制社会,才能维系其政权。清入主中原,可以于马上得天下,然而不能在马上治之。清朝建国的洪业,与它采取的财政制度有密切关系。跟十七世纪的欧洲诸国不同,清廷并没有将盐务改归官办,而是有所选择地继承了明代的官商专卖制,一方面解决了部分饷源,另一方面在利诱之下,吸引了一批富民对新政权的支持。这一政策对天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津的商民在支持清政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天津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逐渐参与地方事务,其中盐商的表现尤为显著。他们逐步演变为绅商,影响力甚至超越科举出身的士绅、在籍官僚。在太平军北伐兵临津沽、帝国主义侵略中华的巨变中,这些绅商扮演过重要角色。义和团运动以后,他们投身于地方教育,资助了地方自治、选举等种种“新政”。本书主要部分就是力求再现他们的历史和故事。
另外,本书还探讨了国家政权、官僚体制与地方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有关的理论著述,多以欧洲经验为准则,这些社会科学家恒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和相应的官僚体系作为现代国家的指标。自十五世纪开始,欧洲诸国君主陆续将兵权收归己有,而榨取经济资源的权力机构,在十九世纪初形成。此时,包商或中介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包税制也被视为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与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
在这个标准化的政治社会发展模式指引下,城市和市民的地位亦有较大变化。一方面,曾经享有高度自治权的都市居民,交出了他们的自主权来换取代议政制;另一方面,商业和产业革命也把经商逐利变成文明的表征,“事事讲求理法,不以执着私利为准则”,一个“彬彬有礼”的市民阶级由此兴起。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以及后来的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更进一步提倡无限制地追求私利,主张通过竞争得到并充分使用资源,从而达到生产最优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而不论出身的市民,从家庭和教堂的枷锁中彻底解脱出来,在咖啡馆、旅社、沙龙像朋友一样聚首。通过平等的讨论和争辩,他们学会客观、宽容、超然、尊重集体意志,形成民意。这种理性的讨论奠定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对抗并限制绝对君主的政治权力。
可是,这种对市民社会的高度评价并没有给黑格尔(Georg W. F. Hegel,1770—1831)造成深刻的影响,他持一种较为消极的态度,因而让这一概念变得混乱。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不是人类获取自由的社会条件,而是历史创造的。个人生存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道德责任胜过他或她个人的需要;但是,一旦个人走出家庭,通过生产和在市场上交换其劳动产品,竭尽全力地满足私欲,这一道德规范便不复存在。因此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私利与私利之间无休止厮杀的战场,是放纵、苦难、道德堕落的深渊。他认为,市民社会必须处于国家的超级智能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这些五花八门的“市民社会”概念,近些年来再度受到重视。一方面,哈贝马斯(J. Habermas)强调自十八世纪以来,英、法、德诸国政治上活跃并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是如何通过公共传播媒介、理性的辩论而形成“民意”,从而为社会提供一股凝聚力的。另一方面,无论美国自由主义或保守派学者,以至拉丁美洲、东欧的政论家,也都把市民社会跟民主制度画上等号,认为它的发展,既可制衡国家权力,亦可解决公益和私利之间的矛盾。
种种“市民社会”理论尽管各具特色,但实际应用起来,仍不免有共通的问题和矛盾未能解决。国家和官僚政治的角色仍然混淆不清:它既是市民社会的卫士,也是市民社会的对手。在洛克看来,市民社会代表了力图摆脱封建制度和国家控制的中产阶层。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中产阶层还要求国家通过立法——财产法、契约法、雇佣法、继承法,建立一种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某些对市民社会的论证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非对抗关系。确实,从理论层面看,市民社会可以与国家共同发展,或一同萎缩,而不是相互排斥。
作为一种理想的类型,这一概念也受到了历史的挑战。现代欧洲人对社会与国家的区分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取决于历史发展状况,因各自的社会、地理条件而异,从而导致了市民社会传统极为显著的差异。甚至在被认为最早出现市民社会自由民主传统的英国,也存在着地区差异。通过对英格兰东北部的达勒姆(Durham)的研究,詹姆士(Mervyn James)发现,作为工业化和卷入全国以至世界市场的结果,这里的旧贵族和以血统为基础的地方绅士为新兴的企业家、专业人士所取代。但这些新兴的地方精英并不足以使达勒姆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或抗拒伦敦中央政府的政策。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企业家、富商巨贾、银行家、贵族互相通婚,彼此扶持,构成了一个能左右国会、国家以至殖民地政策的关系网,跟他们的苏格兰同胞所想象的市民社会风马牛不相及。在这民主面具后面运作的是门槛极高的会所、俱乐部、非请莫入的客厅。历史上的市民社会并不全是以自由结社、平等、公开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财富、庇荫、同学及同事等关系网之上的。
林林总总的市民社会理论同样引起了不少争议。姑且勿论英国的例子与历史差距有多大,哈贝马斯本人就反对把他的理论套用到其他类似的历史现象中。援引这些以欧洲经验为准则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也诱发了不少新问题。以盐务为例,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演变过程恰好颠倒过来,从官运官销开始,逐渐转变成官督商销。虽然两种制度都能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财源,但是因为欧洲经验认定包税制是一个薄弱政权的特征,所以中国以至其他采取包税制的地方,便被视为“东方”的悖态,或者说违反“常规”。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自治权。受韦伯的影响,中国的城市被认为是行政中心。侨寓的行商会眷恋原籍,告老还乡,这意味着城市商人的市民意识极为浅薄。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下,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利用城市这一空间来争取经济和政治权益。
另一方面,罗威廉(William T. Rowe)借用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汉口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把这座城市描绘为有广阔腹地的都会。他认为,在外国商人到来之前,这里精明老练的商人们就已活跃于许多地方事务中,享受着相当大的政治自主权,并进行着合法的自我管理。这些平民在沉浸于这种非政府的公民氛围之中的同时,还作为一种与强大的国家相对抗的制衡力量(如果不是挑战性的话),为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奠定了基础。冉枚烁(Mary Rankin)对浙江的研究也强调,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必然的。她对市民社会和公民环境氛围做了细致的区分,认为社会活动可分为官方、公共和私人的。从晚明开始,地方公共事务有越来越多的非官方士绅参与(也有商人参与,但以科举出身的士绅为主)。到十九世纪末,市民社会终于在中国出现。
这些论点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仅就与国家政权抗衡的职能而论,余英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市民社会没有,也不需要经济基础。一箪食、一瓢饮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朝为官,抑或在野为民,都以天下为己任。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囿于组织能力和资源限制,国家政权并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实际掌管地方事务的是在籍官僚、有功名的士人,以及这些士绅领导的宗族,他们根据相对力量、地区的差异,构成各式各样的“体制外治权”。有些史学家则追溯自宋代以来地方公益事业的产生,对近代绅士由体制外演变成“体制内”治权是否反映了一场深刻而重大的社会变化表示质疑。把既成事实变成合法机构,充其量只是传统内的变化,并没有突破传统的范畴。还有一些史学家则指出中国缺乏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十九世纪的中国,工业企业还极为薄弱,商人和商业资本仍占主导地位,它的蓬勃发展和二重性,意味着中国社会与一般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反比。总而言之,无论作为一个概念或史论,“市民社会”都有许多可以商榷的问题。
本书将以天津为例,对明清市民活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作进一步探讨,从史实出发,尽量避免套用某些理想化模型来解释或预测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国家与社会并不像理论构思中那样势如水火,而是在不同范畴、层次中同时互相影响、渗透,既有合作,也有排斥。地方精英领导下的种种社会服务事业,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国家政权,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他们的财势和人际关系。国家与地方微妙的均衡,由于商人参与而更趋复杂。特别是天津的长芦盐商,既拥有官盐专卖权,与王朝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在种种社会活动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他们能否为士流所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为了全面考察商人的社会环境,需要考察这一社会环境的形成过程、经济基础,以及其中个别成员的生态和经营方式。
本书的研究取向,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国家和社会怎样在不同的层次中互相影响。所谓“国家”并非铁板一块,“社会”也不是完全齐一的。清廷、中央以至地方官僚系统,都有不同的利害关系,都各尽所能攫取最大的权力。这错综复杂的环境给各色地方势力,上至士绅、商绅,下至袍带混混,提供了存在和角逐的空间。在国家体制以外,这些急公好义的地方精英孕育了饶有特色的市民文化和作为“卫嘴子”的自豪感(如果不是市民意识的话),帮助天津渡过了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难关。长芦盐商和他们的买卖也混淆了明清时期的公私经济。盐作为日常必需品之一,无疑能提供一种稳定的财政收入,因此历朝历代都将盐榷之权牢牢地控制在手,若盐商不上税,即以贩私盐论处。清承明制,虽有损益,但还是以保障财政稳定和民食为宗旨,将专卖权授予世袭的包商包额认办。但是这种将国家部分业务和职能私有化的措施引起了极大争议。盐商挟势横行,掺土使水,偷斤减称,是为末端;为牟取暴利而公行贿赂,也导致了种种腐败政治现象。无怪乎蒲松龄尖锐地指出:“朝廷之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其私者也。”换言之,“官”与“私”实际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权势与财力转移而变化的。通过对盐商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探讨商业资本的二重性对明清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
我们将首先从宏观上考察天津城市化的背景,详细探讨天津城在十六世纪前如何从一个军事据点发展为沿海要塞。从十六世纪开始,天津逐渐发展为中国北部的一个主要商业都会,其腹地范围远远超出河北平原。在这一过程中,历代发展农业、沿海和大运河贸易政策的变更,既促进又限制了天津城市经济的成长。
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微妙作用也反映在长芦盐的销售方面。第二章将探讨长芦盐政的运作——盐既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又是私人的买卖;既为国家保证了税收,又让国家不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翻开历朝会典、盐法志、户部则例,以及明清律例等官书,所见盐榷法网不可谓不严,但文献中亦可见到大量赏借、捐输、帑利等“盘剥”盐商的记载。然而,商人亦通过陋规、节敬、报效等手段,得到中央以至地方官吏的默许和认可,得以放手追求额外利润。贪污无疑应受到批评,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视为政治、社会、经济领域间的博弈。
盐商的私家经济和他们的许多民事诉讼,同样也带着国家、社会、经济间种种矛盾的烙印。第三章将讨论盐商家族的运作、兴衰怎样受社会和法律的影响。尽管他们的“家事”属于私人范畴,但无论是父系家长制还是个人私有财产制,都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可是当两种制度有所抵触时,问题又如何处理?在缺乏系统商业成文法的情况下,商业纠纷又如何解决?当地方商务、民事、习惯与律例发生矛盾时,地方官又如何处理?在儒家“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下,盐商的遗孀享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她们又如何在这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中存活?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同居共财“大家族”制度的口诛笔伐,有没有历史和法律的依据?
第四章将通过对遂闲堂张氏、沽水草堂安氏和水西庄查氏这三家十八、十九世纪长芦巨富兴衰的描述,对天津的“盐商文化”进行剖析。时人、士流以至史学家,多对盐商们的附庸风雅不以为然,认为这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至于他们结交官府、钻营权贵的政治文化,更为清流所诟病。盐商们的豪奢、追逐声色自然被卫道士们视为离经叛道;纵使这些商人日日与诗酒为伍,以书画为邻,真正的文人雅士仍不屑与这些满身铜臭的市井之徒比肩。可是,作为天津城市文化重要的一环,这些盐商的所作所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其社会、政治功能,尚有待探讨。
第五章将分析盐商自十七世纪以来是如何参与种种地方公益事务的。无论侨寓、寄籍或入籍天津,长芦盐商通过通婚、世交、乡谊形成日益深广的地方关系网络,逐渐孕育、发展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归属感。津门既无所谓“土著”,盐商便依靠他们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地方官和盐运使的鼓励下,创设水会、粥厂,修桥、筑路,从事种种有益桑梓的事业。盐商的社会服务传统,当然也可被讥为沽名钓誉的公关行为,但这些“天津八大家”的成员和他们的亲朋戚友,如“粮店后街李善人”家、“元昌店”严家、“益德”王家等所组成的关系网,在清政权受到太平军冲击和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帮助天津渡过了这些难关。这些商绅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以正途功名出身的士绅。在“庚子”以后,他们大力发展天津的民办教育,建立学堂,引进新学以至女子教育、职业学校。
商绅的兴起,亦有赖于晚清推行的“新政”和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第六、七两章将分析这一发展过程。在“商战”思潮影响下,天津的商人,包括部分盐商中的积极分子,开始投资于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另一方面,清廷也希望通过变法自强,挽救其岌岌可危的政权。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清廷采纳了留日学生所倡议的地方自治方案,将其作为立宪的基础。盐商和其他商人,在这些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天津商会在王贤宾等人的领导下,更成为一个跨行会、跨行业,代表整个天津商界利益的组织。尽管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些地方组织不过是温顺的改良主义,甚至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超出官方认可的范围,不但对市政提出意见,更就牙帖、税捐等收入和支出与政府和地方官相颉颃。
王贤宾等人被抄家,也是这个国家与社会矛盾激化过程的一部分。第八章将详细分析他们所遭遇的这次盐务风潮。较诸1908年由王贤宾和商会协助解决、涉及1400万两银的洋货风潮,此次累商积欠洋债700万两银,并非绝无回转余地。正当盐商努力提出种种解决方案时,盐政大臣载泽的介入,把本来发生在私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复杂化。尽管所谓“新政”中有以保护商人为主旨的商人法和破产法,但清廷还是以取信洋人、保卫国家主权为借口,宣布累商破产。他们拥有或认办的长芦六十一县引地被收归国有,以抵偿大清银行代还洋款之资。三个月后,当武昌起义令清廷财政陷入危机,盐运使拿着谕帖向幸存的盐商筹借巨款时,一向“急公好义”的盐商也开始袖手旁观了。
关文斌教授研究明清时期天津盐商与社会的专著新版面世,不仅增加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从而保持学术前沿性,而且利用了新的档案资料,精益求精,臻于完善。作者以流畅的文笔为我们呈现出天津盐商家族以及社会网络文化的多元样态,而且剖析了盐商与天津近代化、地方政治的复杂关系,在人们较多了解扬州盐商与社会的知识之外,使我们看到华北重要城市天津的别样社会历史,成为新的学术典范。该书既是通过官商把握传统中国社会的佳作,又是城市社会史、华北区域史的重要读物。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视野宏阔,理论精深,既从城市发展角度对明清时期天津城市发展变迁加以探讨,又以巨量史料对天津空间形态、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家族与网络做了细致的分析,尤其展现了天津盐商这一特殊群体的全貌,进而深刻总结了天津城市发展的特点。此书在手,读者可对天津城市历史有更为全面、深入和立体的认识。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这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著作的再版,必将有力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史、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
——张利民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是一本深入探讨明清时期天津盐商及其对城市社会影响的专著。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梳理整合,深刻剖析了作为特殊群体的盐商,在一个城市的行政权力、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慈善事业乃至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作为,以及自身家族的网络建构与在近代社会变迁下的自救转型,揭示了盐商在天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天津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呈现出一幅长时段、宽领域、多方位的城市图景。
该书的再版对于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天津城市和盐业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
——任吉东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研究员
199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关于天津盐商的著作《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此次重修出版的《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按作者所言是“修订版”。细读之下,本书内容远非简单的“修订”,而是在发掘更多档案及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大有超越。作者提出,天津盐商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处于士、农、工之下的卑贱商人,而是逐步演变为绅商,成为地方精英和地方公益社会服务事业的领导者,影响力甚至超越科举出身的士绅和在籍官僚。天津商人在盐商的带领下成为市民的主导者。
——刘海岩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推荐一
“捐职充商纲总当,一时奢丽众称扬。吾津富贵无三辈,净洗双眸看后场。”
在以农业为主体、以商为末业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农业条件恶劣的天津以其独特而丰富的盐业资源,孕育出一批盐商家族,为天津带来众多移民,造就了天津的市民社会。盐商依靠经营专卖权获得巨额财富,却因其身份与豪奢生活而为士人乃至地方社会所不齿。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一方面向上发展,积极联络官府,组织自己的社会网络,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乃至获得皇帝的嘉奖;另一方面,则向下扎根,在地方上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并发展慈善、教育等事业,以期获得乡民的认可。这造就了盐商群体的独特性,也使他们与清政府和地方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进至晚清,教育改革、地方自治等活动兴起,盐商作为当地最主要的富人群体,更在其中积极活动,积极从事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和慈善事业,推动了天津的近代化,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数百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盐商家族怀抱满腔热忱,与天津城市一同向近代迈进,却在与外商的冲突中被清末的地方官员当作牺牲品。唇亡齿寒之下,幸存的盐商们从政局中抽身,而致力于维持桑梓。本书讲述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群体从兴起、鼎盛到衰落的数百年历史,并以其为主要线索,介绍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社会风貌。
◎编辑推荐二
天津盐商是一群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如何玩转政商潜规则?如何通过联姻、公益事业提升社会地位,建构自己的商业江湖?又是如何掌控盐业垄断塑造一座城市的命运的?
本书是一部讲述天津盐商群体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史著作。天津的盐商是在天津农业环境恶劣、盐业资源丰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特殊群体,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却难以得到士人的认可,社会地位难以与财富匹配。为提升社会地位,积累社会声望,盐商一方面努力经营社会网络,向朝廷捐输,与士人交游,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其他家族互通有无;另一方面服务桑梓,用心于地方公共和慈善事业,并在晚清积极响应“新政”,参与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业。本书讲述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群体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从积极参与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数百年历史,并以其为主要线索,介绍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社会风貌。
查氏家族可被看作明清时期天津盐商的一个代表。他们的势力与财富在曲折的发展中逐渐达于鼎盛,然后由于不善经营或官场打击而渐趋衰落。几百年间,几大盐商家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构成了天津社会的独特景象。
——编者按
查氏家族:盛极一时的水西庄
张氏和安氏败落之后,查氏继起,成为天津盐商社会文化网络的领袖。查氏在天津的两个主要支派可追溯至江西临川。1590年,以查聿和查秀为首的一支迁徙到今天的北京郊区宛平。这个家族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以“义不可辱身于贼”,一门“七烈女”自杀,被文人称颂。查秀的孙子查如鑑曾任扬州府江都典史,他去世时,其子查天行(1667—1747)才3岁。自此以后,这个家庭尽管陷入了贫困之地,却拥有相当多的社会关系。查天行由其任仪征知县的姐夫抚养成人,在他父亲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事业迅速发展。他定居天津,先供职于工部关。这是一个虽地位低但有油水的世袭职位,缺份可以随意买卖。
但是,在查天行看来,长芦似乎更有诱惑力。于是,他成为张霖的合作者之一,牵涉入案,亦被查参,只有125 081两银的资产,却向内务府称贷21万两。他被投入了监狱,并被判死罪。但是,查天行不像张霖,他与亲家金大中清偿了所欠的117 500两银。察察为明的康熙甚至批评办理此案的官僚,因为贷款时议定分八年本利清还,而查、张案发时并未满八年,户部本利一并全追,康熙认为这样做“于理不合”,命令户部解释。大学士马齐为户部辩护,“恩出皇上,部中何敢议免”。这复奏让康熙阐释他对法律的看法:“虽朕之恩,亦据理断之而已。若无理,岂可断乎?”查获得了赦免,1709年被释放。
可是,此次教训似乎并没有抑制查天行的野心。三年后,他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更为严重:为他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串通作弊。据赵申乔的奏折:“本生(查为仁)卷面大兴与册内开宛平不符,榜发十日本生尚未赴顺天府声明籍贯,有无情弊,难以悬定,据实题明,乞敕部查究。”《清实录·康熙朝》1711年10月31日。后来查明查天行雇举人邵坡冒名为他的长子查为仁(1694?—1749),参加1711年顺天府乡试。这一舞弊行为的暴露,原因倒不是枪手失败,而恰恰相反,是枪手考了第一名。在市井传言中,作为解元的查为仁目不识丁,因而舆论哗然。朝廷准备再次调查,父子二人仓皇逃往南方,躲在浙江绍兴一个亲戚家里。1713年,两人被捕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蒋良骐惊异地发现,查氏父子最终竟得到赦免,不像其他的盐商,也不像1711年江南和福建的相同科场案犯——他们都被立即处死。
关于查氏父子是如何化险为夷的,现存史料只有零星的载录。查为仁在刑部西曹的难友张照为查为仁的诗集《花影庵集》(花影庵是查给自己的监牢取的斋号)所作的序言里提供了一条线索。张照的同年进士赵熊诏告诉他,他的父亲赵申乔作为1711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自感对查氏的处境负有责任。步军统领陶和气(托合齐)也介入了此案,目的是报复赵申乔建议参革铜商金、王两姓。陶(托)氏四处散布言论,说这科榜首与取中者多是富人子,是因为他们有行贿勾当,借以打击赵申乔。赵跟托是否有其他过节、赵对查的赦免是否真的起了作用还不清楚,但是,银子能使他们化险为夷。据说,查天行的妻子用2万两银子赎罪,查氏父子分别于1718年和1720年被释放。
无论如何,查为仁成为一位传奇人物,被载入史册和乡土教材。文人雅士们视他为天才,为他能在恶劣的环境下,从目不识丁成长为诗人中的翘楚,为天津文学增光而感到自豪。这些传奇式的说法,自然真假混杂。假如查为仁1713年入狱时目不识丁的话,那么他在创作《花影庵集》(集中最早的诗作于1714年)之前,仅有一年的时间学习诗作的格律与技巧。这是一件有可能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当然,这亦不排除枪手代笔的可能。
不论是否目不识丁,查天行父子继承张氏和安氏余绪,成为天津盐商文化网络的领袖。他们在城西三里购买了一百多亩地,建成“水西庄”,这里便成了查氏网络的大本营。水西庄位于运河南岸,庄里绿树成荫,假山奇石遍布,歌台舞榭等大小建筑掩映其间,房中罗列书籍、画卷、古玩。陈元龙与查昇是总角之交,二人曾同在南书房共事,陈还在各部及内阁担任过要职,如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致仕后旅次水西庄作《坐揽翠轩与天行述旧》一文,回忆两人总角之时,又作《水西庄记》,称“斯园乃尘世之丹邱”。陈的侄子、当时任户部侍郎的陈世倌称查天行为叔叔,在查氏七十寿辰的时候,敬献祝寿词一篇。另一位高官、湖南人陈鹏年,经查慎行和查浦的引介,亦作客水西庄,为查为仁的诗集题写序言。
地方官也是查氏网络的成员。首任天津直隶州(设于1725年)知州宋晶,1725年到任的长芦盐运使张璨,都常到水西庄酬唱。1726年任长芦盐运使的陈时夏撰文赞颂查天行的继室,言及他与查之间近二十年的友谊。英廉在担任天津河防同知时,曾频繁与查氏交往,与这里的诗人唱和。水利专家陈仪(第一章已述及)不无骄傲地宣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查天行了。陈宏谋任职天津河道期间,亦与查氏论交,为查日乾侧室王氏撰写八十寿序。查为义(为仁弟)故后,陈宏谋应查礼(为仁三弟)的请求,作《集堂府君小传》为纪念,“以俟后世之采风者”。
来到水西庄的更多是文人骚客。查氏海宁支系(南查)的查慎行(曾任职南书房,前已述及)视查为仁如同亲子,教他作诗。慎行的弟弟查浦在1700年成进士之后的两年时间中旅食水西庄,与查天行以兄弟相称,视水西庄为“隐逸之所”。厉鹗、杭世骏、万光泰、汪沆和符曾等来到水西庄时无不感到宾至如归。由查为仁命名的水西庄诗集《沽上题襟集》刻印后,一纸风行。查为仁笺注《绝妙好词》,厉鹗将查的笺注与他的笺注相比较,认为查氏堪称第一。这样,查作为诗人和学者日益声名远扬。
然而,当乾隆皇帝驾幸水西庄时,所有这些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都黯然失色。乾隆皇帝于1748年首次到水西庄,他认为这是一个惬意之所。随后他几次来到天津,也都下榻水西庄。只是这一特殊的荣耀,也使查氏付出一定的代价。既然皇帝如此厚爱此园,查氏便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将庄园的一部分修缮一新,专门奉献给皇帝。1771年,乾隆皇帝将此园御笔命名为“芥园”,从此这里成为皇帝亲临的圣地,其他人无论拥有多大权势、多少财富,也不能僭越了。
然而,这样的代价并不算大,查氏因此实现了他们追求的梦想——获得社会的尊重。尽管地方志编纂者对查氏是“流寓”抑或“乡贤”持有争议,但查氏宣称他们自参加科举考试起就入籍天津。他们的姓名甚至进入了本地方言,“阔查”成为富有的同义词。查为仁的二弟查为义曾任安徽太平府通判,致仕返回天津后成为一名盐商、诗人和业余画家。查为仁三弟查礼,1748年在户部任职,外放后领兵参与大小金川之役,最终于1782年任湖南巡抚(未到任)。查礼之子查淳,官至湖北布政使。确实,自查天行之后的查氏五代人,代代至少有一人中举人或成为进士。他们与海宁陈氏(本姓高)源远流长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查为仁次子查善和是陈邦彦的女婿。陈邦彦进士出身,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曾入值南书房,官至礼部侍郎。但是北查到了善和这一代,家道已经开始衰落。科场无论得意还是失意,候补或捐官,都耗资巨万。加上族人“花时载酒,累月流连”,不事生产,所托非人,连年涉讼,“遗赀几荡然矣”。
查昇的后代作为查氏的另一族支(南查),也曾在长芦兴盛一时。查昇供职南书房时虽然经济不无拮据,但因为有天津的北查支持而生活稍得舒缓。他的儿子查昌洵蒙父荫当上了广东长宁县知县,孙子查懋也依附北查从事盐业。懋子查莹是1766年进士,其弟查世倓(1750—1821)四年后成举人;他的孙子查堂也中了举人。与曾祖父相比,查莹作为监察御史,仕途平平,也没有在文学上取得卓著的成就。但是,他继承了家族巨大的财富。他的女儿查有蕙嫁给伯爵孙均,据陈文述的《孙古云传》,孙在故乡和北京俱无恒产,但因为“厚于故旧不能节缩……恒惧不继”,幸亏“外舅给谏查君映山(查莹),世业长芦鹾务,饶于财。病卒无子,以犹子有圻为子。君配查夫人,给谏爱女也。外姑祝恭人以给谏遗言,分质库四,得二十五万金。查夫人贤明知大体,尽以所分属君”。孙在爵位被革后退隐,“不意司事者耗费十七八,岁入不给”,富贵有如过眼云烟,身后萧条。
查氏的这一族支到了查有圻的时候,无论财富还是名声都达到了巅峰,以“江公源”的引名,成为芦纲公所的纲总之一,引地遍布河北和山东。“计产三千万……中外大寮困乏,无不资之,如陶文毅(澍)、百文敏(龄)每贷银率以万计。”跟张霖一样,他最终的目标还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可是当1807年朝廷考虑任命他为户部郎中时,他应否回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那时在京城的官员中还没有回避制度,但是当时主管户部的戴衢亨(1755—1811)是查有圻的姻亲,吏部感到应该实施京官回避制度,对不同的品级和关系予以规定。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两个家族是儿女亲家,关系非同一般,极有可能在共事中串通一气,于是同意以后出现类似情况时应当采用回避制度。查于是转到刑部待缺。次年,查就以“仰沐主恩……身家赡给之资悉荷高厚生成之德”,又恭逢御驾贲临天津,敬进银10万两,以备赏需。
然而,对都察院给事中花杰来说,这种关系不仅会导致失职。1809年,花氏提出了一连串对查氏、戴氏、户部和长芦盐运使的弹劾。他声称,其时正值南运河工程展开,国用浩繁,唯是长芦连年缓征,积欠至700多万两,而查有圻“任性挥霍,骄奢淫佚,京城人谓之为查三僄子”,与他的同族查庆余、查世兴等虽然坐拥厚资,却置国用课币于不顾,承办官引地后既不交窝价,亦不付官租,建议严催积欠“以惩奸商”。他更指控查氏凭借姻亲的庇护,图谋扣压应上缴户部的窝价。另外,在母亲的丧礼上,查有圻让三位大学士当知宾,这虽然算不上罪行,但也是滥用名器,有损朝廷尊严。对戴衢亨及其同党的指控更为严重,花杰称他们阴谋操纵会试,广植门生,在户部滥用权力,又企图把他的门生和党羽塞进南书房。朝廷的调查似乎没有得到多少证据,花杰亦因弹劾失实而被降职。但是,戴衢亨也遇到了麻烦,他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被揭露了。由于戴的叔父戴均元时任仓场侍郎,所以,潜在的利益冲突使戴衢亨降职调至工部。
尽管查有圻在这事件中相对而言未受太大冲击,但是他作为与官僚政治密切相关的盐商,树大招风,成为一个极其方便的攻击目标。据传御史李仲昭曾向查索取贿赂,查拒不顺从,李对此怀恨在心。后来,李重新挑起事端,参奏长芦盐商串谋倒换户部颁发的称盐的砝码。后来的调查虽然找不到查氏直接勾结户部官员和工匠的证据,而且查本人事发时远在苏州,但是查仍然被认定是主犯,因为他作为长芦纲总,是通纲“造谋之首”,玩忽职守,对业务不闻不问,纵容内司冯昶(前文提到的“亦政堂”冯家)、外司樊宗澄牟取暴利75 620余两银,被判追加五倍罚款,共计455 652两,严加追比,查封北京、天津、苏州等地的家产以备罪罚。长芦众商总共应罚银1 478 134两(后修正为1 479 486两),所有职衔顶戴全部革斥。查虽然在限期内提前两个月把罚款交清,但仍得发遣。其母查祝氏(查莹遗孀)以次房独子有圻过继兼祧,“母子相依”,若有圻被戍远行,恐无相见之期,因此愿比照四品官赎军流罪银3000两之例,以十倍即3万两为儿子赎罪。嘉庆以查氏在限前清缴罪赔,加恩宥过,才避免了查有圻的流放之苦。现存史料尚不能证实曹振镛(亦是查的儿女亲家,继戴衢亨为户部尚书,任期至1813年9月)在处理此案中的作用,但1813年,有圻(已革四品卿衔)随同长芦通纲恭进13万两银以备赏需,觉得还未尽“捆忱”,次年又连同查世俨各捐银3万两抗洪救灾,开复了六品官衔。但是经过这一番挫折,南查这一支已经元气大伤,有圻终于1824年告退,次年更因为尚拖欠正杂币利官租27万多两,所呈房产家什作抵不敷而被参革,余项严追。
查昇后代的另一支传至查世倓,绝意科场,协助父亲查懋(引名“江公源”)经营长芦盐业,主持有圻兼祧两房,经理其家后退隐嘉兴。其子元偁(1772—1855,1808年进士)分家,南方产业传与长子绍篯(号玉彭,1804—1854,1846年举人),长芦盐业交予次子彦钧(1806—1861,兵部候补郎中,引名“查庆余”),行办长芦引地十九处(不计京引)。可是彦钧重蹈有圻覆辙,不事生产,“托名在京当差,一切假手商伙冯相桂,任其贻误课运……恃系职官,置若罔闻”而被参革。绍篯虽然已经与彦钧分家,但仍然驰赴天津,倾其所有协助而不济,北京、天津、海宁、苏州等地的产业,尽行查封备抵。其后人虽然继续以“查庆余”引名从事盐业直至民国时期,但仅限于大兴、宛平京引。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