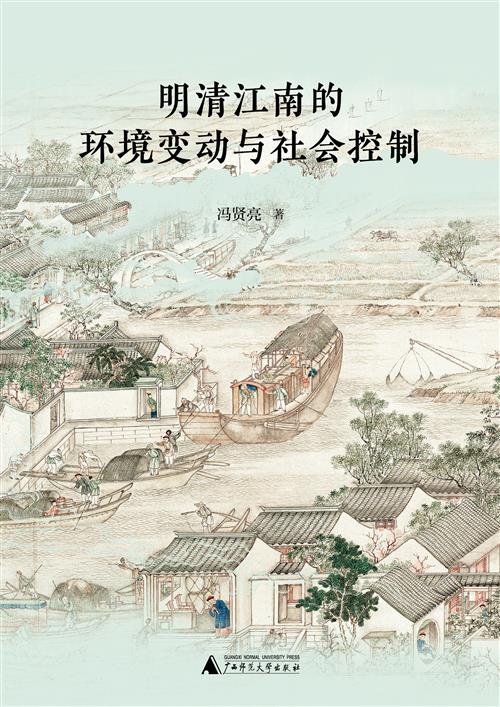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4-01
定 价:128.00
作 者:冯贤亮 著
责 编:梁嗣辰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历史爱好者
上架建议: 历史/中国史
开本: 32
字数: 520 (千字)
页数: 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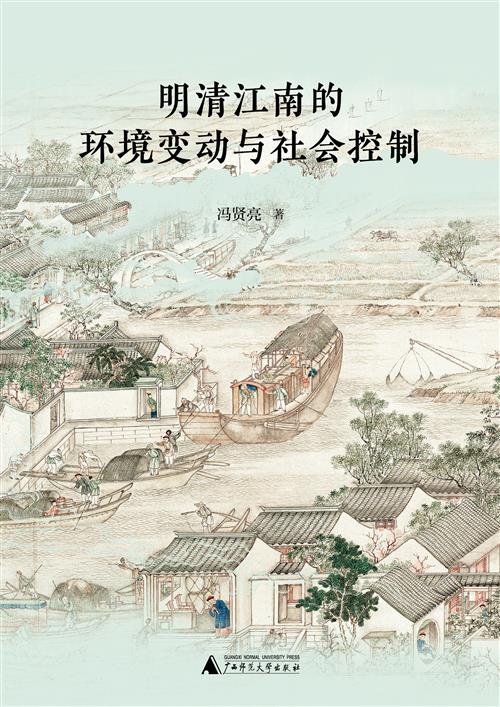
本书深入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长期稳定与繁荣的内在机制。作者结合江南河湖密布、灾害频发的自然环境与官僚、士绅、地主、商人等阶层互相纠缠的复杂社会结构,分析中央政府、地方官府和民间力量如何通过政区设置、社会纷争、灾害应对、城市防护、行业保障、文化控制、民间信仰、乡约规范等手段,应付常态和变态下的环境问题,实施区域社会的较好控制。本书揭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三方力量的协调机制,且地方士绅作用突出的特质,解答了江南赋役沉重但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提出了江南地区存在的成熟的社会控制与基层治理的模式,开启了江南史研究新范式。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江南地区史、中国社会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出版有《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等著作。
绪论 江南的概念、环境与社会控制研究的界定
第一章 江南的生态环境及其内发展
第二章 江南行政区划的变迁
第三章 明清时期江南的基层系统
第四章 明代江南的疆界错壤问题及其影响
——以嘉兴府嘉兴、秀水、嘉善三县的争田事件为中心
第五章 明末江南的大灾荒与社会应变
——以湖州、嘉兴二府为例
第六章 明清江南的水利防护与社会调控
——以湖州府的溇港管理为中心
第七章 晚明江南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
——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
第八章 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与社会
——以嘉善县等地的盗匪之乱为中心
第九章 明清时期江南的行业生活与互济行为
第十章 明清江南地区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府控制
——围绕佛教寺庙与民间相关习俗信仰
第十一章 结论:区域社会的环境变动及其控制模式
附录一 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
附录二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附录三 “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修订版后记
序
本书所论的江南地区,自唐代后期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地区,其地位不亚于汉唐盛世的关中。就政治形势而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就经济而言,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的财赋重地。明人李乐《见闻杂记》:“天下财赋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丘濬《大学衍义补》:“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又云:“扬州富庶,常甲天下,自唐朝及五季,称为‘扬一益二’,今鱼盐谷粟布帛丝絮之饶,商贾百工技艺之众,及陂塘堤堰耕屯种植之宜,于古未有改也。”就文化而言,南宋以后,“衣冠人物,萃于东南”。据何炳棣研究,明清两代五个半世纪中,浙江、江苏两省所产之进士,居全国首二,清一代一甲进士共336人,江苏一省占113人,苏州一府占42人,令人惊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诸方面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已为不争之事实。
众所周知,影响一个地区的兴盛和衰落,不外乎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指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人为因素主要指战争、社会动乱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引起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破坏。江南地区虽然自然条件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优越,在社会动荡方面也是较中原地区相对要轻,但其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一千多年来同样经历了战争、灾害和改朝换代以及大大小小的社会动乱,人地矛盾、阶级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例如,这里也曾发生过重大的灾害(太湖流域水灾、海灾)和严重的社会动荡(如明清鼎革、民众反抗、倭乱、太平天国战争)。但事过之后,总能有自身恢复的能力,最终在经济文化方面保持平衡的发展,并在全国占据领先的地位。时至今日,仍然是全国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的这种繁荣大致上维持有一千年了。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究竟什么机制,能使江南地区有此持续发展的潜力?
由于江南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近代以来对明清江南地区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学科中的热门。综观近几十年来对于江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其量之丰,其质之高,非其他地区所能企及。大量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方面,如江南农业、水利、手工业、商品经济、市镇、近代化、城市化,以及江南社会的影响力量——士绅阶层的研究,等等,为我们呈现了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各层次的方方面面。但是江南地区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持续发展繁荣?明清以来不少明智之士指出,江南地区赋税最重,为什么这未使其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这是以往学者未能揭示的问题,也正是本书所要解决的课题。
本书是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比较新的角度对江南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内在因素所进行的全面考察,主要从行政管理、地方防护、水利调控、灾害应变机制、宗教和民间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三大层面,对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即所谓社会控制,使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秩序和发展势态。
明清江南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首先是自然条件复杂,山地丘陵镶嵌,河湖水网交错,溇港塘浦密布,海陆沙洲相汇;其次产业丰富多样,粮、棉、丝、渔、茶、瓷、纸、竹、木等百业林立,支撑着江南的经济;最后是阶级阶层复杂,官吏、地主、雇农、贫农自不必说,此外,商人地主、士绅、行商坐贾、手工业者、农业兼手工业者、各种出卖劳力的雇工、游民等等,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所有的阶级和阶层,可以说在江南地区应有尽有。他们都有自身阶层的利益需要维护。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内,维持长期平稳的发展,必然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配合。
本书首先从政区的设置角度,探索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控制的思路。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地方分层管理制度,也就是政区的调整。例如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府州县设置繁多,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反映了江南地区赋税繁重、人口众多、地方事务烦冗,中央政府必须强化对江南地区控制,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稳定地方局势的积极措施。作者又通过对江南地区县级以下乡—都—区—图—圩的地方管理系统的实施和复杂变化的细致研究,表明了在江南地区人多地狭的特定地域,土地的重要性远过于人口,因此有效地保证江南地区田亩和赋税的稳定成为政府控制的重要举措。但是这种中央政府对地方统治的强化,必然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例如嘉兴分出秀水、嘉善二县,出现了县以下乡、都、图、圩嵌错的局面,引起地方上赋税不均的混乱,出现了政府会勘与民间争田问题,暴露了当时地方士绅与中央政府的尖锐矛盾,最后政府采用法制手段控制了社会的动乱。当然这种控制只是暂时的,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难以根本解决。
江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并不少于其他地区,但是江南地区的灾前防灾和灾后补救工作比较成功,地方政府和民间尤其是代表地方精英的士绅阶层的力量和宗族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地方密切配合。这当然是因为江南地区对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反映江南地方绅士阶层希望地方安宁以免过分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明清时期太湖水利也由宋代以来单治下游三江转化为上下游区域的综合治理,主要表现在太湖水系中溇港的疏浚和管理过程中,地方士绅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对江南地区社会影响最大的动乱,一是倭寇,以明嘉靖年间为最甚。倭寇对东南地区城市居民的骚扰,促使江南地区各级城市大规模修建起城墙,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城市防护体系,对保证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城市防护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表现了中央、地方和民间三方面力量的联合,而其中民间的社会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盗匪问题,当然盗匪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发生,但在江南地区有其特定的意义。江南地区土地兼并严重,财富集中,贫富悬殊,农业以外的各种产业众多而又不稳定,自然灾害的频发,都是盗匪产生的根源,再则江南水乡河湖港汊密布的地理条件,为盗匪出没活动提供了便利。盗匪的骚扰对富民阶层无疑是很大的威胁,由此影响到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赋税的征收。于是有保甲、乡兵、巡检、水栅等措施以防盗匪。其中中央、地方和民间势力三者如何各自发挥作用,以求暂时稳定,这在封建社会说来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已众所周知。在江南社会中兼营部分行业并占有地产的城乡地主是社会力量的中坚。由这批力量组织建立起来的各种行业在稳定江南社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政府施行许多保护行业的法规以维护其正当利益,如果行业有不正当行为,政府也会出面加以禁止。同时行业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然行业与政府间在某些方面会有矛盾,但总的来说是相互依存。地方政府对行业的保障体现了地方行业在发展地方经济、稳定社会方面起的重要作用。本书研究证明,保护行业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维护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为此,禁止任何侵扰行业生产的行为是政府全力支持的。
对江南地区长期盛行的民间信仰,政府也是尽量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规范之中。民间信仰是广大人民在不能主动掌握自己命运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这种信仰的无序发展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明清政府对地方淫祠的控制和对正统信仰秩序的营造,无疑对江南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种种的研究,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长期稳定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转的,表明了稳定社会诸要素中,中央、地方和民间的力量三者联手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民间社会力量(包括士绅、家族、民间自治力量等)在其中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长期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正是因为这些力量在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不稳定情况时,在妥善处理各阶层利益前提下,相互协调、平衡,不使矛盾激化,保证了社会继续正常运行。正如本书最后结论中所说:“可以将一个区域从变动到稳定的期间定为一个周期,除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动外,水利失控、灾害发生、战争波及、民众抗争等方面问题的产生,可以为政府组织(或是以士绅为主导)的再次重新调整和聚合社会各阶层力量提供机会。所以新的协调之后,会出现又一个平静繁荣期,这时的控制也最有效,整个社会经济仍能得以持续发展。”近年来历史学界对历史时期区域社会的综合研究十分感兴趣,我想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研究。
唐宋以来,江南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今天,我们环顾96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何处有似江南?当然,社会制度不同了,经济体制不同了,明清时期社会的各种弊端没有了,但是保护好江南地区,进一步发挥其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当同此理。研究历史,多少有些借鉴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冯贤亮的博士论文。他近几年来一直在进行对江南地区社会变动的研究,其用力极深,成果也是很显著的。希望同行们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有认真的批评,我想这是作者最希望的。是为序。
邹逸麟
2001年11月14日于复旦12宿舍
自然环境不是地域发展的决定因素,但为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社会治理是家国政治的重要内容,江南社会的变动、控制、治理在明清时期显得尤为突出。该书较早专门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在学术史上具有创新意义,全书考察和论述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的相关内容,在问题意识领域具有填充空白式价值。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
该书是冯贤亮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明清时期的江南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著称,其发展奥秘耐人寻味。江南区域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成果最为丰厚。作者则站在历史地理专业的本位重视人地关系,强调环境变动,而且引入社会控制的研究,增加了国家与区域社会关系的探讨,分析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三者对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作者的论述涉及行政管理、地方防护、水利调控、利益分配、灾害应变机制、思想文化控制等方面,全面考察江南地区社会长期稳定的内在因素,以揭示使社会处于长期稳定的秩序和发展势态。作者的这一综合研究,使得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大为改观,而且对于目前势头正猛的“治理”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建华
历史时期的“江南”概念趋于不断变化之中,且富有伸缩性,但“江南好”一说,几乎已经成为人们固化的历史认知与文学想象。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既沉潜于史海,又有广博的视野,是一位新锐的明清史研究专家。他的这部论著,以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为视角,从生态环境、行政区划、基层系统、疆界错壤、灾荒、水利防护、城市重建、行业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描摹了一幅丰富而充满活力的多样化江南历史图景。此著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探究明清江南的社会控制,是日本学者“地域社会论”的继承与创新,从纷繁的江南史论著中脱颖而出,别开一个生面,堪称新江南史的一个范例。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宝良
明清时期的江南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那时江南就有行业集聚、工人抗争和地方保护主义了吗?为何江南地区在倭乱开始后能迅速建好城墙?
本书尝试以历史地理学为视角,结合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诸因素,解答上述问题。比如:
在环境保护方面,本书着力探讨明清时期围绕水利建设而产生的三种矛盾,即上游治理、下游治理与上下游综合治理间的矛盾,水利设施修建与航运通畅间的矛盾,退耕还湖(湿)与农业生产间的矛盾。此类矛盾至今仍然部分存在,对现实社会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行业生活方面,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地之一,明清江南的行业集聚已经十分明显,行业公所广泛设立,行业互济十分普遍。随之而来的,便是劳资矛盾与地方保护主义。明清时期的江南已不时出现罢工行为(叫歇),在处理劳资矛盾中,政府的居中调停起了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还是偏向资方;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十分明显,地方政府对本地工商业十分保护,在辖地内,严厉打击外地商号与之竞争。
在应对倭寇入侵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城墙等城市防护体系的迅速建立,在当时江南绝大多数城市没有城墙的情况下,城墙的修建对保障江南的城市安全及经济发展起了支柱作用。城墙迅速建成的过程,体现了中央、地方、民间三方面的联合与博弈,而其中民间,特别是士绅阶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长期的繁荣离不开机制的保障。本书重点探讨“什么机制”使江南地区能够在一千多年中保持持续发展与稳定,特别分析中央、地方、民间三方力量的协调与平衡,对立与统一,斗争与合作,以及士绅阶层、行业组织等民间力量在社会控制中的独特作用。为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区域稳定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领头羊与文化中心,本书通过全面而深刻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明清江南并非简单的“经济奇迹”,而是在生态约束下通过制度创新与社会资本积累实现的动态平衡。对理解中国传统社会韧性、生态文明的本土经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行业生活方面,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地之一,明清江南的行业集聚已经十分明显,行业公所广泛设立,行业互济十分普遍。随之而来的,便是劳资矛盾与地方保护主义。明清时期的江南已不时出现罢工行为(叫歇),在处理劳资矛盾中,政府的居中调停起了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还是偏向资方;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十分明显,地方政府对本地工商业十分保护,在辖地内,严厉打击外地商号与之竞争。
——编者按
明清江南的行业集聚、工人抗争与地方保护
1.行业的排他性与自保性
从性质上讲,行业具有较大的排他性和自保性,这是行业生活的必然产物。
在同治九年春天,苏州府长洲县以织宋锦机为业的沈友山、王承忠、孙洪、戴梅亭、吕锦山、朱沛和等人,为遭同业的曹阿传和顾廷等另创行头、“借神勒捐”的问题,要求地方政府予以“究治”。到光绪四年(1878),曹阿传已身故,但有王沛等人“结党成群”,“喊歇停工”,又要“倡捐勒索”,致使同业“受累”,引起行业人员的不满。以沈友山等为代表的机业人员,最终获得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以后如在苏州府的长洲、吴县、元和等地办事,有像王沛等一样,再另设“行头行规”,改立名目,“妄行派费,诈扰同业”,允许机业人员“指实禀县”,官方予以严办。
创于嘉庆年间的苏州元和县光裕公所,是由专业弹词评话的人员集合成立的。但是在民国年间,有社外说书人俞鹍扬等联合社外的露天说书艺人,在恒昌湖田的复兴园等茶室,高搭台面进行弹词评话的演艺活动。这必然影响了在当地说书业处垄断地位的光裕公社的利益。民国十二年(1923),全社联请苏州警察厅给予严禁,规定“凡社外之说书人等,不准于茶室搭台说书,以昭社内外之区别”。
又如,在苏州府元和县的徽、苏两帮烟业,也存在利益之争。后经元和县讯断,两帮在当地进行的公益事业“各归各帮办理,不准紊越派扰”。
前文述及的油麻业在同治年间的公议,所谓“相隔七十余家,方可开设油坊,以免争夺肇衅”,都有着行业生活中的明显排斥性。
在苏州府的吴县,以红木作专营大小梳妆粉镜、文柜等生意的孙明友、潘洪富、匡章正等,建有公所,遵循行规,与同业议定捐资办理善举等事,并于光绪十九年(1893)经苏州府及吴县、元和、长洲三县备案,同业恪遵,并无异议。不料,一向以做红木玻璃灯架、挂镜、插镜机架为业的徐阿四、陈安玉、强老虎等,与孙明友等人的行业毫无关系,而且“既不同行,又不出捐”,居然也“搀做洋镜小亭等物,在店售卖”,侵犯了经营梳妆粉镜、文柜生意的孙明友等人的利益。孙明友等上告当地官府说:“窃思红木业,各做买卖,身等亦不能越做灯架,岂容徐等乱章做卖?”并认为不能越业经营是“昔时议定之规,并非觊觎生妒”。而在光绪十九年官方所给的印示中,载有议规十三条。当地政府即裁定,凡红木作各同业人员,务必遵照规章十三条:“倘有外来同业,阻挠乱规,有碍善举情事,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此外,当地的水灶业因历年较远,久未整理,以致在民国六年(1917)间“城外有人违章添开”,而城内的公所要划分地域界限,店多人众。该业的赵行豪、黄荣炳、宣彩文、徐文淦等人就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同业悉照旧规,只准顶替,不能添开”的要求,得到了政府的允准。可见,即使是同一业行中的不同分派或分工,如有越行行为,也会引起同行的不满和指责,甚至诉诸司法。行业生活的自保与排他的特性十分显著。
同样地,在外地开办公所,也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从而排斥其他行业对本行业生活的侵扰。同治十一年(1872),由苏州商帮的沈时丰等人发起,在上海老北门内措资筹建了珠玉业公所。然而,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南京帮商人的“缠讼”。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间,当地政府判定苏、京两帮商人“各立市场”,并且“给示晓谕”,声明苏帮将公所暂借与京帮进行贸易,“限期五年”,要求京帮商人“从速措办地方,为乔迁之地”;如果逾期,苏帮可以“禀道勒迁”。苏帮又凑了二万六千二百洋元,在原公所对面购得旧屋,连地一亩五分,“建设市场,专为苏州各帮珠玉业贸易之所”。上海县府在宣统元年(1909)进一步作了批示,下令该处市场“系苏州珠玉各帮筹款建设,专为该帮贸易之所,不许京帮入内摆摊”。
2.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调整
当然,行业内部的生活也需要时常协调。为了规范行业生活,维护本行业及其成员的利益,行业大多定有细密的行规条约。如苏州府吴县的纱缎业,曾在雍正元年(1723)制订了一些行规条约,并通过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作为行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互济是维持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无论是对外的援助或进行某项善举,还是在本行业内推行各项福惠措施,都是出于维护本行业发展的需要。而对本行业内部规约的重整,虽多有社会变乱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本行业发展壮大的考虑。吴县地方豆米杂粮业公所在清代已有设置,到民国初期,因年代久远,行规已经处于废弛状态。所以,在民国八年(1919)间就重整了本行业的内部规条,并刻碑勒石要求共同遵行。规约内容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允准。
在米业方面,江南的许多市镇以经营米业闻名,如枫桥市、长安镇、平望镇、新市镇、同里镇、皂林镇等。对于这些市镇米业的保护,也是官方所重视的。以吴江县的大镇盛泽而言,其米业专门建有公所。江南是万商麇集之地,各地负贩及外省商舶往来,本来是以枫桥、无锡两地米业为最盛,平望、同里等镇则次之;至于盛泽,专重丝绸业,从事米业的不过十分之二三。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盛泽米市之盛况已经不亚于平望诸镇。但在咸丰庚申间遭受兵燹后,“疮痍未复,市镇寥寥,间有挟赀招集商舶,逐蝇头利,亦复远不逮前”。同治七年(1868)夏天,地方上有人开始聚集同业人员为长久发展之计,捐资进行重建工作,到光绪三年(1877),终于建成了盛泽镇的米业公所,包括了36家米业同行。这是行业内部的重整调适工作,属于行业本身的保障行为。
道光年间,原籍溧水等县的王有源、俞士胜、陈秉孝、钱廷荣、邵全寿、刘纪煜等人,一起在苏州府长洲县开办水灶业。后因异乡人在苏州府的帮伙较多,而染病身故及患病无力请医调治的也不少。于是,经过同业吴培基等公议,捐资设立了公所,备棺殓之费,设公共义冢,以解决上述诸问题。但有内部店伙等人勾结外匪,借端索诈,酗酒滋事,公所同仁被迫向官方申请禁革,以保护同业的公共利益。元和县地方的水炉公所,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都得到了官方的一体照护,以更好地维续同业人员的经营活动,维护内部秩序。
布业方面,苏州府的布商戴志诗、李邦达等人,因同业遭受兵燹后,“孤苦无告者居多,甚至半为饿殍”,在同治五年(1866)秋就集合同业公议,“各伙友愿于辛(薪)俸内,每千捐钱十文,店主人亦复照数捐助,抵充办善经费”;这样积集一年,经费仍是不足,只好再行劝募,“各庄各坊交易内,每千捐钱两文”,汇存于公所,“按期分给月米钱文,兼助丧葬等费”;并在吴县城中街区购屋,置立了尚始公所。所有这些,都在同治八年(1869)取得了官方的认可,立碑予以示禁保护。同治七年,在吴县木渎镇经理布店的陈熙鼎等商人,因同业伙友大多无力经营,或年老失业,贫病难持,一遇病故,棺殓没有着落,或病故后孤寡无所依靠,衣食难周,就在该年经同业各友公议规条,创设了布业公所,“办理赒恤无力同业生养死殓各善举,公捐经费办善”。这样一直持续至光绪年间。
苏州府的面业公所在光绪四年(1878)因隔壁经营茶叶的盗卖了公所内一条弄堂而集会商议,向县里通禀存案,官方即“给示以碑”,予以保护。后因公所坍塌,要重修大殿,面业同行即公议由陆阿东负责向行友劝助,每位助以丕洋八角的包括陆阿东在内有46人(其中有一位捐助的是一元),捐助五角或三角的共计214人。公议还决定,“众友现做每日捐钱一文”。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苏州府等地疫病流行,面业同行中传染得病身故的很多,公所即邀同业集议,将应办的一切同业善举认真处理,并将房屋倾圮的地方重加修葺,“所需经费仍由业等按月抽助,并不外募”;公所事务由商人代表轮流经理,为防止日常工作受到地匪游勇等人的滋扰,向官方提出保护的申请,得到苏州府衙的支持,并勒碑示谕地方。
3.行业之间的互济合作
实际上,并非只有一个行业可以完全独断本行业的经济生活。许多行业都采取了合作的姿态,以期获得更大利益,或者是稳定发展。
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垄断之态,在意愿上实际想体现一种正统地位。在江南地区,许多行业排斥其他行业的介入,就存有这样的因素。如苏州府地区的金箔、银楼业,为免其他行业的觊觎之心,曾在道光年间要求官方予以保护,排斥任何有损本行业利益的“加价”等行为。当时有人倡议停收教徒三年,其煽惑散匠、羁众停工的意图,就被官府出面干预压制了下去。
然而,两个行业之间,即便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仍会存在互助的情况。如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苏州府吴江县府出面为胡寿康等人“设局捐济绸缎同业”的善举专门立碑,以示支持与保护。当地政府要求各地保和绸缎同业以及绡绸各庄人等永远恪守:“所有职监胡寿康等经置房屋作为公局,捐厘助济绸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等善事。”并指出,如有地匪人等借端滋扰,以及年轻尚有可为、不应周恤而妄思资助、向局混索的,允许“指名禀候拿究”;地保如有徇纵,“察出并惩”。同年四月,邻近的湖州府乌程县,也奉苏州府移文,对胡寿康等的善举予以保护,要求乌程地方的绸庄按数扣交公局,每年刊入“征信录”造报上级,并立碑晓谕:“凡遇苏庄运贩绸匹,务按销货数目扣存汇交公局,以襄善事。”
——选自冯贤亮《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