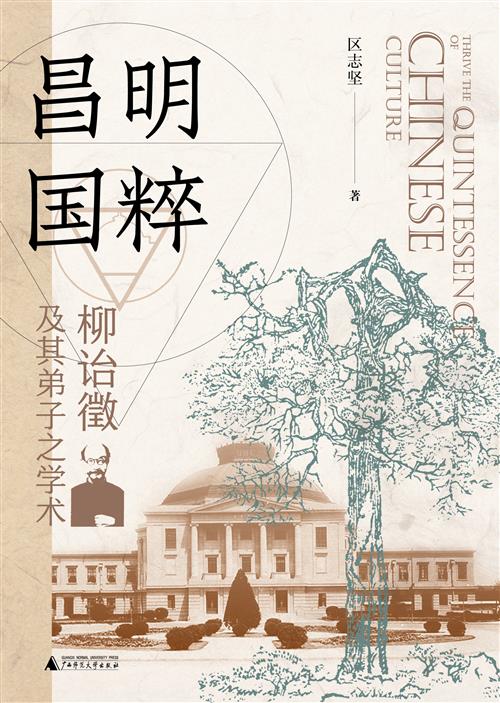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5-01
定 价:89.00
作 者:区志坚 著
责 编:原野菁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历史爱好者
上架建议: 近代思想史;近代史
开本: 32
字数: 316 (千字)
页数: 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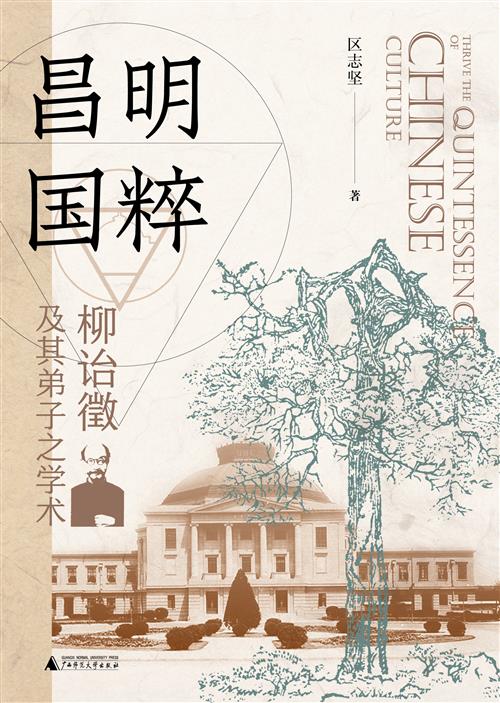
书稿为一部史学史研究著作,以1915年至1931年为研究断限,采用人物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并以史学与学术机构发展互动关系作出分析。第一章为引言;第二章论述柳诒徵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学风尚形成的时代背景;第三章阐述南高史学发展概况;第四章析论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以及史学思想特色;第五章介绍柳氏弟子张其昀、陈训慈、郑鹤声、缪凤林的史学研究,以见师生之间在学问方面的传承关系;第六章为结论。柳诒徵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的作用,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爱护的态度。
区志坚,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中国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香港地区历史教研工作。香港中学《通识教育》《中国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导言 1
第一章 柳诒徵与南高治史风尚的形成 25
第一节 柳诒徵的生平及其学术27
第二节 清末民初师范教育的发展 54
第三节 江浙学风和江南藏书业的发展 63
第四节 反传统思想及中西文化调和论的出现 75
第五节 南高留美教员与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 89
第二章 南高史学系的成立与发展(1915—1925) 107
第一节 南高史学部的成立 108
第二节 南高史学部的课程 113
第三节 南高史学系学生概况 124
第四节 史地研究会及《史地学报》 128
第五节 学衡社与《学衡》杂志 135
第三章 南高史学者的分合关系(1926—1931) 141
第一节 《史学与地学》的出版 142
第二节 中大史学系成立及《史学杂志》的创办 148
第三节 《史学杂志》的内容 164
第四节 南高史学系出版物的流通及其特色166
第四章 柳诒徵的史学观点及其治史方法 177第一节 以礼为中心的史观 178
第二节 通史及“通则”“独造”的文化史观 193
第三节 信古的史观及反疑古史学 203
第四节 地方史及史地学的提倡 212
第五节 致用的考证方法 219
第五章 南高史学的继承与发扬
——缪凤林、郑鹤声、陈训慈、张其昀等人的史学研究 233
第一节 缪凤林的中国通史及中国礼俗史研究 237
第二节 郑鹤声的中国史学史及历史教育研究 257
第三节 陈训慈的地方学术史及中西史学研究 270
第四节 张其昀的人文地理学和地理教育学 282
第五节 其他从事史地学研究的南高学生 293
结论 310
附录一 1915—1923 年南高国文史地部教员表 321
附录二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地学报》发表论文数目表 323
附录三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学与地学》发表论文数目表 326
附录四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学杂志》发表论文数目表 327
附录五 国立中央大学的源流与变迁简表 328附录六 南高史学工作者大事年表 330
附录七 南高文史地部教员及学生照片(1923年) 332
参考书目 337
“新文化”浪潮下“北大南高”的史学对峙
近代中国史学的发端,应以20世纪初梁启超(1873—1929)掀起“史界革命”、倡议“新史学”的义例为起始,然而探讨近代史学的演变,绝不能把有关问题独立于传统史学与时代世变之外。与此同时,学界往往注重一些被视为“主流”的史学思潮,而忽视了不少被认为是反对“主流”的历史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甚至以这些反对“主流”的言论为“旁支”,以致很多历史学者的贡献被湮没。在21世纪之际,处于“世纪回眸”的风气下,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视“主流”以外的历史研究,从而得见近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整体面貌。
当代学者曾经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特色是“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院制度集中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才,史学研究在专人负责下愈趋精密,由于注意史学专业的培训,史学研究更加专门化;及后随着历史学确立其专门学科的地位,史学研究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
然而,中国的史学研究,直至1919年五四事件后,才趋于“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中国古代有经学、史学、子学等部分,经学被视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而成为治世的依据;加上乾嘉学者的研究重心在经不在史,史学被视为经学的“附庸”,考证之旨不仅是厘清史事的真伪,且是疏通文字、通达经义,考证的重心,也在经而不在史。嘉道以降,西力入侵,边疆史地学始日渐受到重视。至晚清康有为(1858—1927)倡导疑经风尚,不但动摇了经学的地位,也带动疑旧史学的风尚,对传统史学也是一种挑战。但若没有学院从事专科知识培训,以及专业史学工作者的钻研,历史学是不能成为独立及专业的学科的。及后,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科史学门,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加上留学生日增,一方面输入了西方史学方法,另一方面亦促使本来在经学笼罩下的史学得与经学并列。五四事件爆发前的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当时是全国最高学府,其史学门虽于1919年前进行课程改革,但已经学院化的历史教育和研究,尚未谈到专业自主,史学仍被视为“国学”的一部分。及至五四运动后,大量留学生回国执教,又受到“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两种思想的影响,而开始进行学科课程的改革。1919年8月,北大史学门改名为“史学系”,但史学系只开设有关中外史学的课程,而修读史学系的学生,也不必修读经学课程,自此史学发展遂趋向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批判传统文化被视为“新文化”的特点,而北大史学系因顾颉刚(1893—1980)等人主张“疑古”史学,批判古史,由是也被视为“新文化”的代表。当时一些曾经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却往往被忽视,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学者的地位,更为人们所忽略。
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史学界,已有南北对峙之势,北京大学是北方的大本营,而南方的代表则为南高文史地部的教员和学生,他们在1921年至1922年创办《学衡》《史地学报》,其后又创办《史学杂志》等刊物,以言论、著作与北大学者做正面的抗衡,学界因而流传“北有北大,南有南高”之说。南高师生曾反对胡适(1891—1962)的白话文运动及顾颉刚的疑古运动,在“新文化”大受重视的学术气氛下,南高学者的地位便被忽略了。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于1915年,原址为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以下简称三江师范),此后校名屡有更易。1923年与东南大学合并,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1927年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该校校友往往把南高至中大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诚如胡焕庸(1919年入读南高)所言:“自南高至中大,学校校名虽经数易,而学校内容,实一线相承,绝少变易;凡治学于此,不论时间之先后,多具有同一之好尚。”陈训慈也说:“南京高师固然为今日中央大学始基之所自,不惟其图书设备犹多沿用至今,其精神遗产保留于今之中大。”该校的学生,视南高和中大为同一个教育事业机构,并视中大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建基于南高时期。又因三江师范至中大,均是同在一个校址,编写校史的作者亦把南高至中大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也承认南高时期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建基时期”。由此可见,南高时期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南高之所以为学界所注意,主要是因为1919年至1923年执教及就读于南高文史地部的师生,反对以北大学者为首发表的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但学者往往忽视了南高师生的治史特色。
现先讨论南高在民国(1912—1949)学术界的地位。曾参与古史辨论战的杨宽(1914—2005)说:“古史辨论战实为北京派和南高派的一场论争。”所谓“南高派”,就是指称执教于南高史地部的教员柳诒徵和他的学生缪凤林、张其昀等人,他们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言论。此外,曾是东大学生的顾翊群在回忆母校生活时也说:
民国四年(1915)南高成立,所聘请知名教师中,人文学者如刘伯明(1887—1923)、吴宓(1894—1978)、柳诒徵诸先生,为当代泰斗,努力启迪生徒,而隐然与资深望重之北京大学分庭抗礼焉。……北大除旧扬新,而南高则对新旧学术兼收并重,端观其(南京高等师范)有无价值以为评断,其(南京高等师范)态度较北大更为开放。
顾翊群指出,南高学人不如北大学者般强调反传统文化的思想,一部分留学美国的教员如吴宓、刘伯明等人,均与接受传统学术训练的史学系教员柳诒徵结交,一起教授学生中外文史哲知识,对中外文化采取融通的态度,由是形成一种有别于北大的南高治学风尚。东大毕业生王焕镳在回忆东大的发展时,也认为南高学风盛极一时。他说:
民国八、九年(1919—1920),朝野时彦,拾近世西洋论文论政,偏曲之见,暴蔑孔孟以来诸儒阐明讲说之理,谓不足存……当是时,南雍诸先生深谓叹息,以为此非孔孟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创办《学衡》杂志,柳(诒徵)师尤反对顾颉刚疑古之论,昌言抵排,为一时之风。
“南雍诸先生”就是指柳、刘及吴三位学人,他们深叹北大批判传统文化的论点,创办《学衡》杂志,标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与北大学者只知输入西方文化及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观点相抗。郭廷以(1904—1975)忆述他初到南京,其友乐焕文介绍南高学风时说:“南高名气不大,但在国内,北方是北大,南方是南高,算是最有名的学府了。”可见时人已认为南高既与其时反对传统文化的重镇北大相为并立,又是南方学界言论的代表。但应注意,时人所说的“南高”,主要应指执教及修读南高史学部课程的师生,特别是指柳诒徵和教西洋史科目的徐则陵(1886—1972)、教地学通论等科的竺可桢(1890—1974)、教西洋哲学史科目的刘伯明,以及一批主修史学课程的学生,而不包括外文系的吴宓。因为吴氏自1921年至1924年执教于南高,时间只有三年,对该校学术的影响尚未明确。而哲学系的刘伯明,自1919年起已是南高的全职教员,至1923年逝世,被南高史学部学生奉为“精神领袖”之一。徐、竺及刘氏三人开设的课程都是史学部学生的必修科目,对日后南高史学的发展甚有影响。最重要的“精神领袖”柳诒徵,自1915年至1925年执教南高,若论时间之长久,实超过吴、刘、徐等人。况且,柳氏曾为《学衡》写序言,又是1925年前学衡社的编辑,在学衡社担当领导者的角色,更是实践其所标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治学精神的人物。故“南高”一词,一方面指称执教南高史学部课程的人物,当中柳诒徵更是南高史学的中心人物;另一方面,“南高”也指修读南高史学部课程的学生,因为他们既为《学衡》的编辑成员,又在求学阶段办《史地学报》,毕业后仍协助出版《史学与地学》及《史学杂志》,努力介绍中外史地学知识,借史学研究保存中国文化,继承及实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至于当时任教及修读国文科、外文科的师生,则并无类似的活动。本书以“南高史学工作者”或“南高史学者”一词,指称柳诒徵及以他为中心而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学生,特别是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四人;而“南高史学”,主要就是指柳氏及上述四位学生的史学研究观点及治史方法。
南高于1920年进行课程改革,国文系、史学系、地学系先后成立,依课程规定,学生在选择本科及辅修学科后,按指定本科所修的学分,定其所属的学部。以修读史学课程为本科的学生,必须要修读一部分地学系及哲学系开设的课程,故史学部学生能兼及地学与哲学,其中结合史地学的研究方法,尤为南高史学特色之所在。其时学生所属的学部,名为南高文史地学部,实则国文、史学、地学三个学系独立发展,而统属于文史地部之下,学生选取史学系或地学系或国文系为本科后,定其修读课程所属的学部。本书为求清楚交代南高史学的发展,便以“南高史学部学生”一词,指称1919年至1923年在南高修读史学系开设课程的“本科”学生。由于学生同时要修读地学部的课程,故书中亦涉及南高地学部的发展,后来地学部进一步独立,由是形成南高史地学分途发展的局面。
然而,对南高史学的研究尚付阙如。近人对民国史学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四方面:(1)史学通史式的介绍;(2)以学派的研究方法分析民国史学发展;(3)以专题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些专题多集中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古史辨运动”等;(4)对个别史家进行研究,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钱穆、胡适、李大钊、李达、郭沫若、王国维等。以上研究中国史学的论著,多着眼于主流的学派或显而易见的史学发展,鲜有谈及史学的其他流派,南高史学就是这样一处被忽略的伏流。
同时,学者还因下列两项意见,而每多贬斥南高史学的地位。其一,近人多持“新文化”与“旧文化”相对的概念,认为五四运动期间,吴宓、柳诒徵等执教于南高的学者,曾反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及陈独秀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胡适等人的言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而持相反论调的南高学者,便被视为“保守”或“守旧”的学者,治五四运动史的专家周策纵也以“保守的教育者”一词指称这些反对“新文化”言论的南高学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也忽视了南高史学的地位。
其二,近人多注意学衡派研究,而忽视了南高史学。早自20世纪70年代,学界在否定“保守”与“现代”冲突的研究学风下,对那些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重新展开评价,然而这些南高史学者多被视为学衡派成员,他们治史的特色往往被忽视了。近人注意的南高学者包括执教外文系的吴宓、梅光迪(1890—1945),哲学系的刘伯明,及史学系的柳诒徵,学界把他们视为学衡派的成员,他们出版的《学衡》杂志亦被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言论的代表。在重评保守派地位的气氛下,学衡派首先受到注意,中外学者先后完成多篇博士、硕士论文,主要如侯健于1980年完成有关白璧德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后侯氏更把其博士论文改写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书,在侯氏指导下的沈松侨,也完成了题为《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的硕士论文,并出版成书,由是推动了学术界对学衡派的研究。单篇论文方面,也有林丽月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等。此外,近人也对学衡社的领导人物吴宓、梅光迪、汤用彤做了专题研究。但以上著作,多注意学衡派的发展,以及学衡派对中西文学和文化的评价,尤多讨论吴、梅、汤三人的治学思想及方法,却未注意南高史学者如柳诒徵的治史思想,及南高史学部学生借办学术刊物延伸“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思想的特色。
至90年代初,学者在重评学衡派地位之风的带动下,开始注意研究南高史学工作者的治史特色。孙永如的《柳诒徵评传》一书,已肯定柳氏不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反对把柳氏“打入反动文人的行列”,但孙氏尚未探讨柳氏治史的核心是礼教文化的观点。至于专注研究柳氏史学方法及史学理论的文章,有康虹丽的《论梁任公的新史学和柳翼谋的国史论》、李宇平的《柳诒徵的史学》、李洪岩的《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文化思想析论》,以上论文多探讨柳氏治文化史、考源史料的特色,尚未注意他提出的“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史学要义,也未谈及其学生如张其昀、缪凤林等人,如何传承与开拓柳氏的治史观念及方法。
最近五年,才有学者注意到南高史学者的治史特色。论文有郑师渠的《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及《“古今事无殊,东西迹岂两”——论学衡派的文化观》,张文建的《学衡派的史学研究》及《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影响》。彭明辉的《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一书,则将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与南高史地研究会刊行的《史地学报》做比较,并认为“以北大为主体的《禹贡半月刊》,和以南高为主体的《史地学报》,应可视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书中也开始注意南高学生如张其昀、陈训慈等人治史地学的观点。但以上论著,只撷取南高师生在后期刊行的《史地学报》及《学衡》杂志上所发表的史学研究言论,对南高师生在《史学与地学》及《史学杂志》上发表的论点未加探讨,也没有说明他们在后期学术上分流发展的情况。
如上所述,前人只注意北大的反传统风尚,以致忽视南高史学的地位,故本书旨在对南高史学展开全面的研究,阐明南高史学的特色,从而肯定其贡献。从以下几点,可见南高史学甚具研究价值。第一,南高师生受师范教育的影响,注意借史地学研究推动道德教化及保存传统文化,从宏观及致用的角度研究史学,努力推动史地学研究及历史地理教育学的发展,实有异于北大“窄而深”的治史观念及方法。第二,南高史学者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建构和解释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在“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之余,亦冀“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他们推崇中国文化,但并不排斥西学,所以不应因他们反对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而将他们视为“保守派”的学者。虽然南高史学者注意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致其史学研究未能朝向专业方面发展;然而,史地部学生由追随柳诒徵治传统史地学,渐转向史、地二学分途,并兼治中外史学,由此也可见近代史、地学科步向专业分科发展的历程,故学界不应忽视对南高史学的研究。
本书主要以柳诒徵执教南高史学部(包括国立东南大学史学系及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历程为主线,并以1919年至1923年于南高文史地部修读史学部课程为主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尤以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及郑鹤声四人的治史观点及方法,作为本书的研究重点。以柳诒徵为本书论述主线的原因有四:
其一,1919年起,南高文史地部独立发展,史、地二科分别成立学系,不再是国文科的附庸,史学研究趋向专业化,学生就读的学部,名为南高文史地部。学制规定,按修读学系的课程多寡,定其为国文部、史学部或地学部的毕业生;而教员则按其专业研究范围,定其所属学系。柳诒徵是第一届南高史学系的全职教员,至1925年离校为止,其间未尝间断,执教共十年之久;此后又于1928年以兼任史学教员的身份,执教中大史学系。他长期从事南高史学部学生的教育工作,影响甚大。
其二,1919年至1923年就读于南高史学部的第一届学生,被认为是南高文史地部历来“最优秀之一班(空前而绝后)”。这届学生最具南高史学特色,他们又都奉柳诒徵为“精神领袖”,故柳氏的治史方法和观点,亦最足以反映南高史学的特色。
其三,对于南高文史地部师生创办的学术组织及出版物,柳诒徵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1921年南高文史地部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及1930年中大史学系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均以柳氏为指导员;而这些学会的出版物《史地学报》《史学杂志》,也由柳氏任编辑或指导员。柳氏更为这些刊物撰写序言或发刊词,树立南高史学“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及借着史学保存文化的研究方向。柳氏虽于1925年离开南高,但得学生张其昀的帮助,以东南大学史学系名义出版《史地学报》,并以东大史学系作为整理文稿的地方,使南高史学不因1925年东大学潮而中断,柳氏始终是维系南高史学的中心人物。
其四,柳诒徵是南高史学发展的启导者,如南高史学部学生陈训慈,日后成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后,从事辑校乡土文献的工作,他认为“此次之始辑校史,开始即受柳师之启迪”。史学部第四届学生郑鹤声也指出,“在南京高师学历史的人,大半受柳先生的影响”,柳氏在评定学生的论文后,“择优选登在《史地学报》或《学衡》上”,可见柳氏极力扶持后进,而郑鹤声也在柳氏的指导下,进行汉至隋代史学的研究。故此探讨南高师生之间史学方法的传承与开拓,可以进一步得知南高史学的发展情形。
至于本书以1919年至1923年修读南高史学部课程的第一届学生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及在1921年入学的第四届学生郑鹤声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南高史学者之间的师生关系,是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1919年后入读南高史学部的学生,其修读的课程甚具特色。前文已提到,1919年南高文史地部成立,代表了史学专业发展的先声,而南高史学部在此年开始,规定学生除了修读史学科课程,还必须修读史学系开设的人文地理及地学系开设的地学通论,此二科由留美学者竺可桢教授,传授西方地理及地理教育的研究方法,此与南高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及柳诒徵提倡的“史地通轨”的治史方法互相阐发,形成南高史学结合史、地及史地教育的特色;同时,哲学系开设的西洋哲学史科目,及史学系开设的西洋史科目,都是史学部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使他们能够吸收西方道德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由是形成南高史学部学生结合中外史学及哲学的研究特色。以上的课程结构,对1919年后入读南高史学部的学生起了启导和模铸的作用。
第二,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及郑鹤声四人,均为柳氏及其他教员所称道。在1919年入读南高史学部的学生当中,张其昀“长于史学”,陈训慈“好深思,长于史学,喜谈江浙学风”,缪凤林“甚博学,恒勤学,喜评论,长于历史,多作文章”;柳诒徵除了欣赏这三个学生,又认为1921年入学的郑鹤声是“得力最深,用功最勤”的学生。他们都承认在治史方法及观点上,受到柳氏的影响,借研究他们的治学情况,自可见师生间的传承及开拓关系。陈训慈及郑鹤声承认其治史方法受到柳氏的启导,已见上文引录。张其昀也说:“柳(诒徵)先生的教泽,是终生受用不尽的。因为当时我校(南高)新设地理课程,他指示我们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踪二顾之学——顾亭林(顾炎武)的史学和顾景范(顾祖禹)的地理学——相勖勉。现在回想起来,得益最多的有三点,就是(一)方志学……。(二)图谱学……。(三)史料学。”足见张其昀是因得到柳氏的启导,而开始注意传统地理学研究的方法的。缪凤林亦谓:“吾就学南高,每念及柳师曾言‘吾国礼乐制度崩坏,急宜补弊起废,求明先圣之志,达万世之思’,深喟叹息,今欲承吾师之志不敢殆!”缪氏研究中国礼学史,就是受到柳氏的引导。此外,这四位学生均是积极参与南高史学活动的人物。他们就读南高期间,成立南高史地研究会,并任《史地学报》编辑;毕业后,或返回其时已改名为东大的史学系继续学业,或任教于其中,都在同一个学术机构内,且以机构的名义出版学术刊物,并协助柳氏出版《史学与地学》及《史学杂志》,使南高史学得以传承下去。
最后还需指出,本书以1915年至1931年为研究断限。因为南高成立于1915年,柳诒徵于此年执教于该校,而文史地部乃拓源自南高的国文史地部,故本书以1915年南高国文史地部的发展为论述的起点。虽然柳氏在1925年离校,在此之前,陈、张、缪三人又于1923年毕业,但1926年后柳氏因张其昀回校执教于史学系,以及陈、郑二人转读东大史学系课程,故能一起以东大史学系为整理文稿及师生聚会的地方,《史学与地学》因此得于1926年顺利出版,由是延续了南高史学的发展。及至1928年,张其昀离开史学系,执教于地学系,但柳氏与陈、缪三人,因在中大史学系任教,成立中国史学会,并以中大史学系名义出版《史学杂志》,中大史学系由是成为南高史学者收集文稿及聚集往来的地方,使南高史学仍能相承不替。而至1931年,《史学杂志》第2卷第5、6期合刊出版之后,没有继续出版,除了缪凤林仍执教于中大史学系,柳氏与张、陈、郑诸人此后皆不在同一学术机构工作,亦不以同一学术机构的名义出版刊物。况且,1931年后各人虽出版不同的学术刊物,但这些刊物上的发刊词或序言,已不奉南高史学的“史地通轨”及借史地学研究以保存中国文化的宗旨。因有关教员分散各地,又没有一同出版学术刊物,各人的治学方向有了改变,故1931年实为南高史学由“史地通轨”改为分途发展的转折点。
本书参考的数据,主要运用了1921年至1931年,由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一起出版的学术期刊,如《学衡》(1922—1933年)、《史地学报》(1921—1926年)、《史学与地学》(1926—1928年)及《史学杂志》(1929—1931年),借这些刊物的内容,以见南高史学的发展,以及有关史学研究者的观点。
本书又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数据,如《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等;以及相关的校史数据,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高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台北“国史馆”藏《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地理历史选科学生履历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一览表》,还有1949年后南京大学校史编辑组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京大学史(1902—1992)》,朱斐编《东南大学史》,朱一雄编《东南大学校史研究》等。以上数据包括南高、东大史学系的课程、教职员及学生名单,借着南高史学部、东大及中大史学系开设的科目,从而得见课程与南高史学发展的关系。
学界探讨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及治史方法,主要根据柳氏著《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本书更运用了南京图书馆馆藏柳诒徵所撰《东亚各国史》等著作,这本书至今尚未为学界所注意。在研究缪凤林的治史特色时,本书除了引用缪氏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还参阅了台湾省图书馆内罗刚纪念馆收藏的《中国礼俗史》一文,以探讨缪氏的礼学思想。论及陈训慈的治史情况时,除了引录陈氏以“陈叔谅”为名出版的《近世欧洲革命史》《世界大战史》,更运用南京图书馆藏本陈训慈所著《西洋通史》等,以见陈氏治中外史学特色。论述张其昀治史地学的特色,多取材自张氏所编的地理教科书。至于郑鹤声的治史方法,除了参阅郑氏编著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及《中国近世史》二书,也引用了上海青年会图书馆所藏郑氏编著的《中国历史教学法》。
本书主要采用人物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并从史学与学术机构发展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做出分析。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二部分为专章论述。第一章论述柳诒徵与南高史学风尚形成的时代背景。柳氏既被南高史学工作者奉为“精神领袖”,所以本书先介绍他的史学及传统道德文化知识的来源,并略述其生平;接着从晚清师范教育、江浙学风、江浙藏书事业,五四前后激进的反传统文化言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西文化调和论等方面,探讨形成南高史学工作者重视传统文化、推动史地教育及治史地学特色的原因,并注意西方哲学、历史学及地理学思想在南高文史地部传授的情形。第二章、第三章阐述南高史学的发展概况,以其“精神领袖”柳诒徵在南高史学部任教的经历为主线,结合南高文史地部、东大史学系及中大史学系的发展,师生一同编印《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的始末,将南高史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15年至1918年是“成立阶段”,1919年至1925年为“成长阶段”,而1926年至1931年为“分途发展阶段”。第四章析论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以及其史学思想特色,特别指出柳氏所提“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是柳氏治史的重心所在。第五章介绍柳氏曾加以称许的南高史学部学生张其昀、陈训慈、郑鹤声、缪凤林的史学研究,以见师生之间在学问方面的传承关系,这批学生也曾师事不同的教员,各自又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因此开拓了柳氏未加注意的史学研究领域。第三部分为结论,对南高史学做出评价,厘清一些尚未受到重视的课题,使民国史学发展的面貌更见完整。
——摘自区志坚:《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
柳诒徵出身传统经学,他借着对中国文化史及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切爱护,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礼教伦理的责任,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他以一个时代见证人的身份教写中国文化史,尤具意义。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
目前学界对于南高“学衡派”已进行过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对于柳诒徵个人的思想、学术也不乏研究,但对于由柳诒徵及其弟子所构成的南高史学群体却相对缺乏深入讨论,尤其是缺乏在“新史学”演进背景下及与北大史学相比较视野下的具体研讨,本书恰是在这方面多所用力之作,从而弥补了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帆
南高学者文史兼容、史地并重,由中国史至西洋史均见措意,又以成立学会和出版刊物互相配合,于治史方法和学术观点上都彰显其特色。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南高学者大体上站于北大学者的对立面,但既以“北大南高”并称,个人认为,时人对于南高是认同其重要地位的。北大学术与南高学术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术的一体两面,忽视南高,对于五四新文化尤其是“新史学”的认识就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了。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新亚研究所教务长周佳荣
就南高而言,由源起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演变而成东南大学,以至中央大学,其所创建的史学风气,主张绍继传统,吸纳西学,以会通中西文化为其治史特色,此即志坚博士新书所研究者。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李金强
编辑推荐一:
在民国学术的璀璨星河中,北大与新文化运动的光芒常被视为主流,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的史学群体却被长期隐没于历史长河。《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首次将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的学术沃土,以柳诒徵为核心,钩沉其与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弟子的治史实践,揭开一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术史诗。
本书以“史地通轨”为钥,还原南高学派如何在五四新文化浪潮中逆流而上,既坚守传统礼教文化的精髓,又融汇西方哲学、地理学与史学方法。柳诒徵提出“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以史为镜,鉴古知今,将道德教化与史学研究紧密结合;其弟子们则各展所长:张其昀开创人文地理学,陈训慈深耕中西史学比较,缪凤林探索礼俗史与民间文化,郑鹤声拓荒近世史研究。他们以《学衡》《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等刊物为阵地,既反对北大的疑古思潮,又积极吸纳西学新知,构建起“守正创新”的学术范式。书中更以海量珍稀史料为基——从尘封的档案馆文献到南高师生未刊手稿,从《国史要义》的深邃到《东亚各国史》的广博——层层剥茧,展现南高史学如何从传统史地学向现代学科转型。这不仅是一部学术史的重构,更是一场文化精神的寻根之旅。在“昌明国粹”的旗帜下,南高学者以史学缝合传统与现代的裂隙,为今日的学科融合与文明对话提供了百年镜鉴。
编辑推荐二:
当“保守”与“革新”的标签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以深邃的笔触,为民国学术补上了一块缺失的拼图。
本书不仅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南高史学的专著,更是一部叩问文化根脉的思想录。书中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核心,展现南高学派如何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既反对激进的反传统浪潮,又积极引介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兰克的实证史学;既以江浙藏书为根基深耕本土文化,又以世界眼光重释中国历史。柳诒徵的“通则”与“独造”史观、弟子们对人文地理与地方史的开拓,无不彰显“守旧”表象下的开放胸襟。更令人动容的是,本书揭示了学术传承的温度。从柳诒徵在《学衡》发刊词中的殷殷嘱托,到弟子们辗转各地仍以刊物维系学术血脉,南高史学的兴衰恰似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
在史料考据之外,作者区志坚博士以二十年深耕,将南高学者的手札、信件、文章、著作化作鲜活叙事,让读者得以触摸那个时代学人的热忱与坚守。尤为珍贵的是,本书不囿于学派之争,而是深入南高史学的肌理:从课程设置到学术组织,从师生传承到史地分途,勾连出一幅民国学术生态的全景图。今日,当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碰撞,南高史学的“融通”智慧尤显珍贵。这本书不仅是学术史的补遗,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文化自信的深层逻辑——传统不是枷锁,而是创新的土壤;西学不是威胁,而是对话的伙伴。对于每一位关心文明传承的读者,这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思想盛宴。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学术的发展,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为教员与学生的学问相传,二为建立安稳的学术机构,如大学课程及学系的发展。借大学及学系提供的资源,网罗师资、广收学生,学系成为一个团结师生的凝聚工具;又或一些师生组成学术组织,如学会等,使在大学行政机构及课程以外,另有一个师生相聚、相讨学问的地方。又因为师生共同参与学会活动,或出版学术刊物,不独增加师生学问上的交往,更使学生多了解教员的研究成果,学会也成为团结师生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此外,学术的发展,也有赖于学术领袖的出现,学术领袖领导学术组织的发展,培训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学术研究方法及观点的“典范”,成为学生进行研究的效法对象。师生遵循着学会成立的宗旨,若学会没有成立宗旨,则从师生间团结一起,以同一机构的名义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刊载的发刊词,或弁言,或序中,可见这些学术工作者的治学精神,这些序言或弁言,又成为团结师生的工具及师生进行研究的指导方向。故学术发展,有赖于学术机构,也有赖于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学术刊物及学术刊物上的发刊词,或弁言,或序。学术研究蔚然成风有赖于师生间学问的传承关系,而在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教员所传授的知识,又成为学生吸收知识的重要途径,学生往往因吸收不同知识及各自不同的研究兴趣,又开拓了师说。总之,学术研究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学者思想的传承因素,另一方面有赖于学术机构的发展。
本书以1919年执教及就读于南高史学部的师生为探讨对象。其一,南高不仅是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史上较早出现的师范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寓师范教育于专业之中”的机构,“南高诸师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南高成为一个结合师范教育专业发展及学术研究的机构。借研究南高史学部的发展,可见中国师范教育传统与南高治史风尚形成的关系。南高师生的治史风尚,主要是结合了道德教化及求实用的治史目的,这有别于其时北大以专科训练为主及“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风尚。北大的治史风尚,以考证文献为主,力求文献的真实,往往认为史学不再是圣皇的载道工具,从而得以澄清史料的真实面貌。
其二,南高昔日为晚清三(两)江师范学堂,于1915年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其后又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至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虽校名屡易,但学风在中大成立之前相为传承,主要朝向“寓师范教育于专业之中”,其中1919年后史学部的发展,尤见近代学术自传统史、地合一,发展至史、地分途的专科发展特色。盖文史地部的前身,为国文史地部,自1920年,史地部脱离国文部,独立提供专科知识,及至1928年后地理学系进一步倡言独立,把昔日属于史学系开设的人文地理及经济地理的科目,改由地理学系开办,由此可知史学系及地学系渐趋于学术专科的发展方向,又可知南高史学工作者自中国传统结合治史地学的特色,发展至史、地分途研究的情况。
其三,重评南高史学工作者的地位。当时学术界认为:“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通中西为职志。”就读南高的学生王焕镳也说:“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朝野时彦,拾近世西洋论文论政偏曲之见,暴蔑孔孟以来诸儒阐明讲说之理,谓不足存……当是时,南雍诸先生深膑太息,以为此非孔孟诸子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也,创办《学衡》杂志,昌言抵排。”以上文中所言“南雍诸先生”,就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执教南高史学部的一群教员及就读其中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风尚与代表北方学风的北京大学相抗。然而在北大教员胡适、陈独秀及日后燕大的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的背景下,南高史学部师生的言论及治学方法,被认为“保守”,在研究领域上,不独不注意其学术地位,更贬斥他们的研究成果。本书借研究南高史学部的“精神领袖”柳诒徵,以及被柳诒徵视为“执教南高,历有数年,以张、缪、陈、郑诸子为得力最深,用功最勤”的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的治史特色及方法,可见师生们治史方法的传承与开拓之关系,也从中得知不可以简单地用“保守派”或“守旧派”这一类形容词来概括他们的治史特色。同时,他们虽有其不同于北方学者的治史特色,并曾反对北方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柳氏也没有介绍西方学术成果,但他们也鼓励学生积极吸收中外史地知识,扩阔国人的视野,《史地学报》的创办就是一例。南高主修史学部课程的学生也致力援引西学,借西学知识,重新诠释及保存中国文化,并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地位及意义,实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治史特色。故不可片面指斥他们为“保守派”的学者,并在研究领域上加以轻视。
其四,本书主要从传统学术发展至近代学术的脉络,研究南高史学的形成及治学特色,从中可见南高史学工作者一方面传承中国传统学术、弘扬道德教化及注意学术经世致用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吸收及运用西方史、地、哲知识,进行史学研究,实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特色。故不可因南高史学工作者反对以北大为首的新文化运动,而片面地认为其属于“保守”的学者,并忽视其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应该视他们为民国史学界甚具治史特色的学术工作者。
除以上四点,南高史学甚具学术特色;但若探讨南高史学的特色,应先探求南高史学出现的原因及时代背景。南高史学的出现,固然与南高秉承晚清三江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传统有关,且受到南高史学“精神领袖”柳诒徵教导的史学方法及研究观点所影响。同时,因柳氏执教南高,学生了解到江浙先贤顾炎武、顾祖禹及章学诚治历史地理学、方志学的特色及要义,尤其顾炎武提出的求通观及学术致用的观点,及章学诚对方志学的看法,更成为南高史学工作者治方志及史地学的知识来源之一。加上南高邻近江苏国学图书馆,馆中藏书以收藏江苏、浙江两地明清文人的文献、方志为主,而南高史学工作者又多往馆中借阅藏书,日后也因得阅此地藏书,并多推动研究地方文化的工作,故江浙学风、藏书事业的特色亦成为南高史学工作者吸收传统学术知识的途径。
至1919年五四事件爆发,国内出现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言论。随后,在反传统学风带动下,出现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认为昔日被奉为道德圣贤的形象,如舜、禹的圣人事迹,均是后人伪造的,并怀疑经书、史书所载的古史的真实性。学界既出现了批判传统的言论,由是激起了支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及圣贤道德教化的言论。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外学术界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及重视西方文化而轻视东方思想的弊点,由是国内外出现一股提倡中西文化调和的思潮。而执教南高史地学部曾留学美国的教员,一方面反对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被中西文化调和论的思想所影响,由是多探求及实践西方学理。而他们开设的课程均是史学部学生的必修科目,故使南高史学部学生得以修读这些留美教员执教的科目,从而吸收西方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的知识。例如,学生修读刘伯明开设的哲学系课程,便能学习西方哲学及结合哲学与历史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修读竺可桢开设的地学通论及人文地理科目,可以了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知识;而修读徐则陵开设的西洋史一科,能够学习西方历史学及历史教育学的知识。
南高史学的发展除了以上所述及的时代背景及留美教员传入中外史地学的知识,更有赖于学术机构的发展。1902年三江师范成立,历经南高、东大、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至1928年中大成立,这几所大学虽然校名屡易,然均在同一地址上兴筑,其间学系虽有增减,但南高的史学部、东大及中大的史学系,均在同一地点上发展。史学部教员的办公地点,史学系的上课地点,以及学生举办课余活动的地方,自南高至中大,均是相沿不改。南高史学部师生创办的史地研究会,以及日后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其收发文稿的地点及师生聚会的地方,也是没有改变。南高的史学部,乃至中大的史学系,可视为一个学术发展的整体。另外,随着专业学科的发展,南高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自史地结合,至史地学分途发展的情形,而南高史学最初奉行“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而最终史学与地学分途发展,由是使南高史学工作者也自团结一起至分散各地,最终出现南高史学结束及瓦解的情况。
1915年至1931年,南高史学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1915年至1918年,为南高史学发展的孕育阶段,南高国文史地部成立,聘任南高“精神领袖”刘伯明及柳诒徵执教其中。南高也从辛亥革命(1911)之后,渐次复完,学制及课程日渐设置,并确立了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1919年至1925年为南高史学发展的成长阶段,于1919年入学的学生有张其昀、缪凤林及陈训慈,此届学生被认为是柳氏执教南高期间“最优秀的一班”;至1921年又有郑鹤声入读其中。而以上四人的治史方法,既受柳氏称誉,也多有传承及开拓柳氏的地方。在南高史学部学生中,以上四位学生在求学阶段,或是毕业之后,均积极参与及协助南高史学工作者出版学术刊物及成立学术研究会。此阶段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及出版的《史地学报》,提供了南高史学部师生首次合作的机会,然而此阶段亦出现了南高史学工作者分散各地的现象。首先,1923年,南高文史地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相继离校,在缺乏人力支援下,史地研究会已出现人手不足的问题;其次,“精神领袖”刘伯明病死,已使南高顿失重心,尤其自1925年东大发生学潮,另一位南高“精神领袖”柳诒徵也因此而离校,顿使南高史学工作者缺乏领导人物。1926年至1931年为南高史学发展自学术专业化步向瓦解及结束阶段。自学潮后,柳氏北上,但他借出版《史学与地学》及借助东大史学部使南高史学部的毕业生再次团结,并以继承史地学研究方法为职志,延续史地研究会及《史地学报》的办报精神,继续提倡“史地通轨”及史地教育,借史地学研究保存中国文化的特色。1928年,柳诒徵、缪凤林及陈训慈先后执教中大史学系,成立中国史学会,及后郑鹤声也因任职南京教育部,参与南高史学者的出版工作。因感竺可桢于1928年提出“史地分途”及使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二科脱离自史学系,改从属于地学部之下,又出版《地理杂志》,柳氏便与缪、陈诸学生于1929年出版《史学杂志》,欲重拾“史地通轨”的治学方法。而自1928年竺氏发表使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脱离史学系,改由地学系开设的言论后,张其昀也于此年秋天,自执教史学系,改任教至地学系。加之,《地理杂志》又于1928年出版,故此年代表“史地分途”的先声。同时,《史学杂志》出版至193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后,便没有继续出版;而自此年以后,柳氏主要的工作地点为中大国学图书馆,而不是中大史学系。陈训慈也于1932年改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其后郑鹤声任职国立编译馆,只有缪凤林一人自1931年至1947年仍执教中大史学系。自1932年后,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及柳诒徵再没有以中大史学系的名义出版学术刊物,也没有一起工作于中大史学系,没有一起组织学术研究会,就此可见从1932年开始,南高史学已进入学术分途发展的阶段。《史学杂志》成为南高史学部师生合作出版的最后一本学术刊物,而南高史地通轨的瓦解及结束,也主要是学术研究趋向专业化所致。
虽然南高史学于1931年秋天之后,已步入瓦解及史地分流发展的阶段,但从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学衡》《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及《史学杂志》上发表的言论中,仍得见他们的治史方法及观点有以下特色:(1)在研究范围上,介绍及研究中外历史学及地理学、历史教育、地理教育及地方史的知识。(2)致力介绍中外传统文化及道德思想。(3)在治学的取向上,一方面涵泳中国传统史地学,另一方面从西学中汲取养分,对中国传统史学,多采取信古态度,而不取疑古史学的观点。(4)在资料的运用上,以史籍记载为主,多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史。(5)在研究方法上,多援引西方学术,重新阐明中国文化的特色。虽然在介绍西方地理学、历史学及哲学思想时,不免有“半生不熟”的情形出现,但在中西文化及学术交流的过程中,这类适应是必需的。而在涵泳传统中国史地学的部分,虽有所爱于经世及取信于史籍,难免在学术上缺乏批判及怀疑史料的精神,也难免在学术客观与政治现实之间略有所倚,但处在当时的环境中,似亦无须苛求。整体而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南高史学工作者所办的学术期刊,师生间传承与开拓的治史方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提倡历史学、地理学、历史教育学、中国史学的研究风气上,南高史学确然经历了自传统结合史地学的研究过渡至史学、地学专科研究的发展,自史地文献考据过渡至人文地理学、地理教育学、历史教育学。而在研究范围方面,南高史学也确然经历了自古代史学过渡至近代史的过程。至于研究工具方面,南高史学经历了自文献资料发展至兼习民俗、出土遗物。最后,南高史学经历了自发展中国史学至兼集中外历史的过程。由此可见,南高史学发展确有其阶段意义。
除此以外,南高史学工作者的治史方法及观点方面,也呈现出一些特点。以南高精神领袖柳诒徵及被其称誉的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及郑鹤声为例,柳诒徵提出“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史学即礼学”的观点,其以礼为中心的史观,借史学研究弘扬道德教化及“鉴往知来”的特色,使史学成为资治借鉴的工具。这固然与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不谋而合,也可见柳氏传承了传统史学“资治通鉴”的特色。因为史学与治道有关,所以柳氏借编《中国文化史》一书,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又借研究地方史,以阐明地方教化。又因通鉴历代,才可有益治道,所以又注意研究通史及文化史,以求人类的“通则”;同时,又因笃信史籍的内容,以为孔子及司马迁的记载尤为可信,所以对上古史均采取“信史”的态度。然而,其学生因为不同的研究兴趣,以及受到执教南高的留美学者所影响,一方面既上承柳氏治史的观点及方法,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柳氏尚未注意的地方。例如,张其昀既上承柳氏爱好中国文化的特色及治沿革地理及历史地理的方法,又因师承竺可桢,从研究沿革地理,转向研究及推动人文地理学及地理教育学。陈训慈也上承柳氏借地方史重振地方道德教化的观点,但因陈氏的研究兴趣及师承徐则陵提倡西洋史学的方法,故开拓了柳氏尚未注意的地方学术史、西洋史学的研究范围。郑鹤声既上承柳氏治中国通史及历史教育的特色,亦因个人兴趣及受时代环境所影响,而开拓了柳氏尚未太多注意的近世史范围。最后,缪凤林既上承柳氏治中国通史及中国礼俗史的研究范围,也开拓了柳氏尚未注意的,以民间风俗、神话传说及出土遗物引证史籍内容的治史方法。由此可见,昔日南高史学部毕业生,既传承及开拓了柳诒徵的治史观点及方法,又注意吸收西方的治史方法及观点,也注意利用新方法治史,故不可因他们曾反对新文化运动,而片面断言他们是“保守”的学者,并忽视他们在史学上的地位。
总括而言,南高史学工作者,既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又力重道德教化及史学致用的特色,且介绍了西方史地学的研究成果及方法。虽然南高史学工作者的治史方法,不同于只提倡问题取向、“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只求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也不同于借治史求致用的现代学术研究观点有关现代学术的研究特色;然而也不可简单地以“保守”“守旧”之词,概括南高史学工作者的治史特色。他们不独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史学的研究,并且积极介绍西方历史地理学、历史教育学及哲学思想,故从传统学术与西学的接触上,南高史学者确有其一定的阶段性意义。
——摘自区志坚:《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