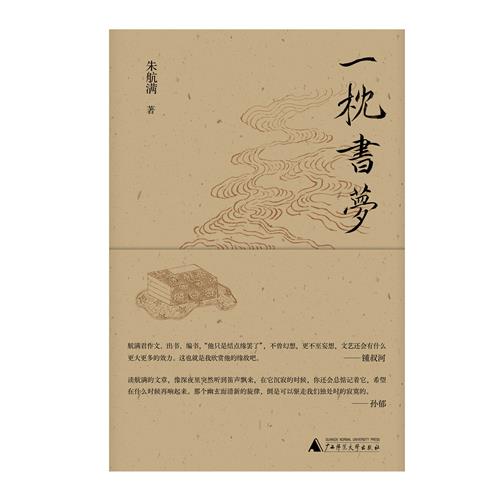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1-01
定 价:72.00
作 者:朱航满 著
责 编:吴义红
图书分类: 中国现当代随笔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散文随笔
开本: 32
字数: 160 (千字)
页数: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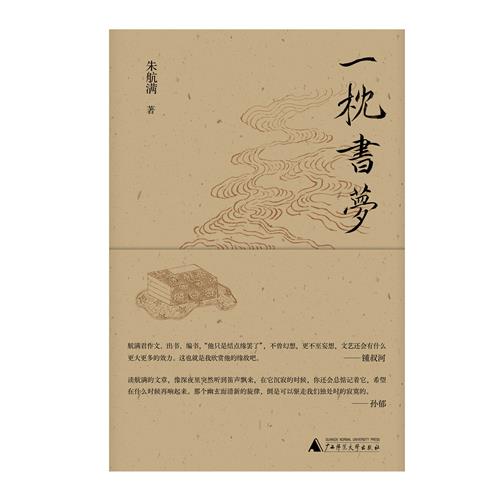
《一枕书梦》是著名散文随笔作家朱航满近年来的读书随笔集,包括《雪天访书》《逛旧书店杂忆》《塔下买书记》《北大书事抄》《鲁迅故居买书记》等篇章。谈作者在京城购书的经历,亦可见当下京华阅事之一斑,其中北京的古迹,如万松老人塔、鲁迅故居、圆明园遗址、北大燕园、地坛公园,读来颇有滋味;趣读周作人及其苦雨斋文人的点滴,其中谈废名、汪曾祺、谷林、陈乐民、孙郁等,乃是一脉文心,于细小处见功力;作者喜好读书的记忆,其中谈张充和的书法、吴藕汀的画册、李文俊的收藏、锺叔河的书信、赵珩的饮食谭,娓娓道来,趣味横生,如沐春风。朱航满追求古朴清明的文章风格,作文质朴,见识通达,颇可一读。
朱航满,1979 年生,陕西泾阳人,著名散文随笔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南京、北京等地读书,文学硕士。写作有随笔、书话、游记、文学评论等,近年来倡导古朴清明的文章风格。曾出版随笔集《书与画像》《读抄》《木桃集》《立春随笔》《雨窗书话》《杖藜集》等多种,编选花城出版社2012 年至2020 年《中国随笔年选》,策划并主编黄山书社“松下文丛”,编选《念楼话书》曾入选多个好书榜单。
雪天访书/001
逛旧书店杂忆/007
塔下买书记/012
北大书事抄/019
鲁迅故居买书记/025
我与布衣书局/031
因书而美/037
地坛书市一瞥/041
辛丑购知堂著作记/047
元旦杂抄/053
我的爱读书/060
海滨消夏记/064
西湖半月书事/070
知堂遗墨琐谈/077
“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083
《周作人散文钞》的注释/090
周作人选集过眼/096
周作人与北京风土书/108
废名谈新诗/114
“用我的杯喝水”:
《念楼话书》编后记/121
陈乐民的士风/131
喝茶、读城与文坛掌故/136
我的老师陆文虎/141
君子文章/148
有了Google或百度,“吾衰矣”/154
我看《蒲桥集》/160
年年岁岁一床书/166
藕汀画册两种/200
张充和题字闲话/206
旧书摊与翻译家/212
谷林『情书』/216
锺叔河先生的信/219
老饕三笔/231
清谷子张/235
我读期刊的记忆/240
芳草地谈书/246
我的第一本书/250
逛冷摊,拨寒灰,访师友/255
雨窗闲话书/260
跋/265
自序
近来编了一册关于书的文集,本拟名为书话集,想起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对书话的阐述,乃是“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并被热爱书话的朋友奉为圭臬。作为也曾自以为写过几册书话著作的作者,我读唐弢先生的这个对于书话的定义,感觉颇有道理,但对比时下各种书话作品,却总是觉得不是滋味。由此想来,书话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可以看作是关于书的纪事,关于书的闲话,关于书的掌故,以及关于书的趣闻,这也便是唐弢先生所说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对于热爱写作的朋友来说,写作书话,其实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有无这“一点事实,一点掌故”。真正的书话写作,其实并非人人可为,而是掌握这些“事实”与“掌故”的作者,他们或者是编辑家、出版家、藏书家,甚或是极有情趣的文人学者。而由此,书话,也才能成为他们在闲余之际所写的一种特别文章。我以为很少有专门的书话家,因为关于书的“事实”与“掌故”毕竟是有限的。作为藏书家的黄裳先生,晚年就常常会为写文章没有材料而苦恼。书话作为一种文体,又因为这“一点”的缘故,多是短的,很少长篇大论;又因为“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则又是言之有物和活泼可读的,而绝不是材料堆砌的八股东西。
谈起书话,首先想到《晦庵书话》。那么,不妨先来谈谈这一路的书话写作。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著名杂文家,而他的另一个醒目的身份,则是新文学版本的收藏者。唐弢的新文学版本收藏极为丰富,现代文学馆的藏书,或有半壁为其捐赠,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印制了《唐弢藏书目录》作为纪念。因为这几种特殊的身份叠加,让唐弢在写作书话时,能够游刃有余,谈书作文颇如囊中取宝,而先生又总是平静而克制的,那抒情的气息是淡淡的,令人如闻清香。这才是真正读书人的神采。继承唐弢新文学书话写作衣钵的,是供职于《人民日报》社副刊的编辑家姜德明先生。姜先生对唐弢先生是极为追慕的,除了大量收藏新文学书籍之外,姜先生还善于交游,且还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姜先生的散文写作十分活跃。此外,姜先生早年还专门研究鲁迅,并就此曾写过一部研究鲁迅的书话作品,与唐弢先生的研究,亦有承接之意。无论是唐弢先生,还是姜德明先生,他们的书话写作,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使得他们能够对掌握的材料迅速做出精准判断,从而写出一篇篇隽永有味的短文。我把唐弢和姜先生,看作是藏书家一路的书话家。
或许是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太有名气了,追随者众,但有大成就者少。黄裳曾写过一篇《拟书话》,便是对唐弢的书话体文章的仿写。作为著名藏书家和散文家的黄裳,按说可以就此写出一大批的“书话”作品来的。但我理解,在黄裳的心中,这个“书话”是有特别的含义的,乃是属于唐弢和新文学版本领域,故而他的这篇《拟书话》,所谈也是难得一见的新文学珍本,而他或也有将自己的谈古书文章与此作以区别的。黄裳是著名藏书家,主要收藏明清珍籍善本,他的关于藏书的文章,却少以“书话”来命名。作为藏书家,黄裳最有代表的谈书文集,一本为《书之归去来》,另一本应为《来燕榭书跋》,这两本书都是他人难以写来的。前者写他收藏古籍珍本的经历,有得书的喜悦,又有失书的沉痛,颇有“沉郁顿挫”之味。得书之作,有《西泠访书记》《姑苏访书记》《湖上访书记》等多篇,皆为云霞满纸的好文章。失书之作,则有《书之归去来》等多篇,还有篇谈他购读《药味集》后又意外的失而复得的故事,堪为奇事。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藏书家的记人文章,写过一系列谈坊间书贩的文章,谈人亦谈书,别有一种风味。《来燕榭书跋》是黄裳用文言写“题跋”笔记,读来颇感文情俱胜,亦可当一种书话来看。
藏书家写书话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若是能够有一支妙笔,则能如岩中花树一般,寂寞的藏书生涯也变得灿烂起来。作为藏书家代表的书话家,除了黄裳、唐弢和姜德明,最为著名的,还有收藏古籍的郑振铎、阿英、叶灵凤、周越然等名流前辈,其中以郑振铎的《西谛书话》最为可看。郑振铎在抗战中,与虎狼之辈争夺典籍,乃是真正的“虎口夺食”,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劫中得书记”,这劫难是民族文化的灾难。后来黄裳写他在“文革”中的失书与失而复得的事情,乃是又一种“劫中得书记”,可谓异曲同工也。郑振铎能够写得一手极漂亮的文章,而他又总是不掩饰自己哀乐,得书之幸与失书之痛总是跃然纸上。当代藏书家众,能如郑振铎和黄裳这样写写藏书闲话的,却是寥若晨星。其中可以推举的,则是京城的韦力和谢其章二位,两位都是有名的民间藏书家。韦力先生以中国古籍版本收藏享誉,谢其章先生以收藏现代人文期刊著名,两人也均是著作等身,其中韦力先生的《得书记》《失书记》与谢先生的《搜书记》《搜书后记》,堪为佳品。《得书记》与《失书记》多写拍场上的得失掌故,是颇为好看的。而《搜书记》和《搜书后记》则是一位民间藏书人辛苦辗转于冷摊的记录,其中的喜怒哀乐,读后令人扼腕。
谈以“书话”为名的著作,除了《晦庵书话》,另一本书话名作,应该是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周作人是现代以来读书极为博杂的文人,他的著作如《夜读抄》《书房一角》《秉烛谈》之类,均显示出浓浓的书斋气息,但以“知堂书话”来命名,实为锺叔河先生的手笔。其实,锺先生的这个命名并不准确。周作人作为极有书卷气的文章家,创造了一种特别的“抄书体”写作范式,成为一代文体大家。但周氏的读书随笔,很少写关于书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可以列举的,仅有《东京的书店》《厂甸》《旧书回想记》《我的杂学》《陶集小记》些许篇章。我曾有意搜罗周氏关于买书、藏书、写书的闲谈文字,成一册真正书话著作,并拟名为《苦雨斋书话》。周作人的这种读书文章,我称为文章家的读书记,追随这种特别的写作的,最为称道的有北京的谷林、苏州的王稼句和定居纽约的张宗子,前者的代表作为《书边杂写》,后者的代表作为《看书琐记》,张宗子的代表作则是《书时光》。当今关于读书随笔的文章可谓满坑满谷,难以列举,虽然不能列在狭义的书话行列,但我以为这样的文章也是很难写好的,如要写得隽永有味,更是难上加难。
锺叔河先生编选《知堂书话》,已成为当代读书随笔的经典文本。而锺先生作为编辑家,除了大半生为周作人编选文集之外,还曾主持“走向世界丛书”,更是影响巨大。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生为书操劳的编辑家,锺先生并未出版过一册以“书话”为名的集子。后来偶读锺先生的书信集,得知先生早年曾有过一册《念楼话书》,而未得出版。我有幸得锺先生允诺,重操此事,并终成一册。《念楼话书》是一册关于书的书,更是一册编辑家的书话书。在此书的出版选题中,我曾这样写道:“本书为著名出版人锺叔河先生的随笔,分为四个部分,一为‘书人书事’,二为‘“走向世界”及其他’,三为‘周作人的书’,四为‘读书一束’,分别选录锺先生的书话、读书笔记和序跋文字的代表作,展现锺叔河先生在寻书、读书、编书、写书等方面的成就和追求,将生平经历与编书生涯编织在一起,是其人生和创作精髓的全景展现。”此外,我还为此书写有推荐语,称此书为“一位著名出版家专门谈书忆旧的精选文集,一本向《知堂书话》致敬的书话著作,一个可以快速而全面了解一位著名出版家人生历程的窗口,一册可以反复咀嚼耐人寻味的散文选本”。
诸如锺叔河先生这样的编辑家书话,坊间也有不少,但如锺先生这样成绩显赫、经历坎坷而又百折不挠者,则是寥寥无几。在《念楼话书》的编后记中,我有这样的感慨:“锺叔河先生一生经历坎坷,所幸与书为伴,成果多玉汝于困苦之中。”锺叔河先生获得自由以后,立即投身到编辑出版事业之中,而他的幸运在于,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而得以大显身手。而锺先生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以及其他诸多好书,有开风气之举,对于推动时代的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新时期文化的复兴与繁荣,与锺叔河这样一大批的出版人和编辑家有着重要的关联,他们所写的书人书事也是最为值得关注的。其中,南有锺叔河,北有三联书店的范用,但范先生似乎并不善写书话文章。我最为关注的,则是一册由范先生编选的《爱看书的广告》,体例特别;后继者沈昌文先生,出版过一册《阁楼人语》,是主编《读书》杂志的絮语闲话,也算是一本特别的书话。作为编辑的扬之水在三联《读书》杂志供职十年,写过诸多的读书随笔,如果要算书话的话,她的日记《〈读书〉十年》也是特别,其中买书、读书和编刊的闲话掌故,俯拾皆是。
无论是藏书家的书话,还是编辑家的书话,我都将之称为“文人书话”,因为他们兴趣广博,性情可爱,文笔雅致。他们的书话文章,我均称为文章家的书话。与之相对应的,我想应是学者书话,而这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学者因买书、读书和写书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就其研究领域而闲闲写来,其中不经意间又谈及诸多关于学问的点滴心得,涉及学林掌故,又读来令人痛快,这是文人书话所不具备的特点。这样的书话著作,也是极多的,我所留意且欣赏的,则是北大的辛德勇先生和浙江大学的应奇先生,前者研究古籍版本和历史,后者研究政治哲学,都是尽精微而致广大。辛德勇先生谈书的书,颇为繁杂,但若以书话来论,首推他的一册《蒐书记》,其中最为有趣的,又要算上《东洋书肆记》《大东购书漫记》和《东京书市买书记》等篇章,写其在日本访书的经历,有事实,有掌故,有见识,更有其犀利洒脱的性情,是十分难得的书话佳作。关注应奇先生,乃是读他的一册《北美访书记》,后来又陆续搜集多种,直到最新出版的《读人话旧录》,虽然所谈都是我并不熟悉的政治哲学类书籍,但他对书的痴爱,买书的热情,乃是心有戚戚焉。
关于书话的书,并非我的这篇短文所能阐述一二的。诸如对于英美书籍的访求和收藏,除了上面谈到的那册《北美访书记》,关于访求域外典籍的书话佳品,我还知道有董桥先生的《绝色》、王强先生的《书蠹牛津消夏记》、潘小松先生的《书国漫游》、马海甸先生的《我的西书架》、刘柠先生的《东京文艺散策》等,都是令我大开眼界的。可惜我对域外书籍少有研究,读他们的书,就只能叹为观止了。对于这些书,我无法领略其中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更多的只是感受他们笔下的“一点抒情的气息”。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供职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一直认为能在图书馆工作,真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但我想说,能有这样的话语者,大都不是真正的图书管理员,而多是一个图书馆的漫游者。故而我能读到写得很好的图书馆员所写的书话,只有一册沈津先生的《书丛老蠹鱼》。沈津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室工作多年,又曾受教于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他对书的喜爱与见识,以及他在海外的见闻与掌故,写来都是有趣亦有料的。
如此这般的一番粗略地梳理,再来回看我写就的几本谈书的书,虽然有一册也曾冠名“书话”,但实际来看并非藏书家的书话,也并非编辑家的书话,更非有所专攻的学者书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爱书人的读书文字罢了。其中的大多文字,都是我写的读书随笔、书人闲话和访书笔记,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文章写得轻松和耐读一些。而我所谈的书,也都是一些寻常的书籍,并非难得一见,故而也没有离奇的访书经历,更没有稀见的资料掌故,在我更为重要的是一种书缘与人缘的“抒情”。周作人的文章《结缘豆》,其中有这样的读书人语:“……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怅怅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周作人的散文作为范本,更把这些嘉言作为勉励,我也愿以此与同好者结缘。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北京
航满君作文、出书、编书,“他只是结点缘罢了”,不曾幻想,更不至妄想,文艺还会有什么更大更多的效力。这也就是我欣赏他的缘故吧。
——锺叔河
读航满的文章,像深夜里突然听到笛声飘来,在它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那个幽玄而清新的旋律,倒是可以驱走我们独处时的寂寞的。
——孙郁
我觉得航满的文章好,首先一个原因,便是他写读书记事两类文章,都能得心应手。他是读书人,也是爱书人,博览兼博识,陶养出他文章的趣味。
——张宗子
朱航满笔下的文字,如静水深流,与时风之急躁习气互相隔膜,这是真正素心的好文字。
——林伟光
《一枕书梦》内容都是围绕一个“书”字:买书、赠书、读书、品书;写书、编书、出书;书人、书事、书趣、书史。作者以古朴的风格、细腻的笔调写出一个个与书本有关的故事,叙述中涉及众多文化名人、文坛轶事,描绘了许多名胜古迹,掌故、趣闻信手拈来,美食美景交相辉映,穿插戏曲书画,更增添文坛雅趣。全书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充溢着古雅闲适情调,给读者以通达悠然的精神享受。
鲁迅故居买书记
鲁迅的北京故居与我工作的单位,只有很近的距离,但去得却很少。有天儿子提及想去参观,便发了信息,问黄乔生馆长,回复说,可以预约参观,馆里还有两家书店,亦开放。儿子读了鲁迅的文章,想参观他的北京故居,我则考虑去故居的两家书店看书。那天带儿子转了一圈,很快便出来了。鲁迅故居的对面是一排老房子,叫作“朝花夕室”。我记得这个地方,过去是鲁博书屋,之前曾来过两次,这次来,感觉故居与这个房子之间的距离,很是逼仄。问了一个保安,说鲁博书屋搬到博物馆的展览厅出口处了。于是带着儿子去看鲁迅的生平展。从展厅出来后,出口处果然有很小的一个玻璃屋子,门口有个木头匾牌,上面有“北京鲁博书屋”几个书法刻字,放在一个玻璃柜子上。玻璃柜子里,摆放着一些纪念品和文化创意产品。进了这个小屋子,有位女店员,问她,书店什么时候搬过来的,说是三年多了。环顾了书架,有不少感兴趣的书,鲁迅的一些旧版本的著作,鲁迅的研究著作,以及鲁迅同代人的相关著作。除了鲁迅的一些老版本的旧书以外,大多数新书都是知道的,且也常见,只是这么摆放在一起,倒有一种特别的气息。
在鲁博书屋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现代文学馆编的《唐弢藏书目录》,系内部印刷的非卖品,标价一百八十元。唐弢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也是新文学史料的收藏家,还是散文家,他的这册藏书目录,对于研究现代文学很有价值。唐弢将生前藏书捐献现代文学馆,可谓功莫大焉。现代以来很多名家,在离世前都将藏书捐献各种文化机构,但有些也是将藏书散掉了。其实捐或不捐,都是自己以及其后人的自由,如果是有心人,在这些藏书散失之际,编选一个藏书目录,是很有益的。读这些藏书的目录,就仿佛是到这些名家的书房进行一次巡游。故而我读这册《唐弢藏书目录》,尽管只是简单的书目及版本信息,却能读得津津有味。这位女店员看我对书屋的书很感兴趣,主动与我加了微信,说书屋的新书,她都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我说记得之前,还有位店员,她说是萧老师啊,过去是萧老师和她一起负责,现在则由她一个人经营了。我这才知道那位店员,原来就是萧振鸣先生。记得萧先生有本新书刚刚出版,她说是有一册新书,但卖完了。似乎又记起来,从一个角落里,拿出来一册,还是毛边和签名本,我立即要求买了下来。
萧先生的这册新书《走近鲁迅》,由三百多个关于鲁迅的小故事组合而成,这些故事,或者来源于鲁迅的著作,或者来源于鲁迅同代人的记忆,多是有趣和生动的。虽是小故事,却很见出写作者对于史料的熟悉。有些小故事,过去未曾体味,经萧先生一写,反倒注意了。似乎由此也对萧先生有了一种特别的亲近之感。与萧先生并不熟悉,却有着特别的缘分。十七八年前,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抽暇到鲁迅博物馆拜访孙郁馆长,不遇,便到故居对面的鲁博书屋看书。印象很深的是,那天在书屋买了一套一九九五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趣文丛”第一辑。买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买谷林的那册《书边杂写》。早就听说过这本读书文集,但一直未曾见过,竟在这里遇见了。书屋就我一个读者,店员见我对书有热情,便与我闲聊了起来。得知我是关中人,他说陕西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镇。又见我对谷林的书感兴趣,便推荐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周作人自编文集》。这套书其实当时已超过我的支付能力了,但最终还是下决心购下了。这次来书店,我才知道,原来那位当时与我闲聊的店员,其实就是萧先生。可惜,这次来鲁博,萧先生已退休了。
从鲁博书屋出来,很快就发现了不远处的鲁迅书店。一家博物馆,有两家书店,这是很少见到的事情。其实,对于鲁迅书店,我亦知道很久了。这原本是朋友李建新和张胜在北京操持的“星汉文章”出版公司的一个书店,可惜“星汉文章”最终悄然落幕。这家特别的书店,也转让给一家文化公司了。虽然书店易手,但书店还是有设计家张胜的风格,简洁,雅致,甚至不乏时尚气息。从鲁博的院子步入鲁迅书店,起先看到一排文化创意产品,有鲁迅的微型雕像,以及印有鲁迅头像的布袋子,其中有几本民国时期的《呐喊》《彷徨》和《新青年》,当即想,是不是这家书店还出售民国旧书或者民国版的影印本,于是立即小心拿了起来,结果大失所望,只不过是个仅有书皮的笔记本罢了。在书店转了转,这里也有很浓的鲁迅气息,有一个书架,都是历年的《鲁迅研究月刊》的合订本,但最多只是一种装饰作用,很难会有读者。有几个书架,是“鲁迅专架”,有《鲁迅全集》的数个版本,其中的两个版本,已是绝版了;还有一些近年来鲁迅研究的专著,有本黄乔生馆长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氏三兄弟》,装帧很漂亮,是张胜设计的作品。
鲁迅书店还有不少“星汉文章”的作品,其中书店入口处的展台上,便有一册“星汉文章”为孙郁先生出版的《鲁迅书影录》。这本小书,承建新相赠,后来又请孙郁先生题写了跋记,作为留念。但实在没想到,“星汉文章”最终没能坚持下来。星汉出版的一些著作,却是很有价值的。这次在鲁迅书店,见到星汉出版的“孙犁集”六种、“莎士比亚悲剧”四种、《鲁迅先生写真集》等,都是装帧别致,也十分漂亮的;还有建新之前在河南文艺编辑的“汪曾祺集”十种,是建新和张胜合作的前奏,堪为当下文学作品出版的典范。“星汉文章”出版的这些书,因为种种原因,很难见到和买到。这次我在书店就看到了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史料学》,这是一册很小众的学术著作,但却在“星汉文章”出版了。其实,当下研读现代文学,或者买新文学书籍,乃至写新文学书话,朱先生的这册书都是十分值得一读的。我们有时对于自己看到的事情,难免一惊一乍,其实便是眼界不够开阔,乃至对于一些基本知识体系掌握不够所造成的。“星汉文章”的书,建新多赠我。这次在鲁迅书店,买了这册《新文学史料学》,以作纪念。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修订
我与布衣书局
黄裳曾有写贩书人的计划,并陆续写过几篇,诸如《老板》《记郭石麒》《记徐绍樵》等。但这个系列没有继续下去,或许相对藏书家来说,贩书人的文章比较难写,但亦有其价值。在《记郭石麒》的文章中,他写道:“在上海买书十年,相熟的书店不少,其中颇有几位各有特点的书友,事后追忆,颇有记述的价值,不但是书林掌故,他们的工作,对保存文化的贡献,也是难以忘记的。”又在《记徐绍樵》中,写道:“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多年来典籍流散都离不开这些中间人。”我读黄裳的这几篇文章,认为都是文情俱胜的佳作,但不如他写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文章有影响。我虽然不像黄裳那样常跑古旧书店,但在京城买书也快二十年了,去过很多的书店,也认识几位书店的老板,但最相熟的,可能还要算是布衣书局的老板胡同。关于胡同和布衣书局的介绍,实际上是不少的,他还曾被拍摄成纪录片,在世界读书日期间播放。他似乎永远都是平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身材微胖,笑容可掬,有些民国范儿,但更像个乐天派。
十八九年前,我刚到北京读书,恰逢布衣书局初创。记得是在报摊买了一本《读书》杂志,那期杂志的一页补白上,登了布衣书局的广告,是王世襄先生题写的店名,但并没有地址,只有一个简单的书店网址。我在这个网址上注册了会员,并经常去浏览那个书店网店上的书,也常常去书店的“布衣书话”论坛看看。相比当时天涯网活跃的“闲闲书话”,“布衣书话”谈的多是旧书,更像一个小小的书友雅集。我那时读书,颇寒酸,很少去布衣买书,但却喜欢看他们卖出的旧书。或许胡同是学美术出身的,他经营的网站和论坛,以及售卖的旧书,都有一种特别清幽的气息。那时他也坚持写“贩书日记”,并将这些日记内容贴在网上,我很爱读,便在报纸上写了一则介绍短文,其中有这样的评价:“读胡同的这些贩书日记,一是对淘旧书很长见识,其中隐藏着关乎文化、版本、人文、收藏等多种知识,又有京城文人和书友交际的情趣,侧面则是一家书店的成长史。而此可见贩书者也并非等闲之辈,长期浸润,日积月累,读书也非泛泛了。”
后来认识了胡同,我曾表示想到书店去看看,他回复说布衣没有实体店,主要还是在网上卖书。这算是婉拒了我的请求。我倒是有次因为要去为自己的一本小书签名,特意去了他的工作室,那里的书架堆满了书,实际上是个库房,外人很难拣选。布衣出售的书,都是文史方面的著述,大体包括三类,一种是近几十年来的旧书,另一种是民国以前的古书,还有一种则是出版社出版的一些特装书,包括一些名家的签名书、毛边书和精装书之类。我有三本小书,都做了毛边本,也在他那里出售。其实在我看来,能在布衣卖书,本身就是一种荣幸,说明能被这个特别的读书群体所接受。记得《雨窗书话》出来的时候,我请出版社做了一些毛边本,但他们做的,与普通的毛边本完全不一样,不是那种毛茸茸的书页,而是将书边打毛,有一种很特别的书卷气息。记得布衣在做推介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毛边书或光边书,而是采用打毛工艺制作,毛状书口。此种书口打毛工艺曾被用于二〇一九年‘世界最美的书’《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与此书古朴雅致柔软的书卷气息十分契合,是设计师的一种创作作品。”
我在布衣书局买的最多的是新书,其实有时倒不是特意追逐布衣的特装本,而是他们选的一些文史书,有些虽小众,但品位很是不俗。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介绍的新书,大多先于其他平台,可以先睹为快。那种作者签名和盖印的附加行为,以及极为细心的包装,则带来了一种特别庄重的仪式感。但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一些旧书,古书我则是买不起的,也很少去关注。我在布衣买到的几本旧书,印象较深的有两本。一本是周作人的文集《自己的园地》,系香港实用书局一九七二年翻印,采用的底版是一九二九年上海北新书局的重印版,品相很不错,价格倒是不贵;另一本则是上海学人鲲西的《清华园感旧录》,当时我刚刚读完鲲西的《三月书窗》,对这位少人关注的读书人很感兴趣,恰好布衣有一册鲲西签赠给“七月派”诗人罗飞的。待这册《清华园感旧录》寄来,令我有些吃惊的是,此册旧书不仅有签名,还有鲲西的一段题跋,并有剪报十余张,书页间还有诸多标记,如此等等,可谓很好的研究资料。我后来据此写了一篇《鲲西签赠本索迹》,勾勒了这册旧书背后的故事。这是在布衣买书的一个意外收获。
我和布衣书局的交往,还有几件小事,但亦可见布衣和胡同的特别之处。一件是黄裳先生去世后,胡同策划一个民间的纪念征文,并拟印制成册。当时亦写了篇小文章,后来没有收入此集,我也没问原因,但还是收到了两册精装的《黄裳纪念文集》。布衣出过两册纪念文集,一册是《纪念王世襄先生专号》,另一册是《黄裳纪念集》,前者应系感念王世襄先生对布衣书局的支持,而后者则有一家旧书店对一代藏书大家的深情怀念。另一件,应是胡同与《藏书报》有过的短暂合作,由他组稿一个书话版,一时书林名家济济,我亦凑趣投稿。一位旧书店的老板约稿谈书,这是很少见的风雅事情,我有幸参与,倍感有趣。还有一件小事,乃是偶然在布衣看到出售作家协会流出的一批会员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旧物,其中有几位熟悉的老作家。我当即决定买下来,送还给这些前辈。其中的一张,是我的老师陆文虎先生的,已经被一位书友买下了。我当即与胡同联系,希望他能帮我协调转让。经过胡同的沟通,这位书友恰巧读过我的小书,亦同意将会员证转给我。这不能不让我感慨,胡同和布衣的书友,多是谦谦君子也。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日,中秋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