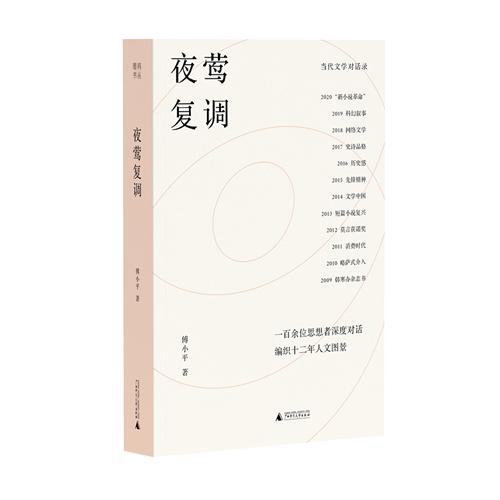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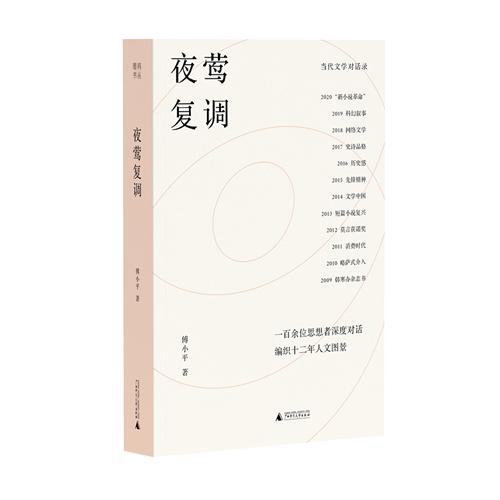
本书记录了2007—2017年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红楼梦》热、先锋文学、韩寒现象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事件,通过口述历史般的采访与文学对谈,就史诗性、神话传统、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科幻文学、都市文学等文学母题与思潮进行了富有样本意义的专题探讨。采访者傅小平进入一个个文学现场,与白先勇、梁鸿、孙甘露、徐则臣、于坚、杨庆祥、张清华、苏炜、邓晓芒等作家、评论家、文化学者对话,形成不同看法的交锋、不同声部的和声,在思想的交织碰撞中探寻当代文学的意义,集结成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与文学史价值的文学对谈录。
傅小平,1978年生,祖籍浙江磐安,现居上海。上海《文学报》资深记者,首席评论员,专栏作家。著作《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获上海市作协年度作品奖。
目 录
一 2020年 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 / 1
二 2020年 新世纪文学 20年:观察与思考 / 59
三 2019年 创意写作:积聚力量,让写作者“破壳而出”,持续奔跑? / 93
四 2019年 科幻小说: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性语言 / 107
五 2019年 我们的文学,依然和乡村有着深不可测的本源的联系 / 121
六 2018年 网络文学: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契机 / 137
七 2017年 在我们的时代里,如何写出史诗性作品? / 155
八 2017年 《红楼梦》:神话叙事和文学传统 / 207
九 2016年 当下写作何以缺失了历史感? / 281
十 2015年 三十年,有多少“先锋”可以再来 / 315
十一 2015年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 / 345
十二 2015年 作家写史与现实观照 / 385
十三 2015年 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 / 417
十四 2014年 今天,如何重塑“文学中国”? / 433
十五 2013年 门罗获奖:短篇小说自此复兴? / 477
十六 2012年 “莫言热”背后,如何确立当代文学价值? / 517
十七 2011年 消费时代与文学反思 / 533
十八 2010年 诺奖、写作与政治 / 569
十九 2009年 重估当代文学 / 597
二十 2009年 文学写作:无关圈里圈外,生活才是根本 / 635
二十一 2009年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打开城市书写新空间? / 657
二十二 2009年 80后办杂志书:叛逆姿态被消费,韩寒的时代来了? / 679
后 记 / 700
自 序
一
出一本汇集22个话题的集子,是我先前没有想到的。话题常是应时而作,为报刊而设。而出集子,把这些在各自话语情境里东游西荡的板块,结集成一幅有“完整”感的文学地图,则近乎奢侈。
再说,这年头颇受欢迎的是那些读来轻松有趣的文字。这一篇篇对话(含 6篇综述),却仿若一次次思想的历险,记录的既不是东拉西扯的闲谈,也不是遍布八卦的趣谈,而是自以为多少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的会谈。虽有让人放松之时,但更多是引人进入思索情境的紧张,即便有时说得一派天真,却看着“一本正经”,就算不惹人讨厌,也是不怎么讨喜的。何况,话题当时看着应景,世易时移也就“速朽”了。如今信息爆炸,眼前的事都顾不过来,谁还会惦念那过了时的旧景呢?
然而此时,我却欣慰于这些板块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欣慰于它们各自归位后传递出来的那份气象与庄严,也欣慰于从中感受到唯有一本集子而非单独的一个篇章所能承载的分量和重量。而这般的欣慰,也是源于这一两年里,我的想法有了某些变化。毕竟我做这些话题,本不是为了应景,所谈也多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亦如诗人于坚所说,作家这个角色永远必须面对的“老生常谈”。说“老”也罢,道“常”也罢,却也可能因不合时宜的“老”与“常”,倒像是我们看一幅历经时光磨洗的画,看一遍后仍觉很可玩味,想回去再看个究竟。
再则, 2009年至2020年间发生了很多文学事件,一树一树看过去,犹如繁花绽放,让人眼花缭乱,却可曾结成多少“思想”的果实?如此,即便是微弱的思想的火光,亦当敝帚自珍。譬如带着“微暗的火”的萤火虫,在夏日的山间一闪一闪地飞舞,不也颇有可观之处?这样想来,有这么一本“文学对话录”聊以备考,无论是于写作者,还是于读者,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吧。
二
我着实被意义难住了。因为自觉有意义,我做了一些话题。也因为觉得没意义,舍弃了一些话题。还因为太执着于意义,也常是提醒自己是不是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意义。但意义的大小与有无,难道不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是只要我们睁了眼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吗?
想起几年前做的一次采访。在收录于前一本书《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的那篇对话里,我问阿来,在史诗渐行渐远的小时代里,该怎么理解史诗?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史诗是中国人的一个病。但这是为什么呢?阿来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路径,他会沿着这个路径,把自己的写作慢慢推进。作家缺的不是什么空间,缺的是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就他而言,他不觉得文学有那么多值得大家焦虑的问题,他只知道写一个小说,该怎么把它写好,把它内在的情感深度写出来。
坦率地说,从事媒体行业多年,先后做过很多采访,这是我不用重读原文就能马上回想起来的少数几句话之一。这么说,是因为我记忆力一向不怎么好,听过的话,说过的话,不是说忘就忘了,就是事后“过电影”才能慢慢回想起来。等想起来了,会发现新大陆似的问自己,我听过这话吗?可不是听过嘛,怎么都忘了!但过段时间没准儿又忘了。哪怕是采访的时候谈得特别好,但做完后,让我想具体谈了什么,有些时候怎么也想不起来。也因为这样,偶尔回看这些年的采访,会庆幸自己没那么偷懒,让它们只是像流水一样逝去,而是化作了可以留下来慢慢回看的“纸上的行旅”。
话虽如此,阿来这个回答,却是我不用怎么想,就能从脑海里欢天喜地蹦出来的。我还记得,面对面交流时,就有被一语击中的感觉。可不是嘛,他说得简直太有道理了!史诗是个什么问题呢?它关一字一句的写作什么事?再往远看,关于写作,关于生活,关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我们谈的问题还少吗?谈来谈去,于事无补,除了满足一点说话的欲望,还能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说,我们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要是活着的当下,乃至恒久的将来,都没法解决这些问题,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实在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即使能答上来,也不会说得像米兰·昆德拉那样好。在晚年出的那本薄薄的《庆祝无意义》里,他说:“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他还说,不但要把无意义认出来,还应该学习去爱它。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读懂了他的用意,但我能明白他提出了一个太高的要求。我们承受得起无意义吗?它是那样轻于鸿毛,又是那样重如泰山。当认出无意义时,我们能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给它一个热情的拥抱,勇敢地说出我们的爱吗?或许我们会本能地逃避它,正如逃避虚无。如果无可回避,那何不装傻当它有意义呢?
我是太执着于意义了。意义之有无,可有什么衡量的标准?其实还是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看法。我们可以从实用主义的层面来爱意义,因为这个有意义,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至于玄之又玄的抽象层面的意义,比如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思想,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只是无意义之意义。去他的爱吧。但倘是以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论,在无意义的炼狱里淬炼过的意义,会不会更有意义?如此说来,昆德拉说的庆祝无意义,或许是庆祝无意义之意义。
三
因此之故,即便史诗就像阿来说的“是中国人的一个病”,就算开出个病相报告,于写作亦无什么意义。这本集子的第七章,却还是谈了被“无意义”的史诗。那是不是说,我们明知无意义,也要制造无意义?
细一琢磨,这个意义与无意义还得两说。我自然赞同谈论史诗这个概念是没什么意义的,却不认为谈论这个话题没意义。因为写史诗,恰恰要求作家必须得有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还有那种内在的情感深度。对史诗的追问,恰恰是对写作终究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的追问。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停留于泛泛而问,或不加判断与辨析就对写作者发出责难:
你生活在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里,怎么就写不出史诗?我们确乎很少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史诗诉求里,到底隐含了什么?
但这样的追问又有什么意义?你追问来追问去,能得出什么确定的结论吗?你谈论的这个那个问题,对写作与阅读能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吗?坦率地说,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要得到具体的指导,我们该去读经典作家的传记、自传,还有他们传授写作经验的“写作课”,再不济读读由美国传入的、眼下颇为热门的“创意写作课”,或是由一些高校或部门编写的“写作指导课”。这些书会告诉你,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写作;雨果常常叫仆人把他的衣服偷去,好让他不能外出,只好待在家里继续写作;巴尔扎克在写作时总会大量地喝咖啡,并且不加牛奶和糖。这些书也会告诉你,海明威总是在小说里把形容词删得精光;福楼拜会在房间里大声朗读,聆听写下的文字是否像音乐一样清澈美好;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怀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妓院里写作,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我不否认读读这些是有用的,至少是一种激励,还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不以为知道这些,就能指导我们的写作与阅读。说白了,写作也好,阅读也好,更重要的是自己去体会,去领悟,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你只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式。相比而言,一些看似抽象的思想或观念,却可能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写作与阅读。比如,余华曾谈到自己曾被辛格的哥哥对辛格的一句教导深深吸引: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我也不确定陈忠实的写作,是不是受了“人间喜剧”的影响,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被郑重其事写在了《白鹿原》的扉页上。
如此看来,相比看似神通的写作秘籍,我对谈论“事实与看法”“小说与秘史”等,抱有更多的好感。虽然这样的谈论,最后往往得不出什么结论。虽然明知在眼下讲求实际的时代里,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最后有确定答案,哪怕是欺骗性的答案或结论,而不是那些“在路上”的谈论,但我还是偏好难有什么结论的谈论。我总感觉, 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学问与思想的大异其趣。在我的感觉里,学问偏重“术”,学问家可以端坐于书斋,为着某一个专业领域,依照某种程序,得出安全可靠的结论,并很可能会得到及时的现世的回报。而思想偏重“道”,思想家须走出孤岛,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场域,而对现实的介入与干预,对既定事实的反思与思考,很可能非但得不到什么现实的好处,还会陷自己于危险与不安的境地。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至今依然有值得让人怀念的理由,虽然此后整个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似乎只是印证了参与者的一派天真与一厢情愿。反观如今普遍的世故,天真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思想的本质,固然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但也是为了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可不是吗?王安忆形容汪曾祺说“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博尔赫斯赞赏不容于世而历经沧桑的王尔德,道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天真”。
四
我想起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夜莺与玫瑰》。夜莺为了帮少年达成与女孩约会的愿望,历经重重磨难找到红玫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少年献上红玫瑰,少女却拒绝了他,因为她担心红玫瑰与她的衣服不相配,因为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给她一些珍贵的珠宝。读到这里,猝然心惊:即使是在童话里,想象中的爱情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诱惑。要知道,夜莺寻访了很多地方,才终于找到了那能幻化出红玫瑰的玫瑰树,她等到月亮挂上了天际的时候就赴约,用自己的胸膛顶住花刺整整唱了一夜,花刺越扎越深,刺进了她的心脏。等玫瑰长成的时候,她已经躺在长长的草丛中死去了,心口上还扎着那根刺。夜莺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在于换来少女的拒绝,换来少年被拒绝后的愤怒,随后一下把玫瑰扔到了大街上,“玫瑰落入阴沟里,一辆马车从它身上碾了过去”?或是换来少年遭受挫折之后的清醒?他感叹,爱情是多么愚昧啊!它不及逻辑一半管用,“于是他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拿出满是尘土的大书,读了起来”。又或者,只是换来一个苍凉的美的姿态?要当真如此,王尔德太执着于不可救药的天真了。
而在安徒生唯一一篇以中国为背景写的《夜莺》里,皇帝听说自己的国土内有只能唱出曼妙歌声的夜莺后,派人把她从森林里找来。不久后,日本天皇进献了一只能发出好听的乐声且外表华美绝伦的人造小鸟,一时间获得了更多的赞美。夜莺飞回了她心心念念的那片青翠树林。然而当皇帝命在旦夕时,人造小鸟却因没有人上发条,唱不出一个音符。皇帝就要死了,夜莺却在这时来到了他的窗外,为他唱起了安慰和希望的歌。于是,随着她的歌声,“皇帝孱弱的肢体里,血也开始活跃起来”,等在他身边的死神则“变成一股寒冷的白雾,在窗口消逝了”。纵使如此,夜莺也没接受什么报酬,因为她第一次唱的时候,从皇帝的眼里看到了一滴泪珠,每一滴泪珠都是一颗珠宝,她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多感人的童话故事。但我还是忍不住假设一下,假如有了如今的高科技,人造小鸟的发条会像永动机一样转个不停呢?以安徒生的慈悲,他为何让夜莺唤回一个垂死的老皇帝的生命,却不给卖火柴的小女孩派去一个美好的使者,而是让她在寒冷的清晨,捏着没烧光的火柴,脸上带着微笑,在街头的墙角里死去?
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是阅读和写作带给了我这样的联想。比如,我会想,如果年老的安徒生遇见年轻的王尔德,又恰好他们有兴致坐下来一起谈谈他们笔下的夜莺,将发生怎样有意思的故事?当然,博尔赫斯与济慈是不可能遇见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里,但博尔赫斯以一首《致夜莺》呼应了济慈的《夜莺颂》,而按博尔赫斯的说法,济慈某天晚上在一只隐蔽的夜莺身上看到了那只柏拉图式的夜莺,于是在他的这首诗歌里,他预言了叔本华发表于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一个论点: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群。引申开去,是不是可以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但可以说其实只是一个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书,也可以说其实只是一本书?何尝不是呢?世界上的作家在写着不同的书,其实写的是对同样几个母题,相互联结又各自独立的不同的讲述和阐释。
五
就说夜莺的主题吧,如果把这些在诗歌里、小说里、童话里呼唤过夜莺的经典诗人、作家都请到一起来一场夜莺对谈,该多有意思。即使不能做到这样,那把他们谈论夜莺的篇章汇集到一起,“编织”成一个对话的场景,又当如何?
或许我做的这些对话,就是这样一种“编织”。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甚或是不同国籍的各式人物,因为这样的“编织”走到了一起,“唱”出各自同时进行、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声部。这些声部各自独立,又尽力和谐地融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这不是想象中的复调吗?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与实际上能做到的多少会有距离,但因为这种想象,我们也要感谢音乐的复调,还要感谢巴赫金让这种复
调,作为一种思想的景观,进入了文学的场域。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一文里,听宁肯、陈联营、陈伟、袁劲梅、梁鸿、余泽民六个人的谈论,是不是像在听六重奏?看我们怎么“编织”吧。把灯光调亮了,让音乐响起来,道具自然要有的,报幕、串词也不能少,如此,对话就自如地像河水一样流淌了,但不是流成互不相关的支流,也不是流成同声相应的一条河。所以,我们还得野孩子般撒野,时不时给对话“制造”一点障碍,让它沿着各自的路径,流成合乎对位法的汩汩流淌的河。
此之谓“夜莺复调”。王尔德还写过一篇《谎言的衰落》,名之为观察评论,实是他虚拟的对话。主角是他两个年幼的儿子西里尔和维维安,地点位于英国诺丁汉郡一栋乡间宅邸的藏书室。我不确定他为什么要虚拟一场对话,是难以承受知音难觅的孤独吗?他又为什么虚拟两个孩子,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家呢?难道王尔德相信唯有孩子般的天真,才能承载他那些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思想?
至少,王尔德该是觉得自说自话容纳不了他的想法,穿上一袭对话的衣裳,也让他那些指名道姓的批评,看起来更有说服力。毕竟两个声部交织并进,不像是传道士在说教,倒是多了那么一点复调的意味。我真心有些同情王尔德,他在短暂的生命里没能更多付诸天才的创作,而是把太多精力耗费在与同时代各种成见的论战上,并最终像堂吉诃德被虚妄的风车“摧毁”了。但我依然欣慰于能看到王尔德的自我对话,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倒是确有一些后来者袭用了这种形式,但效果大抵不怎么理想,要么沦为自我炒作的文字游戏,要么给人感觉还是一个人的自说自话。如此倒不能不佩服他精湛的“编织”技艺了。
六
然而,何以为“编织”?这十二年话题,果真能编织成一幅严丝合缝的织锦挂毯?在这一幅挂毯里,我们既能清晰看到事件的起承转合,也能准确触摸意义的经纬脉络。这是徒劳的。巴恩斯在他那半篇随笔里告诫说,历史向来更像是多种媒体的拼贴,涂抹油彩的是粉刷滚筒,而不是驼毛笔。历史如此,何况一篇编年的文学记录?因此之故,我与其为了它的完整费心“编织”,倒不如让更多的问题从留有的裂缝里抽穗发芽,或可期待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给大地投下一片绿荫。
而这样的“编织”,在我固然是工作需要或受邀而做,但投入了如许热情,却不能不承认多半是出于爱文学,并由爱文学爱屋及乌而至爱人。
就像巴恩斯断言的那样,如果有一千个理由怀疑爱,就有一万个理由相信爱。他说,爱还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在推销它,我们最好点明它是民众美德的出发点。你要爱某个人就不能没有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就不能不学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世界。
实际上,这本集子如果说有什么价值,正在于试着从另一个或更多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但并不如巴恩斯宣称的那样“写尽人类历史的可笑与失落”,恰恰相反,是试图透过“可笑与失落”的假面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一点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审视每一年的文学或是文化事件,试着从中淬炼出事实,由事实生发意义。我们所做的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重估,或是经由重估试图有新的发现。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红楼梦》、奥斯维辛、先锋文学等,同时也试图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韩寒创办《独唱团》等当下事件里倾听过往的回响。我们知道,时间之河里遍布历史的倒影,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虽然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事件,但透
过这新的表层,我们看到的却可能只是历史的反复与变奏。
也因此,在这本集子一些章节的标题里,你会看到“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标注,也会看到“文学反思”与“重估”等字眼。而所谓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向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集子更可以说是一个个“为什么”的汇集,同时也是一个个“是什么”的汇集,从“为什么”走向“是什么”,并从“是什么”回返到“为什么”,如此循环往复,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七
或许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所谓复调,也更多只是不同看法的交锋。但我知道,通过对话,我们不是变得更为冲突,而是达成了某些共识。退一步说,对某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是什么”,也能相对确定地说“不是什么”。即以开篇的史诗话题论,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史诗是什么,却可以说史诗未必是长篇巨著,未必只是悲剧,未必得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也未必是宏大叙事。
我欣慰于看到这样的交锋和共识,却也明白话题纵使有一定的意义,也不过是鲁迅所说的一个中间物,它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让话题本身最终成为过去时,但即使话题有一天过时了,其中有价值的思想仍可能是不可磨灭的存在。倘若以冰山做譬喻,话题的存在,既不是给远航的船做温柔的停靠,也不是意图让它们折戟沉沙,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它的矗立,只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你在某一个时刻听见了这种提醒,唯愿如博尔赫斯说的“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
在那首题为《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的诗里,博尔赫斯还写道:在一个永远不会成为黑夜的黄昏里沉醉,你倾听着忒奥克里图斯的夜莺。如是,在不会成为黄昏的思想里沉醉,我倾听来自时间的足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于愿足矣。
傅小平是公共领域一个独一无二的思考者、提问者、对话者,如果还有谁在我们这个时代将这三者集于一身,向如此多的各式人物提出如此多的问题,并如此锐利、敏捷、多角度地与他们对话、讨论,唯有傅小平。他通过自己与别人的对话,展现了我们的世界,见证了这个艰难而伟大的时代。
——宁肯
今天正是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时代,而某些当代文学似乎背道而驰,正在越来越沦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傅小平们的问题非常值得深思,这些问题都是世界文学的老生常谈,是作家这个角色永远必须面对的,如果他们对写作这个古老的活计怀有使命感的话。
——于坚
当代文坛起于微末发于花枝之处必有傅小平的声音。他以多重角色介入文学生产前沿,以不同的笔调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复杂景观。他敏锐而专注,广博而深刻,活跃而沉潜,从问题入手,将思想结晶落定纸上。《夜莺复调》便如此建构了风生水起的文学与思想现场,复调中夜莺在鸣唱。
——王尧
因为时代的急剧变化,以及写作队伍代际更新过于艰难,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开始模糊和犹豫起来。《夜莺复调》这本书提供的是一种答案。它能告诉你这些年中国文学发生了什么。而傅小平本人,就像是《巴黎评论》的采访人,承担着预言和总结的使命。
——阿乙
★《夜莺复调》中白先勇、梁鸿、孙甘露、徐则臣、于坚、杨庆祥、张清华、罗伟章、邓晓芒等百余位大家的对谈是一场场精彩的头脑风暴,不同的作家、批评家从各自不同的视野对当下文学现象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与阐释,具有意义非凡的反思性。
★时代的急剧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开始模糊和犹豫起来。傅小平与众多作家的对谈,在“世界文学”到来的时代,着眼于当下的文学热点进行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对大众读者还是专业读者而言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21世纪小说二十年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言,从更大的范围看,尤其是相比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小说革命”取得的“革命性”成就,当下作家创作无论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还是在语言、叙事、文本上,都显示出强大的惰性。也因此,小说写作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的呼声日渐强烈。
如何改变近些年小说在整体上停滞不前的现状?青年作家写作应当怎样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当下渐显僵化、保守的小说批评又该做出哪些调整?从 50后到 90后,不同代际的作家、评论家围绕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归根到底是在回应:当下小说界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以期推动小说创作走向突破和创新。
“新小说革命”是相对于 1985年前后的小说变化
VS
自 80年代中期开始的小说新现象被视为一次“小说革命”
傅小平:当我在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现场听王尧老师提
到小说要“革命”,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确实有所触动,因此在冲动之下写了篇观察,这篇文章“落地”后也有一定反响。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话题有讨论的必要。说来也简单,如果当下小说让人普遍叫好,那还革什么命呢?在一些专业读者看来,当今大多数小说,即使是其中被普遍叫好的部分,也不能让人满意,不那么让人信服,更少给人以欣喜之感。就我的阅读,眼下很多小说读后,也只是觉得还过得去,但也不过如此。当然我有限的观感和听闻,不足以代表全知判断,而且也或许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我个人的偏见,所以有必要听听大家对当下小说,尤其是 21世纪以来二十年的小说做何判断。
王 尧:我在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的发言比较简单,但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把我的核心概念概括为“新小说革命”。这是我在一段时间内观察和思考小说创作的认识,也是作为批评家自我反省的结果。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受到莫言和阎连科的启发。莫言的新作《晚熟的人》之“晚熟”有种种解释,我觉得“晚熟”的另一层意思是,小说艺术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阎连科这几年的小说在方法上有重大突破。阎连科认为,我们应该在 19、20世纪小说的基础上往前走。我在“小说革命”之前加“新”,是因为我们曾经把 1985年前后小说的变化称为“小说革命”,今天的小说创作是在这个脉络上发展的。
贺绍俊:事实上,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小说新现象以及一路走过来的轨迹,视为一次小说的革命。我们今天正在分享这次革命胜利的成果。我把这次革命胜利的成果形容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大会师”。
傅小平:这个提法有意思,怎么理解?
贺绍俊:从整体上说,当代小说自 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和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潮的双重洗礼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特别是先锋文学潮的持续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虽然最初是以与现实主义对抗的姿态出现,但最终也转化为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于是构成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传统双峰并峙的局面。两种传统对作家的交互影响大大拓宽了当代小说的叙述能力和表现空间。
傅小平:在这一点上,相信大家都有共识。打个比方说,现在即使有作家依然以现实主义的路子在写作,他们走的也不会是经过先锋文学洗礼之前的那个现实主义路子了。以此对照,我们对当下小说不满或许在于,虽然作家们在两种传统交互影响的轨道上进行创作,却难有新的或革命性的突破。作家们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拓宽当然是好的,但从时间的大框架上看,没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就意味着有所倒退。所以有必要问问你,你说的“拓宽”有哪些积极的表现?
贺绍俊:只要读读现在新创作的小说,我们大致上就能感觉到,大部分小说都很难明晰地判断出是以现实主义方法还是以现代主义方法写的。这说明两种传统都在作家身上起作用。这种作用是非常积极的。我曾这样描述这种作用:“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是作家把自己观察到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重新组织成文学的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既与现实世界有关联,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现实主义戴着理性的眼镜看世界,现代主义戴着非理性的眼镜看世界。当作家有了两副眼镜后,能看到世界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层面。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会师,应该为作家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从而创造出更为完美和完整的文学世界。”我相信大会师后的小说巅峰还没有到来,我们不必对当今的小说创作太悲观。
丛治辰:这二十年的小说创作的确不怎么让人振奋。但是要说没有那种出其不意别出心裁厚积薄发的好作品,恐怕也不对。再有,翻一翻旧期刊,其实在那些被认为佳作迭出的时代,大部分文学创作也还是挺让人沮丧的。所以今时今日是不是“特别”不让人振奋,我也很难判断。
王 尧:事实上,我们无法用“好”和“坏”来判断小说的状况,我们总能举出个别的例子来说“好”与“坏”。当我提出“新小说革命”时,不是基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作家的创作,也不是简单否定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我们需要换一种方法思考。我认为近二十年,小说在整体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无论是思想、观念、方法还是语言、叙事、文本,包括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等,都显示了强大的惰性。我并不否认一些作家写出了优秀小说,但这些优秀小说之于作家个人而言是重要的,但在更大的范围看,其意义何在需要思考和判断。
杨庆祥:王尧老师提出“新小说革命”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和理论的谱系性。不过谈论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充满了风险,因为一个批评家可能并不比一个读者知道得更多,他的趣味和判断往往也带有各种的陈规和惯性。即使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批评家判断失误的时候也比其判断正确的时候要多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二十年的创作就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没有好作品,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个人觉得这二十年依然有很优秀的作品,关键看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系里考量。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