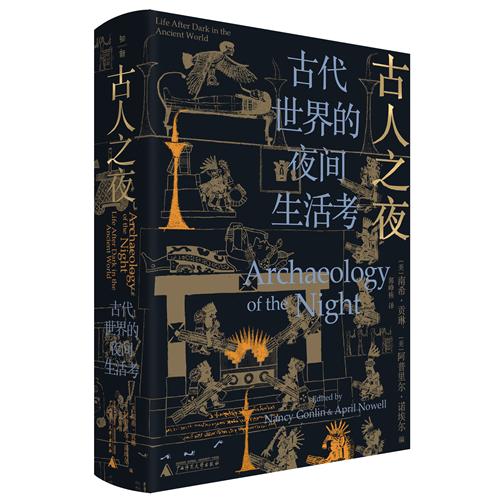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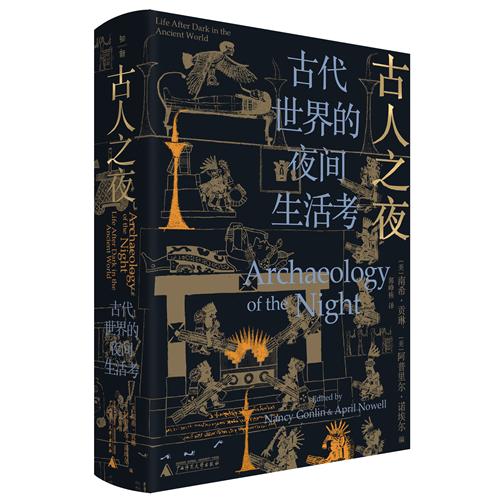
诚如利希滕贝格所言,“我们整个历史仅仅是醒着的人的历史”,甚少有人研究夜晚。然而,古代的夜晚真是漆黑一片吗?古人又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呢?
作为“夜间考古学”领域一部具有实验性质的文集,本书为我们呈现了北美20多位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涉及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古罗马文明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书中阐述了古人的就寝方式,夜间仪式与照明,夜晚的文化意象,星座与建筑、夜间生产活动、神话故事之间的联系等内容,带领我们进入古代世界的“夜之国度”,点亮了一直被学者忽视的那片暗夜。
南希·贡琳(Nancy Gonlin),美国华盛顿贝尔维尤学院人类学高级副教授,曾参与撰写《科潘:古玛雅王国的兴衰》。
阿普里尔·诺埃尔(April Nowell),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人类学教授,考古学家,曾参与撰写《石器与人类认知进化》。
郭峥栋,1984年生,于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致力考古学相关领域的中英文翻译工作,包括《文物》杂志英文版等学术期刊。现居美国纽约长岛。
插图目录
表格目录
前言
序
第一部分:引论
第一章 夜间考古学引论
第二部分:夜景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晚期夜间的声景和情感共鸣
第三章 玛雅古典时期的夜晚: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和萨尔瓦多塞伦遗址
第四章 夜晚是不同的:古代亚利桑那的感官景观和环境赋使
第五章 “油灯很伤心”:科罗拉多—新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夜晚、社区和回忆
第三部分:夜空
第六章 安第斯山脉的夜空和早期城市化:形成时期和蒂瓦纳科时期的的喀喀湖盆地南部的建筑与仪式
第七章 白昼的夜:对比古代和当代玛雅与印度文明对日全食的反应
第八章 在夜海中:古代波利尼西亚与黑暗
第四部分:夜间仪式和意识形态
第九章 夜月仪式:黑暗和烦冗的仪式对智利马普切参与仪式者的影响
第十章 夜晚主宰永恒之处:古代玛雅的暗夜和深邃时间
第十一章 翡翠山遗址、密西西比的女性和月亮
第五部分:点亮暗夜
第十二章 西方的惊人秘密:埃及新王国时期人工照明的转型
第十三章 点燃午夜的灯油:中世纪早期维京油灯的考古学实验
第六部分:夜间活动
第十四章 工程成就和后果:夜间工人和印度文明
第十五章 全罗马都在我卧榻之侧:罗马帝国的夜间生活
第十六章 绿洲中的午夜:阿曼古往今来的农业活动
第十七章 流动的空间和流动的物体: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夜间物质文化,以非洲南部的铁器时代为例
第十八章 夜晚带来的自由:18 世纪和 19 世纪巴哈马种植园中奴隶的隐私和文化创造力
第七部分:总结夜晚
后记:通往更富有想象力的考古学的一扇传送门
作者介绍
本书对我们过往先入为主的研究提出了质疑。除却暴露在日光下清晰可见的事物,作者带领我们探索黑暗,从而拓展了我们与古代世界的感官接触。——《美国考古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以一种既现实又有趣的方式开辟了新的思路……像这样的书又令考古学变得激动人心了。 ——《美国古物》(American Antiquity)
本书是对读者智力上的刺激和启发。毫无疑问,它还将激发进一步的讨论、辩论和研究……——玛丽安·多德,爱尔兰斯莱戈理工学院,《黑暗考古学》一书作者(Marion Dow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ligo, Ireland, and author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rkness)
本书从家庭考古学、平民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古代人类生活情景有了更丰富的诠释。——马克·梅雷尔,北伊利诺伊大学(Mark Mehrer,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本书为关于人类夜间生活的考古论文汇集,属于本书中所称的“夜间考古学”这一主题领域的开创性集中研究。夜晚是人类从古至今存续的一个重要领域,书中收录的各章引导读者探索人类在夜晚的各种复杂的含义、行为和联系,涉及的研究方式多样,主题各异,所观照的文明和地区丰富而广泛。20多位北美考古学家结合自身的专业领域,从“夜晚”这一视角入手,将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考古学功夫相结合,着重从家庭考古学、平民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古人之夜”的新的观点,对古代人类夜间生活情景有了更具兼容性、探索性和开拓性的诠释。
第七章
白昼的夜:
对比古代和当代玛雅与印度文明对日全食的反应
安东尼·F.阿维尼
现代城市文化与夜空的联系于1880年12月21日当天下午5点25分正式断开,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按下了一个开关,将曼哈顿第14街和第26街之间的下百老汇大街上的一长串白炽灯连接到了他附近的直流发电机上(Freideland Israel 2010:179)。因此,他让“不夜街”(Great White Way)灯火辉煌。一瞬间,电灯泡就把黑夜变成了白天。从那以后,发达国家的人几乎从未真正把自己置身于黑暗当中。与我们的祖先不同,我们不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天空。谁还知道今天太阳在何时升起,或是月亮现在的相位?我们用来调整日常活动时间的时钟让我们对昼夜时间段天空中所发生的变化产生了错觉。
尽管我们可以尝试,但我们并不能真正理解古代和现代大多数其他文化中的人民的思想被天文学所吸引的程度。天堂曾经几乎触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发现古代天文学融入了神话、宗教和占星术。人们对太阳和月亮的依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被神化了。这些发光物体的象征物点缀着寺庙,作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它们也成了雕塑和其他艺术品中的主题。人们跟随太阳神活动,格外小心地注意着它的出现和消失。它回到地平线上的某个地方,提醒人们什么时候种庄稼,什么时候河水泛滥,或者什么时候季风时节到来。使用天文历可以有效地标记出节庆等重要的日子。拥有数学知识和记录方法的具有等级组织的文明,例如古代中国和中美洲等,得以完善和扩展他们对天文定位的认识。
关于夜空知识的获取在有关天文学的文献中非常丰富(有关概述和参考书目,请参阅Aveni 2001, 2008, 2017)。本章的目的是强调不同文化的人对昼夜周期性异常中断,也就是日全食的反应。我首先会客观描述日全食期间发生的物理变化,然后列出一些不常发表的日食故事的简要合集,其目的是引起人类学研究领域对该现象做进一步研究。为了在有充足数据的地点进行对比研究,我将主要关注古代和当代玛雅人和印度人对于在白天出现的黑暗的印象及他们的表述。
日全食:另一种夜晚
日全食很少见。在给定的位置大约每400年才发生一次。从技术上讲,虽然总体上需要100%遮盖住太阳,不过日环食发生时,一圈光环会围绕在月盘上,也可以归为日全食一类。当太阳表面有96%或更高的覆盖率,光照度大约等于满月时的天空,就可以产生本章中讨论的大多数效果。当发生这种程度的日食时,除非事先得到警告,否则人们不会意识到夜幕即将降临,直到景观突然变暗,并不是那种如黎明或黄昏一样只在一个方向变暗,而是整个地平线都暗了下来。阴影迅速开始变得明显。太阳在天空中看起来与平时不同,以非常快的速度呈现出残月一般的形状。树木叶子之间的空隙在地面上投射出无数微小的新月形倒影;微风渐起,皮肤变冷。然后,就像远处黑暗中酝酿着风暴一样,月亮的阴影从西面慢慢靠近。人们大多会感受到阈限期(liminality,仪式中的过渡阶段——译者)。随着白天的光照逐渐消失,直到变成一束细小的光带,涟漪般的阴影沿着墙壁和地面迅速袭来:阴影带(shadow bands,阴影带是在日全食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出现在素色表面可以看到的波浪状交替、平行移动的微弱光线——译者)。它们类似于游泳池底部的反射图案。突然间,一道像是镶入发光戒指中的钻石的闪光会突然出现在已变成黑色的太阳边缘(日全食中的钻石环现象——译者),微小的玫瑰色火焰装饰着外圈。然后整个世界突然陷入暗夜。
然而,这种夜间黑暗的本质是无法在普通的认识论和时间框架下进行分类的。在该框架下,现代西方国家的人们将昼夜感官体验作为前提。伴随日全食逐渐褪色的光的品质也对我们的表述带来了挑战。它是由太阳变得微弱的日冕提供光照的,这是一种不同颜色的暮色,被赋予不同的名字,如茶晶色、桃色、金属灰色、绿色、棕红色、黄棕色和硫黄色。星星突然冒出来,行星看上去像是在漆黑圆盘两侧的一条直线上穿着,平行于从太阳日冕向外延伸的微弱的流光。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向不在场的人表达出这样非凡的感官印象已经是非常困难的。我同意乔斯林?霍兰德(Joscelyn Holland 2015)的观点,她探讨了科学客观性与西方日食历史记载中对宗教的敬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基本上是语言方面的问题。
光消失之后,恐惧和迷信在不同程度上侵入了我们。我们被那诡异的黑暗所包围,而黑暗本身早已与我们内心深处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可预见的,这种中断和破坏还是如此令人不安。日食是对每天发生的昼夜交替的嘲弄。然后就是美学的部分——即对某种崇高的事物的感觉。因为日食的黑暗与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过的其他事情毫无可比性,所以一些日食目击者为了选择更恰当的词,用了“死亡”一词来作为比喻。人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正如霍兰德在她写的一篇描述19世纪日全食经历的黑暗的译文(从德语翻译为英语)中所暗示的那样:
这不是如黄昏时的光线消失那样,西方天空的黄色和红色让氛围仍然保持愉悦和充满活力;它更像是一种光的熄灭,无色的灰色逐渐变暗,并且对于观察者而言,这并不会让人联想到平和地进入睡眠的画面,而是自然死亡的画面。(Holland 2015:228,note 32)
然后,仅需几分钟,一切就结束了。时间逆转:钻石环闪烁了出来,阴影般的黑暗消退到东边,星星的光逐渐熄灭,闪烁的新月形太阳重新出现,棕褐色的暮色逐渐变亮,直到变成了一片日光。
每种生命形式都会对这一白天的短暂插曲做出回应。浮游动物——漂浮在海中的微生物或更大的生物——似乎将白昼中断视为纯粹的反射性的现象。生物学家注意到,随着黑暗的来临,层层浮游生物逐渐向海面上升,仿佛在寻找已经消失的资源来食用,直到白昼归来时才回到之前的深度(Kampa 1975;Ferrari 1976)。而昆虫和哺乳动物并不会这样。往蜂巢飞的蜜蜂会在途中变得迷失方向而且会生气,它们会去蜇养蜂人。松鼠疯狂地到处乱窜,奶牛奔向谷仓,而鸡也会随着突然变暗而变得骚动,奔向鸡舍,骚动的程度取决于鸡的种类。狗也有同样的反应(Wheeler et al.1935)。就像浮游动物一样,黑猩猩会随着日光突然减弱而向光源(树木的顶端)移动。据报道,在黑暗开始时,一只黑猩猩直接注视着天空中的黑色圆盘,并向它做动作(Branch and Gust 1986)。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尽管关于各种生物对日食的反应,生物学界已有大量研究,但我们对日食的人类学了解多少呢?可惜的是,不是很多。对日食的探索属于天文学家的领域,他们会到天涯海角,将自己置于月球的阴影中。在那里,他们花时间记录这些珍贵的事件,希望能回答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关于太阳的问题:什么原子成分构成了太阳大气各层?日冕光的来源是什么?该区域的温度是如何升到远远高于下方光球的温度的?对他们来说,观察同样看到了月食各个阶段的人群是无法带来任何信息的。
此处缺失的是人类学家能提出的问题:人类对日食的描述如何能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对来世的信仰,以及他们的社会凝聚力?在他们的物质文化中,他们如何表达自己对日食的见解和感受?他们有能力预言日食吗?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要预言?这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观和历史观?他们讲了什么相关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我们想了解的群体在现场和现象发生后的反应的相关物质记录——人种志和民族历史。我对前人著作的调查显示,关于日食观察的人类学是几乎完全空白的研究领域。
跨文化的日食:制造噪音
当涉及人类对日全食的反应时,人类学家做的并不比动物学家更好。他们可以询问、采访和调查目睹日食的人的后代,不过请注意这里许多报道中提到的信仰已经是受欧洲基督教教义影响过的思想。他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数据之间的连续性和脱节性。例如,他们可能会寻找通过口述传统流传下来的神话中所包含的关于日食的传说,这些传说为作为迷信产物的行为提供了社会背景。可惜的是,关于日食的一般专著中很少提到日全食对人的影响。
在所有已知的对日食的反应中,制造噪音、咬人、进食或吞咽等反应脱颖而出。我们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发出噪音:为了引起注意,为了警告同伴即将来临的危险,或为了吓跑我们在树林里遇到的动物。当代文化中也有噪音制造行为。例如,在1973年日食期间,在南苏丹,人们互相敲击锅具,而且当日食发生时,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祖鲁人(Zulu)拍手和哀号叹息的声音(Alcock 2014:217)。目击者说,人们必须把太阳神从睡梦中唤醒,因为他的不专心预示着巨大的灾难。就像上帝一样,人民变得呆滞:男人们都不和妻子一起睡觉,女人们停止了酿制啤酒,男人们也放弃了狩猎和宰杀,也停止了给母牛挤奶(Alcock 2014:214)。在当代玛雅人的社会中,人们在观看日食的过程中也普遍会制造噪音。他们认为蚂蚁或美洲豹正在吞食太阳,因此需要发出尽可能多的声音——甚至通过掐狗以使其嚎叫。一些玛雅人说,日食和月食是一场古老的宇宙中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延续。这两个发光体正在因为月亮曾经告诉过太阳关于地球上的人的行为的谎言而争吵。日食时人们发出的噪音旨在引起太阳的注意,因为我们需要使太阳相信这些故事是假的(Thompson 1939)。
一些部落文化对日月互动过程中人们发出的噪音做出了性别方面的解释。两个发光体反常的相互作用引出了乱伦的主题。大平原阿拉帕霍人(Great Plains Arapaho)将日食期间日月位置的变化解释为性别角色的转变;换句话说,当两者在日食中结合在一起时,正常的性别关系——即太阳为男性,月亮为女性——被破坏了。关于阿拉帕霍人婚姻的一种神话解释是“每个月的蜜月都会被月经带来的暗月打断”(Knight 1997:133)。实际上,一个女人每月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和与之分开的时间间隔是遵循日月交替的天象的。
奈特指出乱伦与制造噪音之间的跨文化联系,可以在与自然现象——尤其是日食、黑暗和暴风雨——相关的许多仪式中,以及一般的血液流动和不守规矩的行为中被发现。喧闹的反叛、烹饪和乱伦之间的联系出现在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 1970:312;1981:219)关于巴西神话的叙述中,该说法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相比有很多共通之处。一名男子每晚都与妹妹发生性关系,但从未透露自己的身份。妹妹用栀子花类植物(genipa)的汁液弄脏了他的脸,希望能在公开场合找出他。他就去到天空生活,在那里变成了月亮。(注意到月亮脸上的那些斑点了吗?)妹妹跟着他飞向天空;他们吵了一架,她摔回了地面,发出一声巨响。另一个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就向月球射箭。凡人被月球的鲜血溅到了。当他们尝试将血抹掉时,衣服上的羽毛被染成同样的颜色。由于担心落下的血液会污染他们的食物,他们停止了做饭。因此,月食引发了人们对月球血液的想法(Knight1997:137)。
在当代的洛齐人(Lozi)看来,王朝的力量和历史的含义也与宇宙联系在一起。洛齐人是一个由50万人组成的族群,他们生活在赞比亚的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沿岸。根据艺术史学家卡伦?米尔伯恩 (Karen Milbourne 2012)的说法,统治的连续性和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平衡是在观察太阳和月亮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长老们说,起初,他们的太阳神宁贝(Nyambé)与奈丝利利(Nesilele)结合。他们一起从天而降,诞下了第一位国王,国王的后代们是统治该地区人民的天选之人,并守卫着关于天国之谜的秘密知识。每年,以第一个满月为事件标志的季节性河水泛滥后,洛齐人会庆祝朗姆伯卡(Kuomboka)盛会,以承认王朝权力的延续。朗姆伯卡的意思是“从水中走出”;它存在的意义是警告皇室成员和臣民要离开他们的房屋并到高处去。当明亮的月亮在天空中高高升起时,皇家的鼓声发出信号。在仪式上,洛齐国王带领他的人民登上一条黑白条纹的驳船,远离危险。黑色代表乌云,白色代表从乌云上落下的凉爽的雨滴。米尔伯恩认为,黑色和白色也分别代表着通过复兴和祖先来平衡死亡带来的影响;两者都是月球的象征。朗姆伯卡仪式的高潮在下一个新月到来之前(在西面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新月),当驳船到达陆地时到来。在喧闹的鼓声和欢呼的人群中,国王向夕阳示意,旁观者则拍手,拉近着这两个天空神灵之间的联系。同时,国王的随员绕鼓旋转一周,就像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起落一样。
朗姆伯卡仪式似乎旨在表明洛齐国王从其祖先那里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并且他必须准确依照月亮的运行规律不断更新这个合法性。但是,正如米尔伯恩所指出的那样,其实是太阳影响了国王与人民互动的方式。拍手并不是出于恐惧,它更像是掌声。这是洛齐人行为守则的一部分,用于将太阳看作连接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纽带的上天力量。19世纪一份对这种喧闹活动的记录描写到,一群人一起在国王面前鼓掌,说:“在获得他们应得的位置之前,他们双手高举过头,向王室致敬,喊道:‘哟朔,哟朔,哟朔!’”(Milbourne,2012,note 27)然后,当他们继续鼓掌时,庆祝者朝地面鞠躬三下。仪式性的掌声起到了团结天与地,恢复秩序,达到平衡,并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敬意的作用。今天,这样的仪式仍然存在。
跨文化的日食:咬、吃和吞咽
月亮咬太阳是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用来比喻日食的说法。“在您的国家,人们会咬人或者吃人吗?”查姆拉玛雅人(ChamulaMaya)的后裔在一次采访中问人类学家加里?戈森(Gary Gossen1974:29)。他得到的答案显然是:“当然不会。”“这里的人们会咬人或者吃人吗?”加里?戈森反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现在不会,“但古时候的人会”。当戈森继续他的问题时,他开始意识到,就玛雅人而言,陌生人被看作生活在世界的边缘,遥远的、宇宙里的东西也只存在于远古时代。即使查姆拉人声称自己现在已经通过建立杜绝食人和杀婴行为的社会规则而变得文明,但他们仍然认为,这种异常行为可能仍会在宇宙的边缘发生,因此,当地的消息提供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善恶的竞争源头仍停留在太阳和月亮存在的宇宙中,那么日食就提醒人们,社会秩序总是处于失去平衡的危险中。查姆拉人设想中的理想社会,那个没有古代野蛮行为的混乱社会尚未实现。这与基督徒所做的与天体相关的比喻,说在最终审判之时,黑暗将笼罩在罪人身上有何不同?就像现代西方一样,这种突然而至的夜晚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反而为当代玛雅人提供了沉思和讨论自然力量的平台。
预测日食:古时和当代的玛雅人
毫无疑问,当代玛雅人的祖先们试图预测可能发生的日食,因为潜在的力量失衡会对他们产生威胁。在《德累斯顿手抄本》(Dresden Codex)这部幸存下来的15世纪殖民时期之前的文献中,日食表旁边描写征兆的文字讲述了可怕的预言,这些预言让我们在脑海中产生了对占星术的共鸣。玛雅文字上带有一些暗示性的图像,例如吃着象征着太阳图像的有羽毛的蛇,以及在半黑暗的背景上绘制的月亮和太阳的玛雅文字(图7.1)。在上下半页底部排列的数字表示一串重复的177天,随后是148天的间隔。这两组分别是6个月和5个月的时间段,它们是预测日食的关键(Aveni2001:173-184)。另一组以黑色的圆点和横线表示的数字位于这些数字的上方几行。如果把某一列在较低位置的编号加到上一列在较高位置的编号上,则数字为下一列在较高位置的编号。显然,后者是在记录总数。
最近对一座9世纪玛雅城市的发掘提供的证据表明,古典时期的玛雅人与西班牙接触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在预言日食的发生。2011年,考古学家威廉?萨图尔诺(William Saturno)在序顿(Xultun)的第10K-2号房址发掘出了一幅刻在墙上的缩微文本(高2英寸,长17英寸[高约5厘米,长约43厘米——译者])。该文本现在已被严重侵蚀。他和玛雅碑刻学家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uart)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文字。他们在最右边的三列中识别出一种模式,这是全文中唯一可以解读的部分。抄写员精心呈现出大数字4784、4606和4429之间都有177(或178)天的间隔——也就是6个月的月相,或半年的间隔 (Saturnoetal.2012,图7.2)。通过从每个连续的条目中重复减去177(或178),回溯到前几列,斯图尔特发现与尚存数字片段中的残差完全一致。该文本将162个月历月份制成一张表,排列为27列点或条状编号。
图7.1玛雅《德累斯顿手抄本》中的日食参照表:一条有羽毛的蛇(图下部中心位置)咬住了一个半昏暗的太阳(Graz:Akad.Druck-uVerlag)
9世纪玛雅废墟翻新墙壁上的一份刻文,是如何和几个世纪以后的一本预言书联系起来的?首先,两个文本中的黑色数字几乎完全相同;其次,《德累斯顿手抄本》中黑色总数中所记录的时间长度正好是第10K-2号房址墙上刻着的半年期顺序的2.5倍。玛雅数学家对数字情有独钟——越大越好——在小整数倍的比例中,它们彼此产生了共鸣,比如405/162,或5/2的节奏,使这两个文本趋于一致。
图7.2危地马拉序顿遗址第10K-2房址墙上的微缩文字:复原的半年期月历表,可能用于设定日食预警(原图由大卫?斯图尔特绘制,显示为单行文字)
半年期月历表与出现在古典时期的纪念性铭文中的月亮系列直接相关。一开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文本中没有证据与日食预测有任何关系(Aveni et al.2013)。例如,《德累斯顿手抄本》的表中出现的日食预报所需的148天的间隔没有出现在序顿的铭文中。但是,后来对第10K-2房址墙上的一个相邻刻文进行的分析为对此前玛雅创纪元时代出现的日食进行反向计算提供了证据。在此计算过程中,可能使用了半年期表(Bricker et al.2014)。
尽管学者们对记录的是哪组特定的日食(以及它们是月食还是日食)看法并不一致,但大多数人相信,手抄本中的信息证明了《德累斯顿手抄本》日食表与对可能发生的日食做出的预警有关(Aveni2001:173–184;有关尤卡坦历史上可能观测到的日月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Milbrath2016)。将此文字与序顿文本联系在一起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德累斯顿手抄本》表的介绍页面,该页面记录了写下序顿刻文的时间,大致有四个日期,分别是公元755年11月8日、公元755年11月23日、公元755年12月13日,以及公元818年10月8日。这些日期中的第一个日子里有月食发生,然后15天后(第二个日子),有日食发生,随后新月出现。《德累斯顿手抄本》表很可能是较早版本的修订版,或者可能是与当代农民使用的年历相似的一系列表,不断在更新,可以连续使用好几年。序顿半年期月历文字旁边的其他刻文表明,玛雅天文学家当时试图把上一个千年神话时代的日食计算方法运用到之前的玛雅创纪元时代——公元前3114年结束的那个时代(Avenietal.2013;Brickeretal.2014)。
近来对第10K-2号房址生活面的发掘揭示出两名高等级身份的人遗骸上的饰品,与房间壁画上的饰品一致(Rossietal.2015)。墙上的场景描绘了抄写员学校的三名学员。第四个人身着华丽的衣服,似乎正在与皇家人士商量有关庆祝新年仪式的事项。图像附加的玛雅文字把两个高等级人物标识为高级和初级的塔吉(taaj),这个头衔属于具有计算和编写日历表所需知识和技能的礼仪专家。罗西(Rossi)在一具遗骸旁边发现了打树皮器和抹灰器——可以在玛雅图书制作中使用的技术工具。
当代玛雅人使用一些与被冥界的力量撕咬、吃掉或致盲有关的表述方式来描述日食期间发生的现象(有时关于日食的文字中,描写太阳神被蒙住了双眼),动因可能来自日全食附近明亮的行星,尤其是金星 (Milbrath2000)。当不在早晨或傍晚出现时,金星通常被认为是待在冥界中。在日食期间,金星突然闪亮登场,似乎在光天化日之下要明目张胆地攻击太阳。图像旁边的文字提到几天或几年的结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暗示了伴随黑暗来临的时间的结束——长纪历周期的结束,例如玛雅创纪元时代。每一个这样的时代都以太阳的逝去而结束,因此,通常在任何过渡时期都伴随着不稳定性。玛雅人从古到今都相信,他们的复兴仪式有助于战胜黑暗力量(Vail2015)。
为什么古代玛雅人的天文学家如此关注精确性?知识就是力量——解码宇宙中内在节奏的能力将使他们能够探究时间,并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件。这样的信息对于任何统治者来说都是无价的。一个统治者可以追溯到的起源越早,他统治的合法性就越强。有了天国力量加持,统治者的现身将保证一个永存世界在地球和人体神圣的繁衍力量下存在,只要他们按时举行祭祀仪式,向玛雅众神还债。
预测日食、月食也有实用价值。统治序顿的这位不知名的玛雅国王想必花了很多心思寻找最专业的天文观察员、数学家作为宫廷顾问。肩负着皇室任务的抄写员使用序顿墙,就像学生使用教室的黑板或平板电脑来计算最终结果——一个适合手抄本的月食预警表被设计了出来。这张表可以被用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天象——那些代表干旱、战争、联姻同盟等天空中出现的任何可能威胁王朝的天象——的时间。实际上,他们在墙上留下的文字对规划国家未来发展具有开创性作用。
印度的日食
在印度农村的部分地区,日食是调和传统与进步的力量(Chakrabarti 1999)。根据印度教神话,当恶魔罗喉(Rahu)吞下太阳时,日食就会发生。就像玛雅人一样,他们说古时候充满了混乱。恶魔和众神为谁能统治世界而战。在汹涌的海洋中,宇宙保护者毗湿奴神(Lord Vishnu)创造了一罐叫作阿密哩多(Amrit)的永生甘露,供参加者饮用。他化装成一个女人,然后把“魔法饮料”分发给有序落座的双方,从而掩饰了自己的身份。但是毗湿奴通过向恶魔奉上假饮料而欺骗了他们。坐在太阳神和月亮神旁边的一个聪明的恶魔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抓过了一杯真的阿密哩多开始饮。毗湿奴突然显出真身,当场斩首了这个恶魔,让他喝下的永生甘露没法起作用。恶魔的头目名叫罗喉,为了报仇而吞下了太阳。所以每当有机会时,罗喉都会重复他吞下太阳的行为。
一位到印度观看发生在1868年8月18日的日食的英国游客听说了关于罗喉日食的神话,他评论道:“欧洲科学迄今对印度迷信群众的思想产生的影响微不足道。在目睹了8月18日日食的数百万人口中,没什么人真的不相信这是由罗喉吞噬白昼之王而造成的。”然后他补充说:“虔诚的印度教教徒在日食来临之前就拿起了火把,开始搜索自己的房子,并小心地挪走所有煮熟的食物和饮用水。这种食物和水在日食时会引起‘Grahamaseshah’,即不洁,因此不适合食用和饮用。有些人并不在意此传统,他们声称可以通过在食物和水上放置杜巴(dharba)或库萨草(Kusa)来保护它们。”(Chambers1904:191-192)
一个多世纪后,一群印度人类学家进行了一项罕见的研究:研究印度教徒对发生在1995年10月24日西孟加拉邦恒河地区的日食的反应 (Chakrabarti 1999)。他们对电子媒体给诸如罗喉故事等传统信仰带来的影响特别感兴趣。在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城市人口中,人类学家发现特别是妇女,会提到烹饪和饮食方面的禁忌——尤其是吞咽动作。一名家庭主妇告诉采访者她不打算做饭;另一位妇女说,她计划丢掉房屋中的饮用水,并劝阻她的家人在日食时吞咽任何东西。她那位受过良好教育、有外出旅行史的小儿子说,他会服从母亲的意愿,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吞下任何东西会对他造成伤害,而是想避免伤害他母亲的感情,或影响一家人的情绪。
另一位母亲说她打算在日食过后在恒河中沐浴,以消除罗喉残留的任何负面影响。当被问及这些信仰时,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坚持认为,这不是一种迷信,而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违反这种习俗,冒破坏家庭成员福祉的风险。”(Chakrabarti 1999:26)正如我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尽管他们有更独立或世俗的个人见解,但仍可能会拒绝打破我们的家庭文化或宗教传统。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指出,尽管他们完全了解关于日食的科学解释,但他们选择遵循家庭习俗来维持家庭凝聚力。我们很多人在试图应对科学发现的影响时,是不是很矛盾,因为在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中,我们已经与之不再亲密了。
人类学家发现,在印度农村人口中,对日食反应更加基于传统。一个部落的成员讲述了罗喉吞食太阳的故事的简化版本:简单来说,就是月神向太阳神发火,所以吞下了他。另一种说法是,月亮向太阳借了一些米,即古代的标准货币,却无力偿还,太阳出于悔恨而躲在月亮后面:这就是日食的含义(Chakrabarti 1999:42-43)。
借米故事的一个变体是太阳之所以躲在月亮后面,是因为认为月亮又回来借米。在一种从大米债务说法产生的仪式中,人们将一些大米与一枚硬币(现代货币)放在小包中,一起放在房子的茅草屋顶上。日食结束后,人们将大米留作其他神圣的仪式使用。一些印度教徒将其农具和狩猎用具以及一根铁条放在屋顶上,暴露在日食之下。铁条会成为用于制造其他家用物品的材料。如果房子里有新生儿,他们会将一些摆在外面的米放在孩子旁边,然后在夜间将米撒在房子外,以驱赶任何残留的邪恶阴影。一些非部落人士将稻米借贷者解释为较低种姓的人。实际上,他们将日食和食物变质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了纯净和不洁的观念上(Chakrabarti1999:40)。
加拿大因纽特人看到的北部日食
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宗教的生存信念,是跨文化日食观的基础。在加拿大东北因纽特人居住的省,马克?伊詹贾格(MarkIjjangiaq)的日食故事代表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已不再有儿时恐惧。尽管他略带风趣地讲述了故事,但他仍然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一仪式:
我和家人在内陆过暑假时,有一天下午发生了日食。当时我才九岁,确实被这次经历吓坏了。它的效果和一个人戴墨镜时一样。太阳的特征和上弦月或下弦月一样。当时我母亲还健在。我们有一个打水的地方——一条小溪,非常靠近我们的帐篷。日食结束后,母亲让我拿着一个小桶去打水。但我不想去,因为我担心一旦我走到(离帐篷)稍远的地方,可能会有另一次日食,而我是独自一人。(MacDonald1998:136)
因纽特人说,在日食期间,所有动物和鱼类都消失了。为了使其恢复原状,猎人和渔民收集了他们食用的每种生物的样本,并将它们放在一个大麻袋中。他们背着沉重的麻袋,绕着村庄的外围转,沿太阳运行的方向行进。回到城镇中心后,他们将麻袋倒空,分发各种肉的碎片给居民食用。猎人与猎物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因纽特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告诉正在问问题的人类学家,这些生物提醒人们它们需要得到关注,在日食之后恢复狩猎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男人们进行这种仪式,以便动物们可以安全地返回。日食成了人类与野兽接触的媒介。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体验日食
最后,在1960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苏基人(Suki)告诉荷兰人类学家,发生日食的原因是人们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投向了太阳或月亮。如果灵魂无法返回自己的身体,那么灵魂拥有者将会死亡。那些负责日食的人是食火鸟(cassowary,一种大鸟)的成员,是他们自己划分的成对亲属族群之一。该族群与水、雨季、黑暗和月亮有关,而猪的族群则与土地、旱季和晴天有关;后者倾向于负责月食(van Nieuwenhuijsen and van Nieuwenhuijsen-Riedeman 1975:115)。
当一个族群的成员越界到另一族群时,就会违反自然秩序,从而发生日食。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人类学家终于与两位消息提供人交谈,他们多年来目睹了这种事件,并对其感到惊讶。每次日食发生时,一名由负责族群委派的部落民会爬上树,请求天神解释白天的黑暗。有一次,原因是对方部族病人的四个灵魂遮住了太阳。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女人被点名。她在日食后不久就死了。在第三起事件中,部落民爬到树顶,大喊:“Nagaia Namagwaria,Gwauia——这是怎么回事?”预兆回应道:“这里的人是图提(Tutie),我们想把他送回去,但他不听我们的。我们把他的头发剪了,这样他很快就会死去。”(van Nieuwenhuijsen and van Nieuwenhuijsen-Riedeman 1975:116)。当图提得知自己被人指指点点时,他开始哭泣。他们说,他也是在日食后不久死去的。苏基人似乎不惜向外人隐瞒他们的日食传统,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
结论
日食故事中涉及制造噪音、吃、咬、吞的动作,让我们困惑的是神话与认知之间的明显冲突。为什么一个有生命的太阳和月亮要作为重演生命叙事的动作人物?为什么这些心理推测会继续与理性思维并存,在印度教徒对日食的反应中如此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深深地交织在人类拥抱无形自然现象的欲望中,无论是无限宇宙中的黑洞,还是日全食,都试图用我们在有形世界中的经验来理解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有将熟悉的事物投射到陌生的事物上,才有希望找到意义。本章叙述的日食故事是人们将自己的社交投射到自然界的例子,特别是当现状受到侵犯时,例如生计受到威胁、家庭关系被破坏、政治不稳定等。人们创造了关于周围世界的故事,以此将那个不可预知的领域拉近到离自己更近的地方。通过发现反映在宇宙中的社会,它们变得人性化了。
总之,日食本身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对见证者产生的影响,进而做出的行动。对于玛雅人来说,白天的黑暗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的提醒,也是参与维护社会秩序的话语权的需要。印度教太阳观察者让人联想到还债的义务和家庭习俗在科技现代性面前表现的凝聚力,生计面临挑战的环境中,举行仪式以维持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和谐。在现代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太阳和月亮并不是一个独立世界的成员——一个没有精神的物质世界,正如科学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日食的宇宙戏剧中,参与的天体角色提供了一种二元论的意象,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互补的社会概念:男性和女性,纯净与不洁,善与恶,白天与黑夜。来自世界各地关于日食的故事并非仅是有趣的文化遗产,而是让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参与和思考的例子,是建立人与天空之间关于人类生存意义的对话的强大媒介。它们恢复了观察天象这门艺术中已失去的道德成分,并激励我们更加关注人类的多样性。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