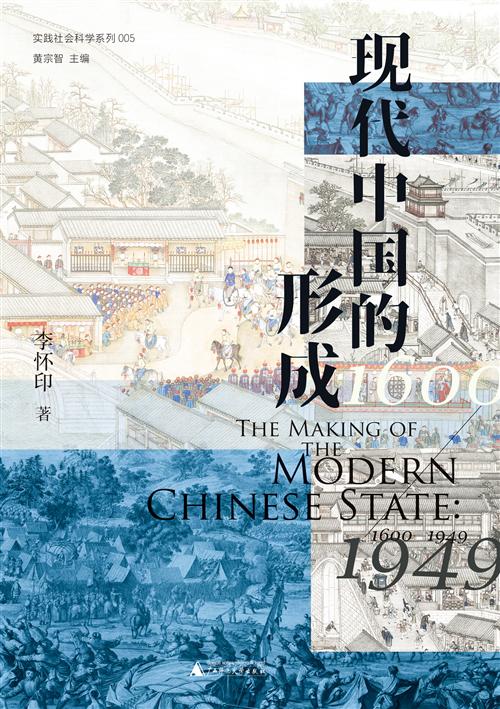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2-02-01
定 价:89.00
作 者:李怀印 著
责 编:原野菁,和永发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社科、历史
开本: 32
字数: 300 (千字)
页数: 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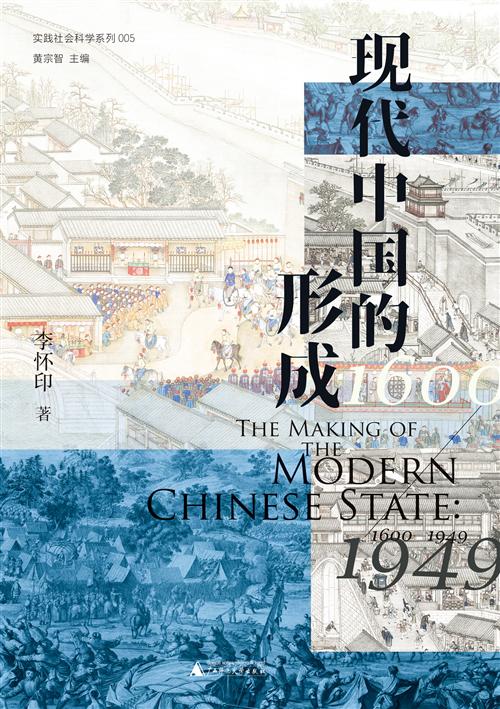
本书为一部关于中国国家建构与转型的历史学研究专著,时间跨度从明清之际到民国,不涉及1949年之后的内容。本书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有选择地聚焦于政治军事、财政构造和文化变迁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探寻明清易代之后国家建构的轨迹。作者试图打破历史研究中惯用的断代分期,并力求突破西方经验的局限。本书认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显示了一个与既往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所形成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认识范式完全不同的路径,其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及逻辑。
李怀印,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学博士,现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代表作《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等。
第一章 导论/1
问题所在/1
地缘、财政、认同:一个分析架构/13
若干关键论题/20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42
边疆的整合/44
治理边疆/55
治理内地各省/62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76
第三章 边疆整合的限度:清朝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88
清代的战争与财政/90
清朝财政的低水平均衡/102
清朝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112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127
财权区域化/130
有条件忠诚之滥觞/145
地方化集中主义/157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160
传统地缘秩序之终结/161
塞防与海防/164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成与败/169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187
财政构造中的高度非均衡机制/189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陷阱/197
缔造新的民族/206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220
军阀竞争中的赢家与输家/223
为何国民党势力胜出?/242
走向国家统一/252
比较分析:从区域到全国的建国路径/259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265
制造新的正统/269
党国之政治认同/279
国民党国家的半集中主义/292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299
共产党革命的地缘政治/304
打造政治认同/310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320
共产党根据地的财政构造/327
一个比较分析/338
第十章 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国家转型/350
疆域的扩张与整合/351
王朝的衰落与调适/358
迈向民主抑或高度集权/364
第十一章 历史地认识现代中国/368
“民族国家”的迷思/369
现代中国之成为“问题”/372
中国为何如此之“大”? /376
中国为何如此之“强”?/379
国家转型的连续性/384
参考文献/389
中文版前言
此书英文稿的写作,始于2012年,我当时刚刚完成另一部英文书稿《重构近代中国》的写作,该书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上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本书的续编,主要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所以,我们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边疆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它在19世纪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20世纪以来不同形态的国家体制,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和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20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通常是在革命或现代化叙事的主导下展开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跟这些叙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也是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长期结构性发展趋势。而历史书写背后的终极关怀,都跟革命/社会主义抑或现代化/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必然性、合法性相关。不过近二三十年来,上述宏大叙事和相关的问题意识已经从中外历史学家的视域中逐渐消退。在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失去了往日魅力之后,人们纷纷埋头从事过去一直被边缘化的课题的研究,诸如妇女、性别、宗族、民间宗教、地方社会及各种边缘群体和边缘现象。这些枝节性的具体课题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宏大历史叙事缺位的情况下,新一代的历史书写也存在“碎片化”问题,人们无法——甚至也不愿意——把这些碎片加以拼凑,以了解它们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下所体现的历史意义。
因此,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不是仅仅从政权性质的角度加以界定,而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把它定义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均有待重构。在前述组成现代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中,除政权外,还必须考虑到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政权本身也必须放在国家形成的宏观历史视野里加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换句话说,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就目前学术界业已提出的跟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可持续性相关的各种议题和认识,做出较为全面的、客观的解读。
基于这样一个意图,我在七年前就开始了本书的构思和断断续续的写作。在方法上,此书采用“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径。所谓宏观历史或大历史,这里有三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它既不同于专门史,也不同于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等专门史,各有自己的一套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彼此之间界限分明,治专门史者也很少“跨界”做研究;而通史又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其分期又受既有的学科体系的约束。本书所采用的大历史路径,则有其独特的综合视角,即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其二,中国的国家转型,是近世以来全球范围的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中国之走向现代国家的轨迹和动力,也必须置于世界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因此,本书始终以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参照,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进展,从而识别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其三,在时间跨度上,本书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樊篱,把近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这个写作计划所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如此之广,要对每一时期、每个具体议题做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已不可能。所幸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军政制度和财政经济的大批档案资料,以及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著述,均已印行;与此同时,中西学术界同行也已经出版了大量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制度和人物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本书各章的写作,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均已一一注明。英文初稿写成后,由下列几位学者译成中文:
宋平明(第一、十、十一章)
林盼(第二、三章)
翟洪峰(第四、五章)
马德坤(第六章)
董丽琼(第七章)
李铁强(第八、九章)
在此谨向各位译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译文经过我的仔细校对,部分内容也有所调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版(Huaiyin Li,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60—1950, Routledge, 2020)。书中观点和史实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李怀印
2020年8月25日于奥斯汀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本书从全球史视野,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中国是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王朝(帝国)基础之上并且成功转型的现代国家,而其转型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艰巨,同样世所仅见。而理解此点,是理解当代中国之关键。本书对于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诸多问题之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之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之反思,皆新见迭出,为近年少见之佳作。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作者致力超越以往的革命和现代化主导叙事,去重新勾勒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次在于作者将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要素形成分析架构,以此解释这个转型过程的发生。这三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近年来多学科学者对包括边疆民族研究在内的区域及跨区域研究、明清财政史研究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研究取得长足推进,故而使诸多微观研究得以升华为本书这样的宏观考量。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探讨“现代中国的形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为一般读者所关注。李怀印教授的这部新著,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碎片化”的细微考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这种全新的解析结构虽然遵循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但呈现四大特色:一是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疆域(领土、边疆)、人口(族群)、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主权展开论述;二是重点选取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关键变项进行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并追究诸类项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影响;三是打破社会形态界限,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国家——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继承、变革、贯通的完整过程;四是将近世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置于世界全史的视域下加以认识和照察。作者所论,非同类著作所可比肩。
——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怀印教授深耕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实际,将宏观历史视野与中观地缘政治、财政及政治认同机制分析完美结合,摒弃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可以既大且强又充满发展的韧性与惯性,为什么可以超越“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本书充满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敏锐而果断地回应了挑激现代中国国家合法性的种种论述。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何以能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政党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在“宏大叙事”早已祛魅、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之今日,李怀印教授大胆揭橥“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大旗,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大要素,对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诠释,讲述了中国由族群国家而疆域国家而主权国家,并最终形成高度集权与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故事,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书视野宽广,内容闳富,体大思精,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李怀印的新著全面阐述了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国家建造过程。作者充分利用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置于财政-军事视角和大历史的架构下,对制约国家形成过程的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因素条分缕析,指出清朝国家独具特色的形成路径对理解现代中国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全书引人入胜,不仅有力论证了地缘格局、财政构成和认同塑造在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在研究路径上与“中国中心论”遥相呼应,立足中国自身的经验,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必须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偏颇和臆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中国的独特路径。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刊》)
在诸多历史学家中间,李怀印的近著代表了一种分析架构上的突破。作者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如何动员财力支撑战争、巩固政权。通过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此书彰显了民国早期自下而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作者对军阀时期国家分裂与统一的财政基础的颇具洞见的分析,则让人相信,有关国家建造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确可应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作者对南京政权和共产党革命的分析则揭示了国家走向统一和集中的不同路径。
——Twentieth 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
李怀印老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是一本既能帮助读者将历史知识升华为历史认识,又能启发思考的好书。这本书有两点非常吸引人:一、作者对许多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的零星的近现代史知识做了整合与重组,经过深入的思考和逻辑分析,从宏观上解释了十七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二、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论述,举例说来:李老师力图证明,不同于传统的屈辱史、失败史叙事,晚清近代化在许多方面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比如它避免了边疆的分离,政权建设也逐步近代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图书的装帧设计与图书内容非常契合。封面主要用了两幅图:《乾隆南巡图》苏州局部,反映东南财税对大一统国家的作用;《乾隆西征图》,反映西北边疆的平定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本版图。同时,正是东南充足的财税为西北用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撑。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东北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东北也因此成为国共内战期间三大战役的首役战场。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共最大和最重要的根据地。东北源源不断的人力、武器等战略物资和后勤支持,是中共赢得了接下来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编者按
为什么东北如此重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的地缘政治环境一度有所改善,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曾获得国民政府的津贴和补给;1939年以后,国共关系渐趋紧张,摩擦加剧,但毕竟没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共产党军队和敌后根据地由此迅速扩张。然而,共产党部队遭受了日本军队的反复扫荡,以及后来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局部攻击。因此,通常情况下,共产党在战场上仍处于守势。对陕北和华北其他地区共产党部队来说,最为不利的条件是,这些地区均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他们很难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支撑快速扩张的部队。正是因为陕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难以招募士兵,才迫使红军于1936年1月发起“东征”,进入山西(逄先知、金冲及2011,1:383)。出于同样原因,红军在1936年5月筹划西征,进入宁夏,以便接收从苏联获得的物资(同上:383,389,402)。后来,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控制的陕甘宁地区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导致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部队无法进入,打击国民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该地区的兵力为共产党的八倍以上(国民党25万人,共产党还不到3万人),一度使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总部陷入险境(同上,2:803)。正因如此,在抗战接近尾声时,随着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共领导人曾试图调整其军队和根据地扩张策略,优先考虑在相对繁荣的南方省份发展;1944年底和1945年初,毛泽东和党中央接连发出指令,要求派遣共产党军队南下,在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新建或扩大根据地(TDGG,15:32—36,145—147,181—187)。
但是,1945年8月发生的几起意外事件——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及其随后在9月2日进入并完全占领中国东北——使共产党战后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极端重要性对中共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东北北邻苏联,西接蒙古,东接朝鲜——这些都是共产党国家或地区且对中共友好;一旦占领东北,中共部队将拥有一个安全而稳定的根据地,而且,它从那里可以采取进攻性战略,对关内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作战。其次,与中共已有的小而分散的根据地不同,东北地域辽阔,面积达约130万平方公里。当时面临两种可能,即既可能让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后随即占领整个东北地区,同时也可以为中共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一旦遭到该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也能够后退,并在规划大规模攻势以最终从该地区驱逐和消灭国民党部队方面,拥有高度的机动性。第三,东北很富裕。该地区广袤而肥沃的土壤带来了农业高产,加上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产生了比其他地区多得多的富余粮食,使东北成为粮食净出口地区。更重要的是,东北有发达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能源生产,占1940年代末全国重工业总产量的90%左右;这里的兵工厂在中国首屈一指。此外,东北还有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铁路里程达到14000公里,约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一半(朱建华1987a:140)。一旦占据东北,这里将成为共产党部队向全国其他地区进攻的坚实后方。
对共产党而言,东北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控制东北,他们只好把作为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的华东地区作为争夺目标,但这样做胜算不大,因为这里驻扎有国民政府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依靠美国的慷慨支持,他们可以轻易地包围并击溃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力量。事实的确如此,国民党仅将约三分之一的部队集中在江苏和山东,便在1947下半年轻松地摧毁了共产党在江苏中部和北部的根据地,并将共产党军队逼退到山东南部,又在1947年5月进一步将其逼至山东中部。如果共产党军队以华北为优先进攻目标,他们将面临国民党从东北和华东的夹击。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先控制东北,利用该地区被苏方占领的优势,“封死”刚刚进入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并彻底消灭他们。只有在完全控制东北后,共产党的部队才能依赖东北充裕的军事和后勤供应,集中兵力在华东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叶剑英1982)。
由于指望从相邻的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从直至1946年4月仍然占领东北的苏联)获得实质性支持,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很快放弃了原定的向南扩张战略,转而在1945年9月制定了新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LSQ,1:371—372)。毛泽东在调整这一战略时曾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考虑,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MWJ,3:410—411,426)七大后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第一个提出“向北发展”的战略。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要我能够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LSQ,1:372)
苏联的支援
尽管苏联有义务遵守其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议,使中共不得不放弃其原有的“独占东北”计划,转而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不过,与苏联占领军的合作仍然是中共在那里立足并成功控制整个东北的关键(TDGG,15:433—436;金冲及2006:14—15)。1945年初,苏联军队欢迎共产党部队到达山海关,并允许他们接管当地政府的权力。后来,苏方允许东北各地的共产党军队自由行动,只要后者不使用中共部队的正式番号;在其进入东北的最初两个月,情形尤为如此(李运昌1988)。苏方慷慨提供的武器使共产党在东北被称为“抗联”的原有部队,能够在一个月内组建一支48500人的“自卫武装”。苏军还向曾克林麾下的共产党部队移交了原日本关东军离沈阳不远的一座军火库,使曾的部队能够从4000人扩大到6万人。10月初,苏方又通知中共东北当局,准备交给后者原关东军在东北的所有军事设备,这些武器足以装备数十万士兵。然而,因为数量过于庞大,最初共产党军队实际上只能接收1万支步枪、3400挺机枪、100门大炮和2000万发子弹。10月下旬,苏军将在东北南部的所有武器和弹药库以及一些重型武器甚至飞机都交给了共产党军队。在1946年4月从东北撤军前,苏军进一步将在东北北部的日本武器移交给共产党军队,其中包括1万多挺机枪和100门大炮。据未经证实的资料统计,共产党从苏军手中接收的日本武器,总计约有70万支步枪、13000挺机枪、4000门炮、600辆坦克、2000辆军车、679个弹药库、800架飞机和一些炮艇(杨奎松1999:262;另有不同估计,见刘统2000)。因此,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力方面,共产党军队均在东北拥有绝对优势。1946年初,为了确保共产党军队在苏军撤离东北后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迅速占领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苏方以各种借口故意拖延撤军,并阻止国民党军队按计划进驻大连,接管城市(杜聿明1985:519—520,536—545)。
东北的实力
东北地区因此成为国共内战期间三大战役的首役(辽沈战役)战场,共产党在此经过七个多星期的战斗,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并在1948年1月初占领了该地区。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东北成为中共最大和最重要的根据地。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以及高产的农业,这一地区很快便成为巨大供应基地,为中共提供人力、武器和后勤支持,使其得以赢得接下来的两大战役,即华东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和华北的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
东北首先是中共在内战期间最重要的兵源地。由于其积极招募且武器供应充足,当地的共产党部队迅速扩大,从1945年底的约20万人增加到一年后的38万人,到1947年底几乎翻番,达到70多万多人(朱建华1987b:602,604),占中共在全国新增兵力的一半;共产党部队在西北、华北、华东和中部省份的兵力,到1947年总共才增加30万人。到1948年8月辽沈战役打响前,中共在东北的兵力进一步增加到103万,远远超过只有约50万人的国民党军(王淼生1997:94)。它们不仅是共产党控制地区力量最大的一支,占整个中共军队的近37%,而且是装备最好的。从1945年到1948年7月,中共招募了120万名来自东北的士兵,占整个共军同期新增士兵的60%以上(朱建华1987a:286)。在辽沈战役获胜后,东北地区派出一支80多万人的部队,加上15万名提供后勤的民工到关内,构成了平津战役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朱建华1987b:69)。
同样重要的是东北的军火生产及其对关内作战所起的支持作用。1945年之前,在与国民党和日本军队打游击战时,共产党部队很少或没有使用重武器;相形之下,中共部队在内战期间的三大战役,采取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形式,每场战役涉及数百万兵力部署,密集使用炮火,消耗大量弹药。苏联移交的原日本关东军武器只能部分满足中共部队在东北战场的需求。因此,共产党军队在进入和占领东北后,利用现有设备和仍在服务的日本技术人员,迅速恢复并扩大武器生产。到1948年夏,已拥有55个不同规模的军工厂,每年生产约1700万颗子弹、150万枚手榴弹、50万枚炮弹和2000门60毫米大炮(黄瑶等1993:436)。1949年,其能力进一步提高到每年生产230万发炮弹,217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火炮,并雇用了43000多名工人(朱建华1987b:70)。东北兵工厂生产的弹药对共产党军队在关内打败国民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东北通过提供大量的后勤物资,为中共在关内的作战做出了贡献。在1948和1949年,东北的农业产量介于每垧(约一公顷)900到1000公斤之间,每年合计生产1200到1300万吨粮食(朱建华1987b:141—143),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年征农业税共计230万至240万吨(1947年税率为21%,1948和1949年为18%)(同上:446)。在1946至1949年整个内战时期,从东北征收的公粮达686万吨;此外,还从农民手中征购了180万吨粮食和7488吨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农产品(DBCJ:210)。中共向苏联大量出口这些产品,以购买苏方的工业、医疗和军事物资。来自农业税和其他渠道的财政收入使得东北共产党政权在1949年可以支出相当于380万吨粮食的军费,其中45%用于关内各省的部队。此外,东北当局为关内提供了超过300万吨的货物,包括80万吨粮食、20万吨钢铁及150万立方的木材(朱建华1987a:384;1987b:71)。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清朝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
在某种程度上,18世纪的清代中国颇类似于同时代欧洲的一些“财政—军事国家”。但与此同时,清朝的地缘政治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遗产,使其政府形态迥异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构建的任何路径。
——编者按
人们公认,战争在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起到关键的驱动作用。在16世纪初,欧洲极度分裂,有近500个大小不等的政治实体,均在不同程度上享有自治权并垄断了境内的强制力量;那里既有大型帝国和主权国家,也有公爵领地(duchies)、王侯领地(principalities)、主教管区(bishoprics)、城邦及其他的更小实体。那些版图较大的邦国君主,多倾向于以间接方式统治所属人口,而那些享有种种特权和自主权的教士、封建主和城市寡头,作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中介,往往自行其是,抵制与自身利益不合的国家要求。国家本身并无自己的常备军。各国的军事组织多杂乱无章,以雇佣兵为主,且掌握在封建主、主教、城市、行会或其他地方社区之手,只是有条件地听命于国家,其态度多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败是否对自己有利。相形之下,到了17世纪晚期,欧洲各地的军事力量多已经成为正规化的常备军,由国家透过职业军官等级体制加以掌控,地方社会群体和机构不再拥有自己的军力。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国家不得不增加各种税收,以扩大其财政基础。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又仰赖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造,亦即国家通过削弱那些代表地方利益的政治、军事势力,把那些零碎的自治城邦和领地整合到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更大区域里,从而达到司法、税收的高度统一(Tilly 1990:38—47)。而所有这些变革背后的终极驱动力量,则是国与国之间持续不断的竞争和交战。正是战争促使君主们竞相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军事机器,为此又不得不提高征税、征兵、动员资源的能力,政府机构因之不断膨胀、分化。查尔斯·蒂利因而有此名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Tilly 1975:42)鉴于财政资源的使用对于强化和垄断各种强制手段如此重要,史家们倾向于把兴起于16至18世纪的那些民族国家称作“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这一术语首先由约翰·勃雷尔用来描绘18世纪的英国(Brewer 1989),继而被史家们纷纷用来指称同一时期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他们在使用此一术语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战争开支的攀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和行政体系的改造,是16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心内容。军事革命在此过程中起到最主要的驱动作用。不仅武器、战术、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军队也变得更加庞大、复杂、常规化。维持军队和发动战争比以往更加昂贵;为此,国家需抽取更多税收及其他资源,也不得不扩大、更新其财政制度乃至整个行政体系,由此导致自身的转型,即从原来依靠领地地租和贡物作为财政收入的所谓领地国家(demesne state)变成了对臣民的财富征税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征税国家(tax state)。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军队也越来越正规化、常规化(Brewer 1989;Glete 2002:10—15;Mann 1986;Rasler and Thompson 1989;Downing 1992)。
在某种程度上,18世纪的清代中国颇类似于同时代欧洲的一些“财政—军事国家”:它有一个集权的行政体系,通过职业化的官僚阶层管理分界明确的疆域;它有一个有效的赋税征收机制,其中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用于军事;政府拥有比任何欧洲国家更庞大的常备军,在占据中原后的一个世纪之中,不时地开疆拓土,巩固边陲。因此,有学者将清朝定义为一个“近代早期”国家,并认为清朝与16世纪以来的欧洲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Rawski 2004;Lieberman 2008)。例如,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对雍正朝财政制度的研究,便把清朝刻画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不断探寻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合理而有效率的官僚统治”(1984:xv),因此18世纪的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颇为相似,双方都面临来自政府体制内外对资源的争夺,并为此都在寻求财政收支的稳定可期。肯特·盖依(Kent Guy 2010)的研究也发现,清代中国通过各省督抚职官的制度化来加强统治者按照己意任命疆吏的特权,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欧洲君主专制的形成遥相呼应。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清朝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所涉及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历史境况进行比较,还是能发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地缘政治关系:垂直型与平行型
所谓地缘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与他国争夺战略优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地缘政治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的目标和优先议程。清代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在这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对比。欧洲各国至中世纪晚期便逐渐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并且主要是跟这一体系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相互交往。对国家的认同,往往是通过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对抗、交谊或中立态度体现出来的。各国之间通过结盟或者对抗展开互动,据此制定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而战争则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Tilly 1990:23,162;Rasler and Thompson 1989:xv—xvi)。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导致欧洲的国家数量从1490年的约200个,降至1890年的约30个;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平均面积,则从9500平方英里上升到63000平方英里(Tilly 1990:42—47)。
地缘政治关系同样在形塑帝制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作用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与欧洲完全相反。欧洲各国共享一套国际秩序,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对等的(即使不是平等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其地缘世界中唯一的主导力量。至少在象征的和思想观念的层面,这里的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垂直型的:大清高高在上,周边由各藩属国环绕,迥异于欧洲列国之间的平等交往或相互竞争。如有邻国挑战清廷的宗主地位或者威胁其地缘安全时,清廷必然会以武力加以回应。这种以中国为中心、周边缺少抗衡势力的国际秩序,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家的内部运作机制。早期近代的欧洲各国统治者,面对持续不断的竞争和战事,纷纷追求扩大和升级军事能力,军事支出因此持续上扬;而在18世纪的清代中国,军事支出以及军队组织和训练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清朝正规军的数量一直保持在80万—85万名士兵,其中包括60万绿营和20万—25万满洲八旗。同时,从1730年代至19世纪中叶,清朝的常规军事支出,也一直固定在约1700万两白银。直至19世纪晚期,清朝对士兵的招募、培养和训练的方法都没有显著变化。由于国内外不存在直接威胁,清朝统治者对现存的军事组织装备心满意足,失去了进一步加以改进的兴趣。与此同时,对武器制造的成本和标准所制定的死板规章,以及长期的物价通胀,也使得武器的更新升级成为一种奢望(茅海建2005:33—88)。从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由于在长期和平环境中缺乏训练,加上军事装备老旧,清朝军队的整体战力江河日下。
事实上,缺乏来自外部的实质性竞争和挑战,不仅导致清朝军事力量衰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家行政和财政体制的整体演进为何趋于停滞。除雍正帝在位期间(1723—1735)曾采取措施,重组了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以此增强了个人权力之外,清朝的官僚系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由于现有的赋税收入足以支付常规开支,而这些常规开支在原则上又长期保持不变,因此,清朝统治者认为并没有必要扩大或更新其财政体制。清朝财政制度的特点,是对直接税的依赖,将田赋视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且赋税征收体系高度集权,田赋税率很低,在征税过程中禁止包税等各种非法活动,因此在19世纪之前并未出现以抗税为肇因的大规模农民暴乱。这些状况,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混乱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当时的每个欧洲国家政府来说,最大的挑战乃是“在战争期间如何调动国家资源,而不至于引发多数民众的强烈不满”(Bonney 1988:1)。例如,由于纳税人口有限,收税权力下移,法国的历代国王为了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不得不依靠下述举措:向金融家借债,用外包方式征收间接税,让贫苦农民承受高昂的直接税(taille)负担。由此出现国王的债务增长,政府腐败现象猖獗,国家财政收入损失巨大,以及农民反叛此起彼伏(Bonney 1981,1988)。
社会经济结构与国家构建:强制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
在国家建构和随后出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不下于前面讨论的地缘政治因素。查尔斯·蒂利和迈克尔·曼均发现,欧洲国家的政府形式与资源获取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例如,那些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商业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在应付战争及其他政府行为时,往往难以增加收入(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的征收),因此只能扩大财政机器,建立专制主义政权,以强制手段“动员”农村地区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那些拥有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资源丰富的地区,相对容易通过征收商业税和地主精英的财产税,获得足够的收入,因此不必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而是朝着宪政政府发展(Tilly 1985:172—182;Mann 1986,I:456,476,479。参见Downing 1992:9;Ertman 1997:13)。蒂利1990年对欧洲国家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模式,以阐明经济如何制约国家活动:在“强制密集型”地区,农业占主导地位,统治者为了发动战争及其他活动,倾向于依赖人头税和土地税,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征税体制,并让地方精英在其中握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在“资本密集型”地区,由于商业经济的发达,国家倾向于依靠更易获取的关税和消费税,并且将信贷作为国家的财源之一,因此导致中央权力受到限制和分割。在这两种理想类型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模式,即“资本化强制模式”(capitalized coercion),国家同时从土地和商业贸易中获取资源,创造了双重国家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精英既要直面金融家的挑战,同时又要寻求合作机遇(Tilly 1990:99)。
上述三种国家形成轨迹,对我们理解清朝国家的发展特征有何关联?显然,无论“资本密集型”路径,还是“资本化强制模式”路径,都不能用来解释18世纪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与英格兰所采取的资本强制化路径相比,这种差异显而易见。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在1700年是英格兰的7.7倍,在1820年是其6.3倍(Maddison 2001:表格B-18),但是,中国的工业和贸易额仅占经济总量的30%,而英格兰的工业和贸易额在1700年和17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分别贡献了45%和55%(Goldstone 1991:206)。据麦迪逊估计,1890年,工业和贸易额占中国GDP总量的31.5%(Maddison 1998),因此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经济结构并没有什么不同。刘瑞中估计,1700年工业和贸易额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30%,1750年占33%,1800年占36%(刘瑞中1987)。而在明代(1368—1644)前期,工业和贸易额仅占经济总量的10%,后期则约占到20%(管汉晖、李稻葵未刊稿)。再对中英两国工业和贸易税额在各自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行比较,这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1700年,工业和贸易税额仅占清政府总收入的17%,到了1800年,也仅占30%(许檀、经君健1990)。而在英格兰,两种税额在1700年和1789年,分别占66%和82%的份额(Goldstone 1991:206)。即使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工业和贸易额在清代经济构成中的次要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法国的经济结构非常类似于中国(1700年,农业占GNP的75%,1789年仍然高达69%),但是,工业和贸易税收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在1700年和1789年依然分别达到54%和50%(Goldstone 1991:204—205)。英格兰与欧洲大陆无疑存在着巨大差异。高度集中的税收制度、对于间接税的日渐倚重、农业直接税的废除,以及由此而来的英格兰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成长的速度。这些因素导致奥布莱恩将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格兰财政制度视为“财政例外主义”(fiscal exceptionalism),并将其与欧洲大陆国家基于僵化的区域配额和盛行的包税制所导致的财政体系上的分权、腐败和无效进行对比(OBrien 2002)。
工商业对政府收入的重要性的大小不同,对于欧洲和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意味深长。在欧洲的资本密集型地区,战争成本的急剧增加,导致统治者越来越依赖资本家(商人、银行家和制造商),通过借贷、征税、采购等方式获得收入,而无须去构建庞大、持久的国家制度。相反,资本家会利用其经济和金融的优势,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以保护和扩大工商业(Tilly 1990:50—151)。在资本化强制模式的国家,战争的巨额支出,国家对于税收、信贷和债务支付日益增长的需求,迫使统治者与各主要阶级讨价还价,在赋予选举权力和使用暴力镇压之间左右权衡,最终导致代议制度(诸如Estates和Cortes)及全国性立法机构的建立和完善(Tilly 1990:188)。
上述状况并不存在于18世纪的中国。尽管在清朝的总收入中,工商税收的份额日益增长(从清初不到13%,增长到1800年的30%),但是,田赋仍是清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周育民2000:238—239)。虽然盐商的捐输,是政府在战争及其他紧急情况下额外支出的重要补充,但清朝统治者仍然认为,既不需要增加工商业税,也不需要为了战争或赈灾,而向商人和金融家举债,只需要依靠国库的现金储备,即可应对大部分额外支出。因此,中国商人并没有任何机会可以与国家讨价还价,以谋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国家也没有采取提高商人地位、鼓励企业扩张的措施,而仅仅是在获得商人的捐输之后,给予他们一个荣誉称号而已。尽管在现实中,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保障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运行,保护商人的生计,但正如雍正帝所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农业为经济之“本”,必须加以培育和保护,而商业和工业都只是“末”,与农业争夺人力和资源,因此必须加以限制(邓亦兵1997;王日根2000)。
同样,中国也不应被当作强制密集型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的强制密集型国家,经济商业化程度低,可从资本家那里抽取的资源有限,因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而不是通过谈判和签订契约,以获得足够的收入,用来支撑战争和国家建设,结果只能通过强化农奴制、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榨取农民(Tilly 1990:140—14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中国,由于纳税人口庞大而军队规模较小,清政府能够将田赋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人口增长尚未消耗掉大量的经济盈余之前,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均能承受此一负担。因此,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必要把耕种者变成农奴甚至奴隶,也不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农村资源。相反,清政府意识到,自耕农构成了纳税人口的主体,他们的生计安全构成了国家财政的基石,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如税收蠲免、鼓励垦荒、限制地租、救济饥荒等)以确保他们的生存。只要现有的财政机构能产生足够的收入,以满足常规和非常规的需求,国家没有理由将行政机器的触角延伸到县级以下。
历史遗产和国家构建:宪政还是专制?
在中世纪欧洲和帝制时代的中国,历史环境尤其是权力结构的模式各不相同,进而影响到中世纪晚期(或称帝制晚期)和近代早期各自的国家建构路径。正如布莱恩·唐宁所指出的,欧洲国家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式的政府形态,君主专制程度相对较弱,独立的拥有采邑的贵族控制了地方行政,并构成了军队的基础”(Downing 1992:249)。王权和贵族权力大体平衡,军事组织权力较为分散,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之间形成互惠关系,所有这些,均为中世纪后期欧洲宪政制度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是:(1)王权和贵族的权力平衡,导致乡村和城镇政府乘机而起,并获得诸多自由权利,制定自己的宪章;(2)代议制议会次第出现,国王借此与社会各等级之间就税收和战争问题展开讨价还价。这些社会等级包括在封建等级中享有地位和权力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以及掌握了城镇财政大权并构成社会等级的富豪;(3)法律具备了新的功能,即用来限制王权和其他权贵的行为,而不再仅仅被用来服务于皇室政策和惩戒竞争对手(Downing 1992:18—38)。
但上述发展在欧洲各地区有显著差异,并对18世纪的国家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依据奥托·辛茨(Otto Hintze)对代议制政权的分类,托马斯·埃特曼提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欧洲各地的地方政府呈现为不同的模式,并对日后各种不同形式的代议机构和政权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他认为,宪政政府之所以流行于英格兰、苏格兰、瑞典、匈牙利和波兰,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单一郡县和自治市镇的有序格局,让本地的自由民负责司法事务,维持治安,组织地方防务,征收税金。这些发展良好的自治组织所选举出来的地方代表,跟教会和贵族领袖一道,形成了国家的代议机构,有效地节制了国王的权力。相比之下,欧洲拉丁国家和日耳曼诸国,虽然也有议会或国会,但由于这些地方在基层治理方面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加上主管工商业的官吏对政治中心唯命是从,导致议会仅仅代表特权等级的利益,不具全国代表性。由于先天不足(尤其是由于不同等级的群体之间难以合作),这类议会容易被那些野心勃勃的国王所操控,从而为绝对主义的建立铺平了道路(Ertman 1997:19—25)。
显然,帝制时代的中国并不具备导致宪政制度在早期近代欧洲成长的历史条件。表面上看,由于县以下国家正式权力机构的缺位,从宋代直至晚清,乡村和城市的地方共同体在自身的治理方面均具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有各种各样的村规民约,界定所有成员在纳税、治安、防匪和公益事业方面的职责和权益。除非乡民之中出现争议,无法在内部解决,进而威胁到了乡民履行对政府的职责,否则官府一般不会干预上述活动(H.Li 2005)。但是,和中世纪欧洲许多地区的情况不同,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村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也没有在本地组织代议机构,让乡民选举村官,决定当地的政策。城镇同样没有出现自己的市政机关,独立于帝制国家的行政网络之外。相反,中国城乡的各种自我管理组织,不仅要为共同体成员的福祉负责,还要致力于满足国家的征税和治安要求,而非将国家的影响力排除在外。
归根结底,宪政政体在中国难以得到发展的原因,是自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尤其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诸国林立,战乱不休,与中世纪欧洲非常相似),从未形成代议制传统,用来限制帝王们的征税权力。而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的欧洲,原初形态的宪政机构渐次出现,对于中世纪晚期的代议制、公民权以及法治的全面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进而导致近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形成(Downing 1992:36)。同样重要的是,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与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相比,在结构上非常不同。除了个别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或宗教组织很少具有欧洲贵族和神职人员那样的自主权力和影响力。同样,中国的富商也不享有在欧洲所见到的基本权利、自由以及宪章所规定的豁免权。换言之,中国缺少像欧洲那样支撑其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绝非一个“绝对主义”的国家,因为绝对主义(absolutism,或译专制主义)本身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不受代议机构约束的王权,此乃中世纪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而在中国,这种基于身份或国土的代议机构从未出现过。同样,也不能以“东方专制主义”来解释帝制中国。卡尔·魏特夫在描绘此类政权时所设想的那些特征,包括统治者的无限权力、庞大的军力、高额的税收,以及国家的宗教基础等(Wittfogel 1957),并不完全适用于帝制时代的中国,至少不甚适用于清朝。应该说明的是,尽管宪政和代议机构从未出现于中国,但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权力并不是无限度的,而是受到意识形态和行政体制的约束。儒家思想和“祖宗规训”,要求统治者必须仁慈勤政,加上言官和大臣们的直言谏劝,使得皇帝在通常情况下难以独断专行。事实上,无论统治者是热心早朝、批阅奏章,还是不理朝政,国家事务均归训练有素的文官集团处理,他们会按照规章和各种先例履行职责,自主行事。
总而言之,18世纪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遗产,使其政府形态迥异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构建的任何路径。在欧洲,大国间的领土和军事竞争,驱动其财政需求不断上扬,而直接税(主要是土地税)的收入增长滞后,使得财政供需之间难以形成均衡。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国家要么增加对农村人口的剥削,强化对社会的控制,要么加强货物税的征收,向富人借贷,从而产生强制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形态。相比之下,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中国,由于缺乏能与之对抗的外部势力,清朝军队规模和军事装备大体未变,导致政府的财政需求和收入不仅有限,且相对固定;作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田赋也处在低位。不过,在18世纪,清政府的税收总量尽管并无太大变化,但仍然能够满足其常规支出的需求,甚至积有相当规模的盈余,在人口的持续增长耗尽经济剩余之前,足以应付各种非常规支出,这种状况至少一直维持到18世纪晚期。清朝国家的核心特征,一言以蔽之,是其财政构造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上独特的均衡状态。它实质上反映了一直持续至18世纪后期的中国地缘政治和人口规模的理想状态。
然而,这种均衡局面在18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越来越难以维持。人口和经济资源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导致政府财政盈余下降,因此在处理边患问题上渐趋保守。然而,正是在同一时期,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相继经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列强从未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毕竟是以手工劳动和有机能源为基础。尽管出现劳动分工和商业发展,人口压力也推动经济发展,但其增速依然较慢。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列强,在经济总量和制成品的整体竞争力上,没有一个是中国的对手。但是,到了1820和1830年代,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其制造能力迅速膨胀。化石能源在机器化生产和运输领域的大量使用,取代了旧的斯密模式或马尔萨斯模式所依赖的传统动力,刺激整个经济的指数级增长。关于经济增长的不同类型及其对于理解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的意义,参见Feuerwerker 1992;Wong 1997:43—52;Goldstone 2004。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力量,“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Marx and Engels\[1848\]1969)。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伴随而来的还有欧洲列强的军事威胁。不幸的是,清朝国家对此毫无准备。尽管在应对西北边患的过程中,清廷有效处理了危机,但直到19世纪中叶,清廷仍然未能放眼整个世界,将其地缘政治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视角之下,更没有打算以全局性的“外交”政策,取代旧有的局部性的具体“边患”处理方式(Mosca 2013)。更糟的是,19世纪的清廷,在全新的外患之外,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使其处理外来危机的能力受到制约。下一章将对此展开讨论。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
清朝是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中的最后一个王朝。那么,相比其他朝代,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这些独特之处,对现代中国形成又有哪些影响?
——编者按
复合型集权自主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把边疆与内地的两套不同治理体系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清朝国家的基本特征。首先,清朝的国家结构具有不同于以往中原王朝的鲜明的复合性(hybridity)。如前所述,清朝涵盖了两个在地理环境、人口、文化和制度上都差异甚大的部分:汉人内地诸省和由满人、蒙古人、藏人及其他非汉人组成的边疆地区。中央政权依靠内地诸省满足其财富和人力需求,同时通过建立和巩固边疆以维护地缘安全。为了确保财源,维持其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地位,清朝把内地各省置于其直接管控之下,并在地方治理方面,推崇儒家思想,实践“仁政”原则。而为了保障边疆稳定、提高对于朝廷的认同,清朝允许当地精英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还对流行于蒙古人和藏人中间的喇嘛教予以庇护,并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部落同汉人隔离开来。尽管存在着这些巨大的内部差异,清朝还是成功地将版图内不同族群的精英人士聚拢在一起,对朝廷产生共同的认知,这要归因于清廷在治理不同地区的过程中,重视利用宗教纽带、文化涵化和制度建设上的因地制宜,而不仅仅依靠军事控制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
其次,在内地各省,清廷在中央和省级行政体制中开创了一套复合结构,由满洲贵族与汉人官员平分关键性的文武职位。不过,尽管清廷一直宣扬满汉平等,这种“满汉共治”的原则并未应用于中下级的朝廷官职,这些职位大多由满人占据(Rhoads 2000:45—46)。清朝的兵力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类。前者主要由满人构成,驻防内地各省重要城市;后者由汉人组成,以维持地方秩序。城市里的满人也跟汉人隔开,自成满城。虽然这些生活于内地的满人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原有的语言以及其他一些文化特征,产生认同危机,但是,清廷仍然鼓励在满人内部使用满语,并力图维护源自游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研究者把这套做法形容为“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Elliott 2001,2006)。因此,纵观有清一代,满族从未被汉人文化所完全同化。到了清末,满汉精英之间的矛盾更是愈演愈烈,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满洲贵族对革命党人反满的一种本能回应,同时也是汉人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意识日渐觉醒的结果。
如果再就边疆与内地各自的治理体系来看,清朝国家则具有“集权自主”(centralized autonomy)特征。首先,它是高度集权的:无论治理边疆的理藩体制,还是内地的州县体制,都受到中央的有效的直接控制;无论是内地的州县官还是蒙古各盟的首领或各旗的札萨克,新疆穆斯林地区各地的伯克,均由清朝中央直接任命,而藏区噶厦的四名噶伦的任命,也须经由中央的批准。但是,在内地的州县以下,或边疆的盟旗、伯克、噶厦以下,却各自存在着一套相对自主的治理体系,承担日常治安、司法、征税、公益等具体职能。正式的官僚体制或理藩制度高度集权于中央,并且在制度建设上高度标准化,内地各省之间以及边疆各地内部差异不大;但地方上自主的日常治理制度却有明显的区域变化,其具体形式取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
集权国家的低成本
理解清朝国家高度集权的上层机构与相对自主的底层结构同时并存的关键,在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机器运转的低成本。如果把清朝和之前的汉人王朝加以比较,这一点尤为突出。例如宋朝和明朝,作为汉人政权,均面临北方游牧部落持续不断的乃至致命的侵扰。宋朝先后与女真及蒙古发生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还被迫南迁,最终亡国。明朝的衰亡,也由于跟满人对垒,开支浩繁,不得不想尽办法筹集兵饷,导致民怨沸腾。相较之下,清朝在将蒙古、新疆及西藏纳入版图之后,再无传统意义上的“边患”。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周边没有可与其一争锋芒的势力,主导其与相邻国家关系的是以清廷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由于没有任何势均力敌的外来威胁,清朝统治者没有必要保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更无须像早期近代欧洲国家那样,在列国竞争的格局中一直不断地更新军事装备。清朝维持一支常规军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内秩序。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其常备军的规模保持在80万人左右,包括20万汉人绿营和60万满洲八旗(彭泽益1990:55;陈锋1992:23,97),在清朝人口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1700年前后约0.4%,1800年前后约0.19%,见Pingti Ho 1959)。而政府的常规军事开支,1720年代每年1300万两,1790年代每年1700万两(陈锋1992:194),占清朝经济总量的比重同样很小(1720年代约1.24%,1790年代约0.85%)。虽然维持常备军的耗费占清政府每年总开支的58%—65%,但仍在其支付能力范围之内。从1730年代到1840年代,政府每年军事开支稳定在1700万两上下。出现这种常规军事开支相对稳定的状况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外来军事挑战,现有的常备军规模足以在平时确保国内局势稳定,故而无须扩充和更新军备。
除地缘上的对外优势使其能够维持较低的军事开支,清朝的政府开支较低还有一个原因,即维持国内秩序稳定所需要的花费极低,这可进一步归因于两方面:其一,内地人口在族群、语言和文化上保持着高度同质性,尽管地区间的差异很大;其二,政府管理采用的是一套承袭自明朝的基于公平竞争的文官遴选机制,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
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以下几个关键环节导致中国国家在族群融合的基础上走向集权并日臻完善:(1)商朝和西周时期(前1600—前770),华夏族群从黄河中游向东、向南扩张,形成华夏文明核心地带;(2)秦朝(前221—前206),华夏国家持续向南扩张,并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包括文字、交通和计量的统一)取代分崩离析的封建体制;(3)儒家世俗说教在汉代(前206—220)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此后在历代依然保持其正统地位,教义也日趋复杂;(4)唐朝及此后历代采用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士人地位上升,主导了地方社会。
上述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到了11世纪,在族群融合和文化昌盛的基础上,华夏国家已经日臻成熟,尽管王朝屡经更迭,但这种国家体制变化不大,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这些世纪里,中国的国家体制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同时代的欧亚大陆其他国家。首先,士人阶层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高度认同,因而使得政府可以将大多数行政职能下放给士绅,而不必将行政权力延伸到县以下的数百个村落。其次,秦代以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确立,排除了贵族阶层拥兵自固、威胁中央,导致四分五裂的可能,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出现过。再次,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与官僚制集权国家的融合,以及儒学对“怪力乱神”的质疑,大大限制了各种内生或外来宗教的生存空间,使其无法挑战儒家思想在精神世界的正统性,也无力发展出自主而庞大的宗教组织,对各种世俗权力构成威胁。最后,科举考试在吸纳富商进入士人阶层、培养商人对朝廷的认同、阻止他们形成一股自主的社会力量等方面发挥巨大效用,削弱了商人通过经济途径干预国家的潜在可能。
因此,宋代以后,统一的官僚制国家在华夏本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朝廷牢固控制了各项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而不受地方割据势力、宗教组织或商人阶层的挑战。比起欧亚大陆的其他强国,中国用于维持有效统治的开支低得惊人。直至19世纪末,清政府的规模仍只限于大约23000名享有俸禄的官员(Chang 1962:42),即平均每17000人供养一名官员。国家的行政开支非常有限。例如,1766年,所有文官和王公贵族的薪俸总共只有497万两;该年国家的总支出亦仅为4221万两(陈锋2008:408—409),约占同期国家经济总量的2%。清代国家政府确可谓规模小、成本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方可理解清代地方治理的独特之处。
在帝国与主权国家之间
清朝和之前的汉人王朝确实有所不同。那些汉人王朝虽然也讲儒家的“仁政”,但为了对付边患,往往不得不增设苛捐杂税,以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一如在明朝末年所见。清朝的不同之处,在于把蒙古、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之后,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边患问题。由此,清廷得以把军费以及税率降至较低的水平。同时,为了在汉人社会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清廷也有必要采用轻徭薄赋政策,忠实地践行儒家的仁政理念。
清朝地缘战略的核心是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全。纵观清朝早期历史,与漠南蒙古的同盟关系,是满人得以征服内地各省的重要因素。在平定中原之后,内蒙古和满洲地区作为清廷的“后院”,一直是清朝战略安全的重中之重;直至19世纪后期中国被卷入全球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导致其地缘格局发生根本颠覆之前,这种局面一直未变。也正是这样一种地缘格局,催使清廷下决心平定对漠南蒙古造成最大威胁的准噶尔蒙古部落,并在此后将西藏和新疆并入版图,以彻底消除边患。但是,边疆地区对于清朝的重要性仅限于此。统治者既没有被新疆的人口和财富所吸引,也并不是真正对西藏的喇嘛教感兴趣。这些地区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担负着维护清朝地缘安全的作用。
但是,清朝并非一个军事帝国。尽管在其早期历史上,曾经全力以赴扩张版图,但是在征服中原之后,清朝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清朝统治者不再对开疆扩土感兴趣,而是致力于将自身转变为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在治理内地各省和处理与周边朝贡国的关系方面,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大部分制度。它既不想对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进行征服,也无意要求藩国进献大量的贡品。在定都北京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清朝满足于它从明朝所承袭的版图。就疆域而言,此时的清朝跟明朝的差别,仅限于满人入关时所带来的满洲地区和内蒙古,以及1683年从反清的郑氏手里收回的台湾。此后,从1690年代到1750年代,清朝次第把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乃是抗御准噶尔势力的军事威胁的结果。一旦彻底消除了此一威胁,清朝再也没有兴趣将其边疆向中亚腹地进一步拓展,尽管此时清廷的财政之充沛已经达到了历史顶点,足以支撑其继续用兵。相比之下,军事征战和疆域变动始终贯穿于欧亚大陆其他帝国的历史。这些帝国往往源自小块核心区域,然后逐步对外扩张,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富,并为此将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变成其藩属,再将藩属进一步变成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奥斯曼帝国(详见第十章)。清朝平定中原后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中国本土规模够大,财政收入又足够充盈,除非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否则清廷并没有必要无休止地开疆拓土,将藩属并入版图,用以增加国库收入。总之,清朝国家的形成,虽具游牧民族的背景,并一度展现出征服王朝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与欧亚大陆诸军事帝国相似的道路,但它跟后者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迁都北京后,清朝很快转变为一个复合型国家,既延续了内亚游牧民族的传统,又承继了中原王朝的政治遗产。
最后,清朝在本质上又和现代主权国家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清朝的立国理念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所有主权政体一律平等的原则南辕北辙。尽管如此,在19世纪卷入欧洲中心的国家体系之前,清朝仍然显现出一些向主权国家发展的蛛丝马迹。尽管清朝将明朝的朝贡体制继承了下来,尽管这一体制对于维系其统治合法性非常重要,但是清朝并不热衷于增加朝贡国的数量及其觐见的次数。通过在中亚内陆的开疆拓土,清朝在对外交往方面,要比明朝显得更有信心、更具安全感。在处理欧洲和俄国来华的商人和使臣问题上,清朝灵活应对着他们的各种需求,并没有要求对方严格遵守根据宗藩体系确立起来的交往方针。更重要的是,清朝通过与俄国和中亚国家的交锋,逐渐树立起领土主权的意识,通过一系列条约、协议的谈判,与相关的周边国家之间明确了边界(参见Esherick 2010:23),从而告别了中国旧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
清朝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
鼎盛时期的清朝统治者,掌控着辽阔的疆域和多元的人口,比起先前的帝王都更有可能宣称自己是普世君主,并对大清版图内的各种文化和语言都表现出尊重,无论这仅仅是一种姿态,还是出于真心。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在与具有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民众打交道时,的确是以不同的形象出现的。在内地汉人社会,清帝力图以儒家圣贤君主的姿态展现自己;面对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徒,以及满洲地区的萨满教信众,则以慷慨的护主身份出现;同时,为了让从满洲到中亚的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臣服于朝廷,统治者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先前部落国家时代可汗制度的传统。乾隆帝因此会不时地自视为跨越文化和族群藩篱,统御四海的“天下共主”(Crossley 1992,1999;Rawski 1996,2004)。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清朝将边疆和内地等同视之(参见WaleyCohen 2004;Millward 1998:201),也不意味着清朝皇帝作为非汉人族群之护主或可汗身份,跟在华夏本土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所扮演的“天子”角色同样重要。概而言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迁都北京、平定中原之后,清朝将自己的定位从偏居边陲的满人政权转变为统治华夏本土的正统王朝,并且重新界定了“中国”,涵盖范围从内地省份延伸至边疆地区,从而使大清等同于“中国”(参见G.Zhao 2006;黄兴涛2011)。相应地,清朝统治者也改造了自身与边疆地区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部落首领之间平等相处,而是继承了先前中原王朝的一套规制,将其界定为基于儒家政治秩序的君臣关系。对于清廷来说,内地各省无疑构成其疆域的主体,因为这里不仅为国家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所需的财富和人才,同时还为他们统治华夏本土、边疆及藩属国提供了政治的和文化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尽管清廷允许边疆地区的精英享有一定的行政和宗教自主权,但在处理与边疆的关系时,毫不犹豫地将其纳入承袭自先前华夏王朝的儒家政治秩序的框架之中。
总之,清朝最好被视作一个二元国家,它融合了游牧民族征服王朝的传统与中原王朝的文化及政治遗产。相较于此前曾经入主华北或统治中国全境的异族王朝,包括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386—534)、契丹人建立的辽朝(907—1125)、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06—1368),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最长(1644—1911)。清朝国祚绵长之根本原因,是其相辅相成的两个特征,皆为国家建构所不可或缺:(1)将内亚边疆地区正式纳入版图,由此消除了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2)继承了前明的正统,从征服王朝转向复合型王朝。清朝通过尊重士人特权、认同儒家理念、因地制宜地选择治理策略等,赢得了地方精英的忠诚。在内地各省,它既依靠士绅精英处理乡村日常行政事务,同时又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自主权,由此既能把汉人社会置于中央的有效统治之下,又将政府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同样,在边疆地区,通过庇护喇嘛教及允许当地的宗教和世俗领袖掌握一定的地方行政事务自主权,清廷也赢得了他们的支持。由此,清朝无须大量派驻军队,即可维持边疆的稳定,同时也无须使用强制手段,即可确保边陲地区非汉人族群的臣服。清廷强调通过宗教和政治纽带稳固边疆,而非诉诸暴力,也有助于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产生认同。前后两个世纪的开疆拓土和边疆的巩固,不仅使得中国的版图得以扩大,也有助于在汉人与非汉人精英之间产生共同的国家意识,即他们一同生活在一个重新界定后的疆域之内。这种观念的生命力,甚至比国家本身更加久远。归根到底,清朝可谓帝制时代华夏国家谱系的最后一个王朝。但清朝的“中国性”,跟清之前的王朝不尽相同。“中国”的概念重新得到了界定,既体现了中国以往的文化和政治遗产特征,又显现出以往所未见的多样性和复合性。事实上,中国文化本身之所以如此悠久而富有韧性,正是因为其长期以来一直保有向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族群因子开放的传统。正是由于华夏族群在同化其他民族且又吸纳异族文化遗产的要素方面,所展现的非同寻常的能力,才使得中华先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坚强生存,繁衍不息。清朝只是这一长篇故事的最后一章而已。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有条件忠诚之滥觞
重塑晚清权力结构的关键性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此前,满人和八旗精英几乎占据了清朝的全部重要职位。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彻底颠覆了此一局面,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汉人督抚逐渐崛起。最终,权力由清廷向督抚倾斜,汉人取代满洲和八旗贵族,成为晚清政治的主角。
——编者按
汉人疆吏之崛起
重塑晚清权力结构的关键性事件是发生于1850年代及1860年代早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此前,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省的整个政府体制的特征,不仅在于其沿袭自明朝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还在于让满人和八旗精英充任几乎所有的总督职位,以牢牢控制各省的军政大权。仅把半数的巡抚职位留给汉人,以管理地方民事。这在乾隆朝(1736—1795)尤为突出(孔令纪等1993:327)。在嘉庆(1796—1820)和道光(1821—1850)两朝,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此时,汉人精英占据了半数总督的职位。例如,1850年,10个总督中的6个是汉人,15个巡抚中仅有1个是满人,其余全是汉人。然而,一旦遇到危机,皇帝总是委任满人充当特使(经略大臣或参赞大臣以及后来的钦差大臣)去监督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督抚们要听从钦差大臣的指令,在军事行动中处于辅助地位(所谓“承号令,备策应”)(QSG:3264)。在正常年月,督抚们则与另外两个中央派驻本省的重要机构,组成错综复杂的监督和制约关系;其中一为布政使司,监管本省的民政和税收,一为按察使司,掌管本省的诉讼和判决。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颠覆了此一传统。在最初两年,清廷依靠自己的正规军即绿营镇压太平军,却未能抑制其迅速蔓延。因缺乏训练,组织涣散,军官腐败,绿营早已失去战斗力。结果,太平军很快于1852年12月进逼到湖北武昌,即将沿江而下,攻占富庶的长江下游主要城市。此时,清廷不得不允许在籍官员就地招募成年男性,组建团练,保卫乡土和阻击太平军。这种做法在1790年代镇压白莲教叛乱时即曾施行过。湖南的曾国藩是1853年初被咸丰帝任命的分布于10个省份的43个团练大臣之一。1854年7月,曾国藩带领一支人数过万的军队夺回了武昌,显示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在随后几年里,他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作战,最终成为两江总督,1859年升任钦差大臣,总管江南军务。1861年末,他进一步被授权统管江苏、江西、安徽和浙江四省文武官员。在他的举荐下,一大批来自湖南的下属被任命为长江中下游各省督抚。湘系的崛起因此成为晚清数十年省级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军机大臣文庆(1796—1856)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清廷不得不依靠汉人精英而非满人,授之以军政要职:“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薛福成1987:250)据估计,从1851年到1912年,满人仅占据34.6%的巡抚职位和22.2%的总督职位,而在整个清代,满人占据了57%的巡抚和48.4的总督职位(Rhoads 2000:47—48)。
导致晚清政治中汉人督抚持续占支配地位的原因,首先是他们牢牢控制了取代正规军而成为镇压太平天国主力的私人化兵勇。湘军与正规军的主要区别,是其用私人纽带把不同层级的官兵联结在一起。组建团练时,每一个层级的指挥官都要负责招募下一级的军官,直到10人一队的头领。头领负责从家乡招募士兵,知道下属的住址、父母、性格和能力,士兵要签押保证遵守军队的规定(刘伟2003:119;Kuhn 1970:122—148)。这种组织手段杜绝了绿营常见的士兵战场叛变和违法行为,也使团练沦为地方督抚的私人武装。
团练之所以为督抚们所把持,还因为它能自我维持,无须中央的支持。督抚们须“就地筹饷”,动用所有可能的资源供养自己的团练,比如征收厘金,出售官衔,截留解饷和海关收入,征收田赋附加,等等,前文已述。为了确保筹集到足够的款项并有效地经营管理,各省都建立了由督抚直接控制的财政机构,即粮台或中粮台,可以不经省布政司的监管而分配资金和报销费用。
督抚们不仅控制各省的军务和财政,使它们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央政府的监督;他们还把亲信安置到本省的重要职位,从而控制了地方政府的人事。清朝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各省督抚可以向朝廷举荐任命本省府县的官员;不过,他们的举荐权是有限制的(总督每年推荐3名候选人,巡抚每年推荐2名)(刘子扬1988:35)。在出任两江总督掌管长江下游四省军务之后,曾国藩突破了上述限制,连续举荐一系列职位,囊括从巡抚到布政使和按察使,直到更低层级的官职。只要认为合适,各省巡抚或总督便会设立名目不一的“局”“台”“所”,以负责办理团练后勤以及与战后重建有关的各项具体事务。这些机构都处在正规的政府体制之外,仅向督抚负责。
概言之,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汉人督抚日显强势,独揽所辖各省的军事、财政和人事权,这是19世纪中叶之前所未曾有过的。他们通过私人关系结成了官僚集团,与过去在清朝政治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满洲贵族分庭抗礼。因此,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乃是权力由清廷向督抚倾斜,汉人取代满洲和八旗贵族,渐成晚清政治的主角。
忠诚之再定义
清廷对汉人精英权力的迅速膨胀自然有所警觉。例如,1854年曾国藩夺回武昌的消息,曾让咸丰帝既兴奋又焦虑,因为某大学士提醒他,“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薛福成1987:252)。因此,咸丰取消了原先想委任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决定,在随后的六年里对曾国藩始终持有戒心。曾国藩仅凭徒有其名的兵部侍郎之衔,转战邻近数省,在试图寻求地方军政当局提供后勤支援时,屡遭挫败。在指挥团练在长江中下游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把自己直接控制的正规军(即绿营),集结在太平天国首都南京附近,设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用来围困南京,以待团练消灭了大部分叛军后对南京展开进攻。换句话说,由满人将领统率的两大营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由汉人统率的团练在平乱中获取头功。难怪两大营于1860年被太平军彻底摧毁时,曾国藩在私下与下属交流时喜不自禁(范文澜1949:144—145)。此后,清廷不得不完全依赖曾国藩和其他汉人精英统率的团练,授之以总督职位,统辖四省军务。
不过,接下来的数年里,清廷和汉人精英的关系依然紧张,某些时候还格外尖锐。例如在1864年7月,曾国荃(曾国藩之弟)率领湘军攻破南京,决定性地击败太平军。为了阻止曾氏兄弟居功自傲,予取予求,清廷威胁要调查湘兵抢劫太平天国囤积的大量财宝以及太平天国幼主的下落。曾国藩不得不做出让步,许诺解散湘军,削减军事开支,让其弟返归原籍。结果,清廷停止了调查。再如1865年镇压太平天国后不久,恭亲王因数次过错屡被弹劾,其中一个过错便是过于依赖像曾国藩这样的汉人。慈禧太后也对恭亲王怨恨已久,欲褫夺其所有职位。曾国藩为此“寒心惴栗之至”,在一条小船上与亲信商议应对之策时,两人“唏嘘久之”,与清廷的关系几近破裂(朱东安2007:37)。幸运的是,恭亲王不久复出,曾国藩的危机得以解除。满人统治者与汉人精英之间的联手,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儒家的君臣伦常观念之上,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言之,君臣关系是互惠的,君待臣以应有之道,乃是臣忠于君的前提条件。在双方关系遭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如果其中一方不作出妥协,危机便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幸运的是,对清廷而言,曾国藩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既熟谙儒家伦理传统,又具有治国才略,始终能够凭其机警和克制,驾驭一再出现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廷的有条件的忠诚,可以被视为对清廷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尊崇儒学并且在任用官员方面缩小满汉差异的一个回报。正因如此,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大部分汉人精英都认同了源自满族的清王朝,接受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并用儒家伦理观念来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曾国藩忠于清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双方都面临着同样的敌人,即太平天国起义者。对于曾国藩和其他许多汉人精英来说,与太平天国作斗争不仅是为了保住大清,更是为了捍卫华夏文明。正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雄辩地宣称的那样,太平天国起义者所崇拜的洋教,与儒家纲常格格不入,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已经遭受根本威胁(ZGF,诗文,232—233)。
概言之,1850年代和1860年代汉人精英之所以在晚清政治中如此独特和强大,主要得益于他们拥有以前从未具备的优势,即控制了所在省份的军务、财政和人事大权;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抱团的派系,以集团的形式捍卫自身利益并与清廷打交道。湘系的核心当然是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之前,其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其职业生涯的顶峰,“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容闳1985:107)。在曾国藩周围,有众多的下属后来都升任地方要职。到1872年,其中11名先后被任命为巡抚或总督。曾国藩门徒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李鸿章,此人后来组建了以其省籍命名的淮军。李鸿章及其兄同时出任总督达4年,即1865—1877年,他的四个重要下属则出任巡抚(龙盛运1990:482)。相形之下,同一时期仅有一两名满人出任总督,其中有两年根本没有满人总督。同时,在此一时段,通常每年仅有一名满人巡抚,只有其中一年存在过2名满人巡抚,还有一年根本没有满人巡抚(同上)。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和之后,清廷与汉人官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迁都北京后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的中枢曾经历了一个集权的过程,其集权程度超过了此前的中国历朝历代。征服中原后,满人统治者不仅从明朝继承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政府体制,还把中原的体制与其原先的猎牧部落政权的一些做法(即军事行动中的互相合作,部落联盟体制之下各部落首领的权力共享,以及大汗对所征服和奴役对象的绝对权力)结合在一起(Crossley 1992)。18世纪的清朝皇帝一直对清初遗留下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持抵制态度,重建了中枢决策机构,力图把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同样地,在处理同汉人官僚的关系时,清朝皇帝拒绝建立一种互惠关系。儒家治国理念把这种互惠关系理想化,认为臣对君的忠诚端赖君待臣以应有之道。相反,满人统治者把自己同汉人的关系视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要求后者无条件地服从和效忠(郭成康2000)。然而,这种单向关系在19世纪后半叶期走向终结。汉人官僚在镇压叛乱和处理外交危机中变得不可或缺,他们在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上权势渐重,在与清廷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具自主性,对清廷的忠诚也越来越讲条件。
“十八国”
这里有待澄清的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发生的分权化趋势,是否会在太平天国之后随着清政府试图恢复它已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早期失去的军事和财政权而扭转过来。中央再度走向集权的一个重要迹象,是1864年清军占领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之后,大部分湘军被遣散。的确,在数月之内,一支曾经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指挥下攻陷南京的5万湘兵被彻底解散,曾国荃也辞去所有职务,回原籍“养病”。一年后,鼎盛时期一度超过20万人的湘军大部分被裁撤,只留下数营、约一万人用于维持地方治安和长江巡逻。
然而解散湘军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源于湘军的淮军的幸存和壮大。1862年,李鸿章因指挥自己组建的淮军(士兵多来自其家乡安徽)抗击太平军,保住了上海,而被委任为江苏巡抚。在裁减老弱残兵后,淮军仍然保持超过5万人的规模。后来证明,在清廷剿杀捻军(1853—1868)的行动中,尤其在1865年捻军大败清朝最强悍的正规军并杀死其统帅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之后,淮军是必不可缺的。李鸿章彻底而迅速地消灭了捻军,在处理棘手的对外事务中也展示了很强的能力,这些都导致清廷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1870—1895),使他成为19世纪晚期最有影响的汉人官僚。他的淮军也于1875年壮大到95个营,在随后的20年里扩张到146个营,在十多个省份都有淮军驻扎。实际上,淮军取代了过时而无能的八旗和绿营,成为清廷装备最精良、最重要的防卫力量,直到义和团之后的10年才被袁世凯的新军所取代(董丛林1994:28;刘伟2003:277—278)。李鸿章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使他能举荐自己信得过的下属出任淮军、新建的北洋水师以及一些省级机构的重要职位。这些人凭借家族和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和庇护关系,编织成一个集团,从1870年代到1890年代,一直主宰着清朝军队。
清廷不仅未能重建其对军事的集权控制,就连抑制督抚们不断增长的行政管理自主权也困难重重。在同治、光绪两朝,清廷一再采取措施限制督抚的权力。例如,在任命省级或更低层级的官员时,清廷只允许巡抚推荐,而把最终任命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同治朝伊始,便一再重申这项政策。为了阻止督抚在荐举中任人唯亲,1894年清廷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即只要其中一个被推荐者不合格,所有一同被推荐者均不能被录用。为了强化对督抚的监督,清廷鼓励各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就其所察觉到的任何过失,弹劾当地的督抚。清廷认识到,这些专员从1860年代以来,除了例行向朝廷报告自己的到任和退休事宜,从未向朝廷提交过任何有实质内容的奏折(刘伟2003:362—363)。不过,这些措施对督抚们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央控制不了由督抚组建和任命的非正规机构中大量非正式的职位(诸如总办、会办、提调、委员、司员等等);这些机构在1870年代至1890年代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纷纷出现。
19世纪晚期,清廷重新集权的最大失败,在于它未能控制地方财政。以厘金为例。据估计,各省向清廷上报的厘金收入,仅占其实际总收入的30%—40%。1894年,清朝各级政府的实际收入可能高达1.46亿两,而账面上的财政收入仅为8100万两(史志宏、徐毅2008:133,275,279,289)。同样,清廷很难知晓到底有多少钱花在与自强运动有关的新项目上,这些费用从未被列入常例支出。当督抚们缺钱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向外国银行或者国内债权人借款而无须清廷批准。尽管清廷已经恢复了太平天国时期一度瘫痪的旨在监察各省财政活动的审计制度,由于这些隐形收入和不明就里的支出大量存在,这套审计制度也失去效力,变成敷衍了事。结果,晚清的督抚们在财政上日渐自主,这与19世纪前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有效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
鉴于各省督抚在管理地方政府的军务、人事和财政方面的自主权不断增长,时人把十八个行省称为“十八国”也就不足为奇了(LQC,6:614)。清廷在防卫和财政收入上依靠督抚的做法也使后者有能力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不同于19世纪之前那些在朝廷面前束手束脚的各省督抚。以李鸿章为例,在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其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时人这样评论:“(李)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奏章,所请无不予也。……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转引自王尔敏1987:397)李鸿章之外,声名显赫的督抚还包括:左宗棠(1812—1885),系李鸿章的长期对手,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早期,一直担任东南、西北和长江下游诸省总督;刘坤一(1830—1902),在1870年代至1890年代多次出任长江下游和南方沿海诸省总督;以及张之洞(1837—1909),于1880至1890年代先后担任三个不同地区的总督,但时间最长的是在湖北和湖南。这些封疆大吏在为清廷建言或决策过程中均起到关键作用。
自强新政与原初型民族主义
督抚们在财政构造和行政管理上的相对自主,也使他们能够举办一系列后来名之曰“自强”或“洋务”的建设项目。在1860年代早期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即曾出现过用西式方法训练、用西式武器装备自行招募的军队,可视之为自强运动的起点。自强运动的重心,是设立在上海、南京和天津的三大军工厂,设立在福州的一座近代造船厂,以及分布于其他各省的一些小规模兵工厂。这场近代化运动的高潮,是建立三大水师,以分别巡防华北、华东和华南近海;其中建成于1888年的北洋水师不仅是中国也是当时整个远东地区最大的舰队。为了配合国防建设,上述项目往往都还附设了把西书译成中文的译书局,以及招收学生学习外语和近代科学的学校。此外,这场运动在1870年代还延伸到民用领域,建设了轮船航运、铁路运输以及采矿、冶炼、电报、纺织等一系列民用项目,甚至将幼童送往美国留学。除了水师系由中央政府筹资建设,其他项目均由地方督抚发起和筹资建设。从1866年到1895年,兴办和运营这些军工厂和造船厂的费用,计达5000万两至6000万两。民用项目的集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官办,即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有的则是地方政府投资一部分、向社会募集一部分,也有的全部由商人投资,但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即所谓官督商办。同一时期,地方政府花在这些民用项目上的费用,加在一起可能高达1500万两(周育民2000:303—304)。
各省督抚建设军工厂的直接原因,当然是要用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这样也抬高自己在官僚体制内的地位。但这个自私的动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场自强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并发展成一场涉及国防、制造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性近代化运动。在为新的建设项目辩护时,李鸿章和其他领导人总是把它与中国的“自强”联系起来。除了通过“自强”回应西方列强的挑战,还要应对日本的竞争,因为日本也在不遗余力地使其军队近代化,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新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明治维新前四年的1864年,李鸿章就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危险,在呈给清廷的一份奏折里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他还写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LHZ,29:313)
还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在论及中外关系的奏章中每提到本国时,都使用“中国”二字而不是清朝官方文献和话语中更常见的“大清”“皇朝”“天朝”之类用词,这反映了19世纪中西冲突过程中汉人官僚意识上的微妙变化;他们更多地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而非仅仅从清王朝的立场,来倡办近代化事业并重新定位自己的认同。这种意识反映了19世纪后期在西方列强的反复威胁刺激下,汉人精英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萌发。这种民族主义意识还很模糊,并与他们对清廷的忠诚纠缠在一起。不像20世纪民族主义弥漫全国,19世纪这种初始的民族主义还只限于汉人统治精英;他们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即已经接触过西方和日本。此种意识根源于儒家治国思想中的理性实用精神,刘广京谓之“儒家爱国主义”(K.Liu 1970)。
各省精英的早期民族主义意识有其局限性,因为他们通常是把地区的和个人的利益而非全国性利益放在优先位置。疆吏们手中掌握大量的且不断增长的非常例和未上报的各项收入,根据个人的立场和利益来决定资金往哪里花、花多少。他们都热心于把一切可获得的经费,用于建设和强化自己的军工和民用产业。他们也愿意把资金以“协饷”的方式投放到亲朋同僚圈内的那些督抚们所举办的项目上,或者用于自己所提议或支持的用兵方案。然而,他们极不情愿把朝廷摊派的税额解往与其无关的目的地,总会百般延迟或者减少他们的解款。在自强运动存续的30年时间里,每个自强项目或者用兵行动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督抚们的态度及其所贡献的资金数额,这在下一章所讨论的边疆和海疆的防卫中,将得到最好的证明。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国家转型的连续性
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与“帝国—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完全不同。它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20世纪中叶达到的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
——编者按
以上对影响中国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的讨论,对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国家的特质到底有何含义?
首先,奠定现代中国的疆域和族群构成基础的清朝国家,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征服帝国。前面我们已经反复论证,清朝并不依靠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恰恰相反,边陲整合在迁都北京后的清朝历史上仅仅限于1690年代后期至1750年代中期的半个多世纪,是在自身的核心地缘战略利益受到根本威胁后的被动反应和预防措施;在1690年代之前的半个世纪和1750年代后的其余年份,清朝从未寻求陆地疆域的进一步扩张。一言以蔽之,边陲用兵是1644年以后清朝历史上的例外,而非通则。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除了准噶尔部落一度构成威胁,直至1840年代之前,清朝在其周边并不存在任何对其构成致命威胁的竞争对手;而内地十八省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已足以满足其日常开支所需,并能产生巨大盈余。它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上承明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王朝,并以内地各省为其全部的财源;而对边疆各地区,则以军队加以驻守,以确保其地缘战略上的安全。因此,1640年代以后的清朝地缘战略取向是守成的,而非外扩的;它始终能够保持整个版图的大体稳定。与周边邻国的边界,也通过正式谈判或非正式的习惯性划分而得到明确的界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并不寻求通过战争获得邻国的土地,而是一直保持着和平状态。这与欧亚大陆的所有征服帝国完全相反:后者以扩张为其生存方式;一旦失去扩张能力,便纷纷走向萎缩和四分五裂的时候。所以,我们最好把清代中国定义为一个早期近代的疆域国家:它既不同于靠战争维持其生命的军事帝国,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历史上缺少明确疆域概念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它拥有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版图,拥有一支庞大的形制完备的常备军,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化的行政体制,拥有一个高效的无须依赖外包的税收系统,此外,在各族群精英中间有着通过多种方式凝结而成的共享的国家认同(这当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所有这些,都使得清代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主权国家更为接近,虽然它不是一个正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之一员。
其次,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显示,1850年代之前的清朝作为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与此后日渐融入世界国家体系从而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连续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疆域而言,从清代到1949年后的人民共和国时期,由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与非汉人各族群为主体的边疆地区所构成的格局一直未变。这与欧亚大陆旧帝国在衰亡后裂变为众多主权国家,以及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后在第三世界诞生了众多“新兴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理解这一反差的锁钥,在于清朝国家的形成动力和治理方式,与上述诸帝国有根本的不同。清朝与其说是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一个濒临近代主权国家边缘的前近代疆域国家;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前近代疆域国家所业已具备的各种资源和遗产(固定的疆域、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巨大的财政资源、对国家的认同等等),晚清政权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全部边疆,逐步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并且将其版图完整地传承于1912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其二,就权力结构而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转型,一直是在集中化与非集中化的辩证运动中展开的。权力的非集中化,既推动了国家建设,为更高程度的统一和集中奠定了基础,又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统一和集权的最大障碍。从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义,到民初的集中化地方主义,从国民党的不完全集中主义,到共产党的全面集中主义,中国的国家转型,正是在克服非集中化的过程,一步步走向更高程度的统一和集中。
因此,现代中国的形成,最好被视作不同的历史遗产叠层累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涵是由以下四个各具特色的层次所组成的。在其新近的表层,中国呈现为一个党治国家,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它是共产党革命尤其是1946—1949年内战的直接结果。在此表层之下的第二个层次,中国呈现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下与所有其他国家一律平等,并且对于其官方地图所显示的边界之内的所有土地和水域拥有排他的主权。它的出现,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被逐步纳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果,并且以丧失部分领土和主权为其代价,而国民党国家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建国努力,对于界定现代中国的主权范围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在第三个层面,中国还把自己表述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行政划分上包含23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省份,4个直辖市,以及5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这一行政的和人口的区域划分,源自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疆域整合,同时也离不开此后一个半世纪清廷对边疆的用心治理。而处在国家历史建构最底层的,则是华夏族群在其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原初“中国”及其所孕育的延绵不断的文明;它为现代中国人民形塑民族认同、建造现代国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丰沛的文化资源。中国的国家转型,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上述四个层次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含义;现代中国孕育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但更是清代以来国家转型的结果。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显示了一个与既往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所形成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认识范式完全不同的路径。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人们把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帝国崩溃后,有相同族群或文化背景的民众组成单一的“民族国家”视为唯一的“正常”路径,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体现民族国家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是欧美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事实上,作为国家形成先行者和“民族国家”标本的那些西欧国家本身,在其形成过程中,亦充满了军事征服,某种程度上与帝国的形成过程并无实质性区别;同时在彼此竞争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外扩张,把自己打造成殖民帝国;这些所谓民族国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而已。而19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在非西方世界纷纷诞生的所谓民族国家,也大多是在原先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在短暂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人为地匆忙产生的,并且大多以欧美的代议制民主为仿效的榜样。然而,它们随后所经历的往往是持续的政治不稳定,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战争乃自种族灭绝,以及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贫穷,形成所谓“失败国家”。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与上述“帝国—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完全不同。它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20世纪中叶达到的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驱动这一演进历程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的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那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外来影响的决定性支配。中国的建国力量,从晚清的改良和立宪派,到民初的革命党人,以及20年代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都曾一度倾心于欧美、日本或苏俄的各种建国模式,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国民党国家的半集中主义
在全面抗战前和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同样清楚的是,国民党的国家建设远没有取得切实的成功。制约国民党建国成败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其财政构造、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认同上的“半集中主义”特征。
——编者按
在全面抗战前和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5),国民党在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方面取得了进展。它恢复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完整,在控制并消除国内分裂状态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在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已击败党内的对手;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范围,也从华东数省扩张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南和西南各省。在所有这些省份,一个中央集权的架构已经在行政、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立起来。在财政上,国民党国家通过有力的集中化和标准化措施,控制了全国的间接税,大大拓宽了税收基础,从而推动国民政府努力寻求整个国家的军事和行政集权。这些突破使蒋介石及其政府得以调动全国的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抵抗日本侵略,得以在1937年11月淞沪战役后将其政治中心和军队从华东迁至西南地区,得以在盟国对日作战中构成最重要的力量,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为数约四百万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了约五十万或更多的日本军队,否则这些日军会被派遣到其他地方”(Mitter 2013:379)。假如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于国民党统一全国、蒋介石巩固其国家领袖地位之前的话,中华民国的生存机会将会很渺茫。
事实上,国民党国家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最终在二战结束时战胜了日本,更奇迹般地和美国、苏联和英国一起,成为1943年开罗会议的四巨头之一,决定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形成,后来在1945年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关于国民政府重建中国国际关系的成就,见Kirby 1997。尽管盟军的进攻直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但中国能够经受住历时八年的日本全面侵略战争,且在二战的最后几年对盟军打败日军做出巨大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抗战前后国民党的建国努力。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地方势力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那些来自广西、云南和四川的军队,他们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已被完全纳入蒋的党国体系;与此相反,他们一直遭到蒋的怀疑并被部署到抗战前线,往往比蒋的嫡系部队承受更多伤亡。尽管如此,这些地方领导人还是主动从遥远的南部或西南省份派遣了自己最优良的部队到华东和华中地区,积极参加徐州、武汉和长沙等最重要的战役(例见LZR:504—505)。他们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更多的是出于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动机,这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个人或地方利益的盘算。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成为共同的基础,使多年来冲突不断的中央和地方力量走到一起,为了抗日这一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归根到底,一个凝聚所有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国民党多年来的建国努力和地方领导人致力民族生存的共同结果;而他们能够做到共赴国难,也是基于各自的合法性需求,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已经在政治话语中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同样清楚的是,国民党的国家建设远没有取得切实的成功。而制约国民党建国成败的关键,则在体现于其财政构造、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认同上的“半集中主义”特征。这种半集中主义,是此前曾构成广东国民党区域性政权之最大优势的“集中化地方主义”在全国的放大、稀释和扭曲。就财政构造和收支总量而言,在1928年以前,宋子文在广东打造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体系,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每年产生8000万至9000万银元的年收入,如果加上公债,在1927年更达到近1.5亿银元,使国民党政权的财力在全国各支地方势力中首屈一指,为其军事上统一全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权既没有能力把广东模式移植到已经被中央控制的邻近各省,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体系。因此,南京政府的财政增收,不得不靠海关税、统税、盐税等间接税和发行公债等相对简便的途径,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跟不上一个全国性政权的开支需求,特别是事业性机构和公务员队伍的急剧扩大所带来的非军事性开支的膨胀(详见下一章),结果反过来制约了军事开支的增长。直至1935年,南京政府的军务费仅为3.6亿银元,相当于1927年的2.76倍(杨荫溥1985:70)。军费的不足使得蒋介石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统一,从而将中央对各级地方政权的直接控制推广至全国。
在组织结构和政治认同方面,1927年以前,国民党内部的相对团结,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衷共济,以及反帝反军阀的政治宣传,曾经使国民革命军成为一支士气旺盛、所向披靡的部队。但是1928年定都南京之后,蒋介石政权在追求党内政治统一方面困难重重,更无力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高度统一集中的行政管理体系。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蒋介石一直面临着来自粤籍国民党高层的持续挑战和抗拒;在权力中心之外,蒋介石还要应对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虽然宣称忠诚于国民政府,承认蒋介石的国家领导地位,但不管是在抗战前还是抗战后,依然与南京政府离心离德。在思想层面上,国民党虽然成功建立了三民主义的正统地位,取代了民初的共和主义,但三民主义本身缺乏严密的理论建构,容易被挑战国民党国家的各种势力进行不同解读和操纵。蒋介石因此不得不转向国家主义,要求将国家目标和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甚至引入法西斯主义,以聚集人气支持其独裁,同时依靠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以及法西斯组织(最出名的是蓝衣社)来增强自己的力量(Eastman 1974:31—84)。由于缺乏基于共同理念和使命的政治认同,蒋介石不得不依靠传统的人际关系和小团体的忠诚来进行统治,以暴力和恐怖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正如张治中所陈,执政后的国民党,“以派系意识代替党之组织关系,使以主义为中心、以革命为任务之党,变为以派系甚至以个人为中心之党。党员不为革命入党,而以私人权力入党,使有志气有革命性之人士,咸望望焉去之”(ZZZ:252—253)。
国民党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也是浅尝辄止。1930年前后,国民党曾在所控制的地区展开乡镇自治运动。自治的核心是重新组织基层政权,以区和乡取代北洋时期的警区和自然村,乡进一步分为闾(平均25户)和邻(平均5户);乡长由村民选举产生。与清朝和民国初期相比,国民党政权的行政触角的确更深地进入到乡村基层。以“黑地”调查为例,依靠乡、闾、邻组织的发动和基层行政人员举报,国民党地方政权得以掌握大量曾被长期隐瞒的土地,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北洋时期的历次清查黑地举措。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宣传也成功地渗透到乡村地区,确立了其在地方精英中的话语霸权(H.Li 2005)。然而,由于没有触动乡村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土地所有制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重组往往流于形式。基于血缘、邻里关系的社区传统纽带,或基于自卫、治水、宗教仪式等集体活动的跨村社会网络,继续支配着农民的社会空间和村庄社区的自治机制。大多数村民仍主要以其家族、村落或邻近区域,而非以整个民族或国家,来界定自己的认同。国民党政权依然无力动员农村人口参与国家建设,更无意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纲。张治中在检讨国民党执政后的乡村政策时,即曾抱怨,“对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农民问题,亦即土地问题,在此二十年间,理应加以解决,但非不能为而根本忽略而不为,致坐失最大多数之群众基础”(ZZZ:253)。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国民党一直专注于击败地方军阀和共产党军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认真进行乡村重组,展开土地改革,从而有效地控制农村社会和财政资源。结果,田赋的征收和使用只好归省级和地方当局手中,而这本可能成为中央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的财政体制走向崩溃从而导致战场上败北,与此不无关联。
概而言之,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前十余年的建国努力,使南京国民政府比晚清和民初国家政权都更具财政军事实力,更有条件终结19世纪后期以来的国家权力非集中化趋势。不过,国民党国家只是在其上层的正式结构方面实现了相当程度的集中化;这种集中主义是不完全的,蒋介石未能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控制方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治国家,也无法在其追随者和支持者中打造高度的政治认同,更没有动员社会底层资源的能力。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全国领袖地位,国民党政权之所以显示出非同寻常的韧性,更多地有赖各党各派在民族危急关头所自发形成的共同御敌的使命感,而非国家政权本身的统一和集权。当时各支政治力量之间所展示的团结,更多的是一种表象或暂时现象,而非可以持久的实际状况。事实上,在1940年代初,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已存在严重的分歧,导致汪精卫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另一个亲日的伪国民政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也日益严重,抗战后期更是摩擦不断。1945年日本投降后,民族危机一旦解除,地方势力与中央合作的基础也随之消失,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将遭到来自各方异己力量特别是共产党的挑战,国民党国家的生存也将成问题。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为何国民党势力胜出?
清末财政、军事能力的下移和私人化,持续至民国初年,导致国内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军阀混战。国民党势力的最终胜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无可匹敌的财政能力。
——编者按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广东的情况,这个南部省份的经济繁荣和政府税收仅次于江苏。孙中山于1917年8月起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1921年4月后任民国“非常大总统”,影响力仅及广东和广西。他努力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消除军阀和统一中国,但在1925年3月去世前,这种努力屡次失败。不过,仅仅在他去世一年后,国民革命军便开始北伐,并且出人意料地,仅用十个月不到的时间,即打败了长江中下游的军阀,进一步北上清除了关内的奉系势力,于1928年6月推翻北京政府。1928年12月,东北军阀张学良(1901—2001)宣告易帜,服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国民革命军不同于军阀武装的地方,在其受苏俄的影响,用政党加强军队的凝聚力,以党代表制消除军阀式的自行其是,避免军权分裂,同时注重以反帝、反军阀的意识形态灌输士兵,力图克服下级对上级的私人忠诚,使部队成为所谓“党军”(McCord 1993:313—315)。但国民革命军能够在北伐中一路取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无可匹敌的财政实力。其财力的发展分三个重要步骤。第一步,当然是在广东建立一个牢固的财政—军事政权,使国民党势力得以发动北伐,并在数月内占领华南的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第二步,是在占领上海后与江浙财阀结盟,使国民党有可能通过不断出售公债来迅速增加财政收入,为国民党持续北伐提供补给。第三步,是在1928年12月统一全国后,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并很快使关税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源(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约占其全部岁入的60%)。
广东与北伐
孙中山在广东屡遭失败,部分原因在其过于依赖军阀势力,而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先是寻求广西军阀的支持,然而后者在控制了军政府之后,反而把他架空;后来他又转向军阀陈炯明(1878—1933),结果陈坚决反对他的北伐主张,只想在当地经营地盘。孙还曾于1922年末试图联合奉系来打击直系,后来又在冯玉祥于1924年10月打败军阀吴佩孚并结束直系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之后,试图与冯联盟。正是在接受冯玉祥和其他强人的邀请、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而赶赴北京的途中,孙中山过世了,给自己的追随者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
然而,导致孙失败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其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财政收入,而这又与1920年代初广东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有关。1923年2月,孙在广西和云南军队的帮助下打败陈炯明,回到广州,发现自己的命令只在广州一地有效;广东的其他部分要么在陈的余部控制之下,要么在云南、广西、湖南甚至远至河南的军队手中。结果,他的政府在1924年上半年只征收到460万元的税款,多半是通过商人包税获得的,而财政部长们也因为在增加税收上的巨大困难,一个接一个地辞职。孙的军事建设的转折点之一,是1923年5月后获得来自苏俄的财政援助和军事供应,包括1924年200万卢布的贷款,1925年价值280万卢布和1926年至少284万卢布的各种援助(朱洪2007)。苏俄的援助,使孙有能力在1924年5月创立黄埔军校,部署新组建的部队,包括军校学生,于1925年2月和10月先后展开两次“东征”,最终击败了陈炯明和其他军阀势力,将全省置于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之下。
统一广东之后,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收入逐年激增。例如,在1925年,随着国民党迅速扩大对该省的控制,其税收从上半年的大约400万元增至下半年的1220万元,全年税收超过1600万元,是1924年水平(860万元)的近两倍。在接下来的两年,国民党在广东的财政收入,增长更为显著,1926年为6900万元,1927年达9650万元,是1924年的十倍多,也是清末数年广东省岁入(3740万两)的2.4倍(秦庆钧1982)。一两白银在1910年相当于1.09银元。不过,全省的统一,并非国民党财政收入暴涨的唯一原因。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宋子文(1894—1971)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措施。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925年9月担任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他所实行的措施可以分成以下几类(MGDA,4:1400—1404;秦庆钧1982):
(1)政府财政收支的集中化,例如:
●从驻守各地的部队手中接管征税权;
●终止商人包税;
●禁止各军政机构截留税款;
●向新占领区域派员建立地方财政机构,直接对省政府负责。
(2)征税机构的科层化,例如:
●将现有的各自为政的印花税、赌博税、禁烟税征收机关,归财政部统一管理;
●在财政部内建立统计部,以增强会计和审计能力;
●建立一个全省范围内的武装来稽查商品走私;
●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招聘财政部公务员,并惩罚官员的腐败行为。
(3)税收主要来源的整顿,例如:
●调整印花销售渠道,对酒精和鞭炮征收印花税,并对所有商品的印花使用加以标准化(1926年的印花税年度收入,因此从原来的60万元增加到304万元);
●对煤油征收特别税(在1926年下半年创造了200万元收入);
●调查沿海的沙地并征税(结果年度增额超过100万元);
●通过禁止走私,垄断鸦片销售(结果该项来源的半年收入从1925年的200万元增至次年的900万余元);
●调查并审计对所有国内货物的厘金征收,1926年1月增加税率20%,次月再增加30%(该项来源的年度收入因此在1926年增加了两倍,达到近1600万元);
●对所有货物征收“国内税”,普通商品税率为2.5%,奢侈品税率为5%(始于1926年底,每年约征收500万元);
●发售公债(到1926年9月总额达2428万元),以取代过去靠中央银行发行大额纸币,从而保障了银行信用,也避免了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这些措施汇聚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集权的、有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能够充分调动全省的财政资源(该省的经济繁荣程度仅次于江苏,而在国内和对外贸易上甚至比后者更发达)。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结果令人惊讶。自从宋担任财政部长,仅仅两年时间,广东省的年度税收增加了十多倍,到1927年已超过9000万元。相较于参与武力竞争的国内其他各派势力,国民党的财力是最雄厚的。
多年以来,奉系曾独占鳌头,1920年代中期满洲三省的年度财政收入超过2700万元,使其在所有军阀势力中最具竞争力,在1924年打败直系并控制北京政府以后,在华北已无任何对手。但是国民党势力在广东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局势,而支撑国民党势力迅速崛起的,则是宋子文所推动和建立的一个高度集中且富有效率的财政机器,调动了该省的财政资源,并使其发挥到极致。
宋在广东的财政手段是强硬的。厘金和杂税,作为该省的最大财源,覆盖了几乎所有种类的商品和服务,且税率之高前所未见。1925年以后统治广西、后来加入北伐的李宗仁,因此如实地把宋在广东的措施描绘为“竭泽而渔”“横征暴敛”(李宗仁1995:251)。然而,宋的政策的确奏效。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充足收入,为国民党军队在1926年北伐并在战场上迅速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撑。根据宋子文的一份财政状况报告,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达8020万元,其开支也增至7830万元,其中6130万元(占78.3%)用于军事。直到1926年11月,当国民党势力完全占据湖南、江西、福建和湖北省,并准备挺进河南和长江下游区域时,广东省依然是国民党势力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在北伐进入河南、浙江和江苏之后,每月的军事和战争开支增加了730万元(MGDA,1.1:518)。宋因此得意地声称,“惟历来革命根据地惟有广东一省,以一省而供给中国全国革命之需用。最近纵横中原,北伐经费,全赖广东”(吴景平1992:43)。无疑,北伐的成功与各种因素有关,包括国民党军队高涨的士气和严格的纪律以及民众的支持,还有来自广西的军队和来自西北的冯玉祥部队的合作,另一方面,也由于长江中下游的军阀们之间缺乏协调。但是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保持战力并获得胜利,关键在于其兵力的迅速扩充(从北伐开始时的13万人迅速发展到1927年初的55万人),武器和弹药的充足供应,以及对士兵们的慷慨津贴(曾宪林等1991:73,197);如果没有来自广东省的无可匹敌的财政收入,至1927年初一直在支撑着国民党军队,所有这些均不可能发生。
武汉国民政府之困境
国民党军队在1926年末对湖北的控制,更重要的是1927年3月对上海的占领,改变了供应北伐的路径。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不久,湖北便取代广东成为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看来,在支撑了一年的北伐之后,广东已是“孔需亟矣,罗掘俱穷”;因此,让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其他各省与广东一起共同分担财政负担,势在必行(吴景平1992:43,61)。由于广东不再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在占领区实现财政统一之前,其他省又不愿意贡献其财政收入,所以武汉国民政府只能靠湖北一省作为其税收的主要来源。为了扩大政府收入,宋在湖北尝试了许多曾在广东成功的措施。不幸的是,湖北的情况相当不同。在经受了不同军阀派系之间十余年的连年混战之后,该省的经济已经凋敝不堪,有待恢复;因此,尽管在湖北施行了与广东相近的措施,武汉国民政府在1926年9月到1927年9月间,只能从各种税收中获得约1900万元的财政收入(贾士毅1932:114—116),仅相当于广东政府在1926年9月以前通过征税所获岁入的34%(同上:112)。结果,武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发行公债、向银行借款、印刷纸币作为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同期财政收入总额的84.5%)。
然而,在牢固控制该省之前,武汉国民政府很难获得当地商业和金融精英的合作。由于跟南京的国民党势力关系趋于紧张,并遭到后者的贸易禁运,其财政更加吃紧。武汉政府因此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禁止现金流出武汉,市面上只许使用武汉政府印制的纸币。但这些举措只会疏离本地商业精英,引发通货膨胀,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MGDA,4:1485—1486;杨天石1996:420—427)。在丧失了财政信用之后,武汉政府要通过发行公债或印刷纸币来筹集资金,则越发困难;它很快便放弃了与华北军阀和长江下游国民党势力的竞争。
北伐之推进
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裂痕,早在北伐之前便已显现。大体来说,左派聚集在汪精卫(1883—1944)周围。汪在1925年7月出任广东国民政府首脑,1927年4月旅法归来后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坚持在其政府和军队中跟共产党合作。而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则反对共产党的激进主义和国共统一战线。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北伐期间逐渐加剧,并在1927年3月占领上海之后,发展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公开对抗。蒋对自己所控制的城市中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清洗。1927年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蒋在国民党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左派,于1928年1月恢复了总司令的职位,并在三个月之后重新开始北伐。
蒋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蒋出生于浙江,曾于1920—1921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过经纪人,该交易所由曾做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1867—1945)经营;这些背景对他与那些多来自浙江的上海财阀们建立联系非常关键。为了与蒋合作,虞很快于1927年3月创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以取代曾经支持过军阀孙传芳的组织紊乱的上海总商会,并表示他对蒋的国民党军队的公开支持。蒋抵达上海后,便采取行动清除共产党,逮捕和杀害了上百人。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两天之后,蒋正式成立苏沪财政委员会,其中15名成员中有10位系来自上海和江苏的商业和金融领袖,并由上海银行联合会主席陈光甫(1881—1976)任主任委员,其主要职责便是为国民政府筹集资金。作为交换,蒋允许该委员会在任命和管理国民政府的所有财政机构上有完全的自主权(吴景平1992:58—59)。委员会的第一个举措,是在1927年4月向蒋介石提供两笔短期贷款,均为300万元贷款(SSL:57—59)。更大的一项举措,是支持国民政府在1927年5月发行30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今后通过提高海关税率2.5%所获得的额外收入作为担保;并为此设立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多为来自江浙的商业领袖,来管理通过发行国债募集的资金(SSL:74—75)。1927年10月,国民政府又发行了2400万元国债,仍以海关税新增收入作为担保(MGDA,5.1.1:521—522)。
然而,销售如此巨额的国债,对蒋和购买者都是一项巨大挑战。对蒋来说,出售公债,及时募集足够的资金,“军政党务之命脉全在于此”;要维持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巩固对江浙的军事控制,都急需大量资金。为此,蒋在1927年5月写信求助于陈光甫:“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指出售政府公债)。”(SSL:110)而银行家和企业主们则试图以各种借口减少或拖延购买被分摊的公债。因此,蒋不断采取强制性措施。例如,面对公债出售进展缓慢的局势,他强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预付1000万元以满足军事开销的紧急需求;对曾为武汉国民政府提供资金的该分行经理,以“阻碍革命”和“有意附逆”的罪名相威胁(王正华2002:105)。对于那些未按要求购买足够公债的企业主,他下令逮捕企业主本人或其家人,还以其曾资助军阀的反革命活动为借口将其财产充公(Coble 1986:32—35)。这些胁迫手段对于他榨取想要的资金只能一时有效,不能成为其筹措资金的常规办法。因此,当1927年10月销售另一笔4000万元公债时,因购买系自愿行为,进展极为缓慢。身陷与武汉国民政府旷日持久的对抗,加上北伐部队出师不利,在徐州被北方军阀击败,不得不撤退到长江南部,蒋只好在1927年8月暂时辞去总司令职位,让武汉和南京之间有时间进行和解,也使自己有时间重新建立起与上海财阀之间的私人联系(同上:32—35)。
不出众人所料,蒋在1928年1月重新上台,此时的局面已大为改观:武汉国民政府成员已前往南京,加入那里的国民政府,蒋本人也于1927年12月与宋美龄完婚,成为宋子文的妹夫,最重要的是,宋子文在蒋恢复总司令职位之前,便已接受了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职位。有了宋的帮助,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在1928年迅速改善。自出任财政部长六个月之后,通过银行贷款、出售公债以及征税,宋子文为国民政府筹集资金计达1.9亿元!(MGDA,5.1.1:520—521)这笔巨额资金使得蒋可以再度北伐,并于1928年4月在北方各省对奉系发动全面攻势。在战争高潮期间,宋被要求每5天提供160万元。事实上,他做到了,而且所筹集的资金远多于规定数额(贾士毅1932:216)。
国民革命军于6月占领北京,北伐至此达到顶峰。南京国民政府因此于1928年1月15日正式宣告全国统一。然而,这更多地是反映了国民党的政治决心,而非国家的现实,因为奉系虽从北京撤退,却仍控制着东北三省。要挺进满洲的广大地区,击败奉系军队,这将是国民党人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幸运的是,曾抵制日本迫切要求控制满洲的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死于日本关东军所策划的爆炸中,其子张学良成为奉系的新领袖,于1928年12月29日正式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全国各省由此正式统一于蒋介石麾下。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