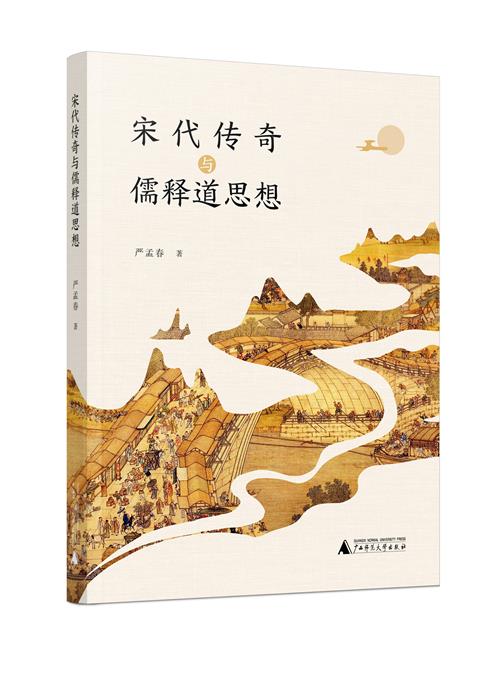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1-01-01
定 价:48.00
作 者:严孟春 著
责 编:郭春艳
图书分类: 文化评述
读者对象: 高校学生,古代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宋代传奇研究者和爱好者。
上架建议: 古代文学研究·宋代传奇
开本: 32
字数: 260 (千字)
页数: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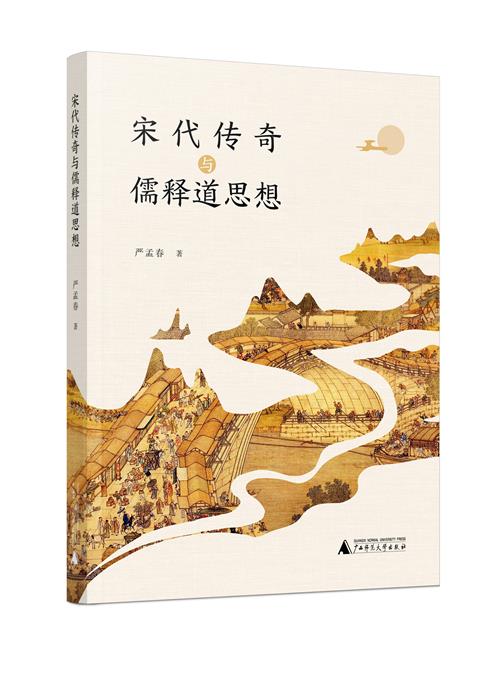
本书从宋代传奇的题材内容、主题表达、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以及重要意象等五个方面入手,分别探讨宋代传奇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道教思想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宋代传奇的关注与研究,我们既可以很好地认识宋代传奇这一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使有关的文学史(宋代文学史或文言小说史等)面貌更全面、更清晰;同时也可以很好地认识宋代文化的特质,知其博大精深,知其涵育醇厚,知其影响广泛而持久。
严孟春,江苏镇江人,文学博士。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海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编辑出版学研究。曾荣获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编辑奖、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编辑学论文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征文金奖等奖项。已在《出版参考》《江淮论坛》《海南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绪 论
第一章 宋代传奇及其文化学意义
第一节 宋代的传奇
第二节 观察宋代思想文化的一扇窗口
第二章 宋代传奇与儒学
第一节 社会伦理题材及历史题材选择的思想背景
第二节 阐“道”述“理”的主题
第三节 平淡无奇的“传奇”叙事
第四节 节妇、义士和忠臣、孝子
第五节 书剑恩仇——与儒学相关的小说意象
第三章 宋代传奇与佛教
第一节 佛教:宋人绕不开的创作领域
第二节 因果报应和劝善惩恶
第三节 佛教与传奇情节的异型建构
第四节 僧尼众生相
第五节 佛教意象:莲花与梦
第四章 宋代传奇与道家、道教
第一节 宋代的道家、道教和传奇小说中的道家、道教题材
第二节 超越世俗的追求
第三节 幻设为文,糅合佛道
第四节 神鬼·仙妖·道士
第五节 山·洞·药·酒
余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序
孟春是我的博士生,她本来不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但她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2014年她第一次参加博士生招生的考试,就一举成功,而且分数很高。
孟春入学以后,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有悟性,是读书的好料子。虽然她硕士的专业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她在复习考试阶段,就已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有关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很快就入了门,有了强烈的专业感。入学后,角色转换迅速,按照我的要求及课程的安排,她读了不少专业著作。这些著作,特别是一些原著,是有较大难度的,但她读得很专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肯动脑,勤于思考,不是死读书。所以,没有多久就写出了一篇学术论文,就陆游《钗头凤》中的“红酥手”提出新解,认为“红酥实指唐宋时期贵族妇女们制作的一种果品兼工艺品,因此,陆游所谓红酥手乃是赞许唐琬有一双点制红酥的巧手,是词人借以即景抒怀、回望从前的重要意象”。虽然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可见孟春读书的细心、敏锐以及不肯人云亦云的精神。二是勤奋,肯用功。孟春早已成家,但为了读好书,她抛开繁杂的家事,按照学校的要求,克服了许多困难,到桂林扎实地待了两年时间,完全脱产学习。她常说自己专业基础差,需加倍努力。所以,在这期间,她阅读了大量有关专业书籍。特别是确定了要研究宋代传奇后,对相关资料更是做了全面研究,用功之深,用心之细,令人赞叹。三是对人厚道诚恳。孟春待人之诚,不仅表现在对我,而且也表现在对其他老师及同学上。除了每逢节日的问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她经常帮助他人。今年上半年,教研室的多位老师到海南参加集体活动,孟春竭诚款待,令老师们大受感动,回来后交口称赞。孟春家有年迈多病的婆婆,孟春极尽孝心,倾心相待,付出了大量精力。由此可见孟春的人品。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工作又有变化,家务也需操心,短短三年之间,孟春头上竟然有了少许白发!令人感慨,也令人心疼!
孟春早早就选定了宋代传奇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撰成《宋代专奇与儒释道思想》,并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再经修改后,拟正式出版,邀我为之作序。我于宋代传奇素无研究,但孟春是我学生,考虑再三,于是欣然从命。
传奇的研究,历来不是唐宋文学研究的重点,虽非显学,但是仍有不少学者涉足,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唐宋传奇的各个方面都已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孟春选择传奇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我是暗中捏一把汗的。孟春是那种有主见、有行动,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既然她选定这一方向,一定有她的理由,也肯定有充分的把握。于是开题时,就以此为题,正式确定了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
孟春研究传奇,没有选择已研究得比较充分的唐传奇,而是选择了研究相对薄弱的宋传奇。这是她的一个明智选择,这样,她研究的空间就相对大得多,而且也可以发挥她长于细读、心思细密的特点。
宋代传奇作品看起来似乎数量不多,但同样也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从什么角度来进行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空间与观点。孟春选择的是宋代传奇与宋代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研究。这应当说是宋代传奇研究中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因为在此之前虽有这方面的相关成果,但多为个别的、零星的,很少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孟春由此切入,研究的空间也比较大。
孟春从宋代传奇的题材内容、主题表达、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以及重要意象等五个方面入手,分别探讨了宋代传奇与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宋代传奇与佛教思想、宋代传奇与道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论述宋代传奇与儒学时,就分别从社会伦理及历史题材的选择,阐“道”述“理”的主题,平淡无奇的“传奇”叙事,节妇、义士和忠臣、孝子,书剑恩仇的意象等进行分述。这就抓住了儒家思想影响宋代传奇的主要问题。再如论述宋代传奇与佛教,孟春是从创作题材,因果报应和善恶劝惩,传奇情节的异型建构,僧尼众生相,莲花与梦的特殊意象等来阐述佛教对宋传奇的影响,也是纲举目张,抓住了重点。之所以主要从这五个方面入手,是基于孟春对传奇的认识。她认为,“传奇之所以为奇,奇就奇在它的故事、它的情节、它的人物,还有它的细节”。抓住“奇”字做文章,这是孟春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果孤立地研究宋传奇,就无法凸显其特点,也影响研究的深度。孟春深知这一点,所以,她在研究宋传奇时,常常将其放在某种关系中、联系中去考察。将宋传奇的主要特点与儒、释、道联系在一起,这本来就是建立起一种关联,避免研究的孤立。除此之外,例如,孟春在谈到宋传奇的某一特点时,常常要追溯一下这一特点在前代文学中的表现,这就将宋代传奇与历史上的此类特点联系在一起了。如第四章《宋代传奇与道教》第四节《神鬼·仙妖·道士》一节中,先追溯前人的艺术积累,从庄子、屈原,再到唐传奇,然后再论述宋传奇中的神鬼仙妖,由此也就清楚地梳理出了宋传奇中神鬼仙妖与前代的联系与区别。再如,孟春常将宋传奇与唐传奇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比较,以此来突出宋传奇区别于唐传奇的特点。在《宋代传奇与儒学》一章中谈到宋传奇平淡无奇的“传奇”叙事时,先引用唐传奇《虬髯客传》为例,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此来说明“唐代传奇的艺术优长就是情节叙写的奇特曲折、宛转详尽,令人有惊奇之感”。在此之后,再申说“宋代传奇虽也忝称传奇,然而其中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奇’,宋代传奇总体上给人以一种平淡的感觉”。认为宋代传奇作家“把心思放在了作品的‘思想’经营而不是‘艺术’经营上。……他们很在意在传奇中向人们传递了哪些知识、学问,或讲说了哪些思想与道理,以此显示写作的意义。由此导致艺术性的缺失,使作品‘味儿’不足,传奇不再‘奇’,而是趋于平淡”。两相比较,各自的特点一目了然。
孟春在研究宋传奇时,常能别具只眼,提出新说。例如论述儒学对宋传奇意象的产生时,特别拈出了“书”这一意象,认为读书是儒家的传统,“书籍成为延续儒家思想文化的纽带,成为儒生、儒士安身立命之本”。在此背景下,书就成了宋传奇中最常见的一个意象,即使作品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渔夫、商贾或者普通妇女,也要写到他们好读诗书,吟诗作对,甚至出现了《书仙传》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眼光、论述,是已有的宋代传奇研究成果中很少见的。书中类似的论述比比皆是。
孟春富于文学气质,书中优美的语言及富有诗意的叙述、精到的分析等,无不显露出这种气质,相信阅读此书的读者不难体会到。
孟春现已毕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希望她以此书作为研究工作的新起点,不断取得新成绩!
王德明
2020年秋于桂林
由于唐传奇的优秀以及宋代文学的丰富,宋代传奇的价值和意义长期以来被忽略。作者大胆地舍弃热门题材,而选择了宋代奇作为写作主体,可谓大胆而又新颖。而本书主要立足于宋代传奇的文学文本来探讨宋代传奇之所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为读者更好地观察宋代文学、宋代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作者一方面通过唐传奇与宋传奇的比较研究,让读者知道,宋代传奇之所以一直不受重视,是因为其叙事方式平淡无奇,过于中规中矩,而且大多兼具教化功能,娱乐性和文学性不足,甚至有时候很难匹配“传奇”二字;另一方面,作者又将宋代传奇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儒释道思想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让读者明白,宋代传奇平平无奇的叙述方式是有它的成长土壤的,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作家们写起故事来自然难以放开手脚。这样的研究和分析,让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可谓非常客观公正了。
那么宋代传奇果真如我们表面所见的这样平平无奇,无一可取之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作者所说,“传奇之所以为奇,奇就奇在它的故事、它的情节、它的人物,还有它的细节”。宋代传奇能被称为“传奇”,自然有它“奇”的一面。撇开叙事方式,宋代传奇在题材内容、形象塑造、主题表达和重要意象等方面,都与唐传奇大不相同。比如对历史题材的偏爱,对贞女节妇、义士孝子的刻画,对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执念,对法术、仙境等超越世俗的意象和意境的描绘,无一不给这些传奇作品打上深深的宋代烙印,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章 宋代传奇与儒学
第五节 书剑恩仇—与儒学相关的小说意象
三、刀光剑影:徘徊在义与法之间
《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清]黎翔风:《管子校注》“牧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在儒家思想文化语境里,礼与义二者并举。从宋代传奇的创作实践来看,表现礼的重要意象之一是音乐,表现义的重要意象之一是刀剑。
前一节说到向拱其人,他因认为与之私通的妇人杀死自己的丈夫是不义,便毅然杀掉了她,并“掷首级于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杀此妇人。’徐徐掉臂而去”。换言之,他把如此行径看作是行侠仗义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却依然以此为荣。在这一“行侠仗义”的行为中,用刀剑砍去“不义者”的头颅是核心情节,乃表现了侠与义的内涵。
何为侠?《韩非子·五蠹》解释说,“以武犯禁”者为侠,是带剑者,和“以文乱法”的儒皆属国之蠹,当除去之。[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五蠹》,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五册),第344页。]当然,这是法家的看法,侠客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除暴安良、抑强扶弱、见义勇为作为人生使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了心中的一点理想、一点信念而甘愿冒杀人的风险,甚至献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刀剑是他们的身份标志,杀人是他们通往正义的途径。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也是边缘人,但由于对社会生活,乃至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侠客们受到某些势力的利用,更受到特定思想的灌输,视其行为义。
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为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春秋战国时期影响了当时政治历史发展进程的著名刺客(侠客)树碑立传,推崇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第520页。],从而赋予了侠客们的刺杀行为以历史的正当性,刀剑意象也由此在文人笔下获得了更广泛、自由的意义,成为行侠仗义的象征物、代名词。
大诗人李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游侠思想的影响,其诗文作品中不时见到刀剑意象、侠客身影。他曾对韩朝宗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唐]李白:《与韩荆州书》,见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6页。]又作《侠客行》等诗歌,表现自己挥剑慕侠的思想:“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唐]李白:《李白诗集新注》,第59页。]据说李白年轻时还曾因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龚自珍评李白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矣。”[ 王济民:《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诗学》,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39页。]可见李白和游侠思想的关系。
唐代诗人中有慕侠尚义之心者不在少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唐传奇,特别是晚唐传奇中,有一些作品写及剑侠题材,或刀剑意象在其中处于突出位置。如《虬髯客传》有一个情节可谓惊心动魄:
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 [唐]杜光庭:《虬髯客传》,见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
刀剑意象在这里即是行侠仗义的化身。
宋代传奇继承唐传奇,也有若干涉及剑侠题材的创作,故事中闪动着刀光剑影。但宋人笔下的刀剑意象和唐人所写是有区别的。同样是用刀剑斩杀“不义之人”,唐传奇赋予了这种行为以完
全的正当性,赞美侠义,歌颂复仇;宋代传奇则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和前人一样,他们肯定侠义、复仇的行为,认为伸张了正义、铲除了不平,是应该有所激励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这种行为触犯了法律,应该受到制裁。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用单一的视角来审视侠客们的杀人行为了。一边是忘恩负义、社会不公需要侠客们展现身手,一边是法律严禁私自杀人,哪怕是“不义之人”。那么怎么办呢?宋代传奇作家有两个处理办法。
一个办法是让侠客们斩杀不义之人,伸张正义,然后亡命天涯,躲过法律的制裁,如前面提到的向拱,再如高言(《高言》)、王寂(《王寂传》)等。向拱“会赦方归”;高言“北走入胡地”,又沦落海外数国多年,“后属仁庙崩,新君即位,有罪者咸得自新”,得以归国;王寂则沦为强盗,“椎牛、椎豕、掠墓、劫民、烧市,取富贵屋财。……视州县若无有,观诏条如等闲”,后遇赦向官府自首。
另一个办法是如《王实传》里所示,让侠客受官府制裁,却享受着“义士”的待遇。孙立受王实之托,杀死恶人张本,“断其颈,破脑取其心,以祭实父墓。乃投刃就公府自陈。太守视其谳,恻然”。有一段对话显示了太守、旁人实际上即作者对于孙立的尊崇态度:
立曰:“杀人立也,固甘死,愿不旁其枝,即立死何恨焉!”
本之子告公府曰:“杀父非立本心,受教于实。”
太守曰:“罪已本死,何及他人也?”
立曰:“诚如太守言,不可详言之也。立虽糜烂狱吏手,终不尽言也。”
太守曰:“真义士也!”召狱吏受之曰:“缓其枷械,可厚具酒馔。”
后日旬余,至太守庭下,立曰:“立无子,适妻孕已八九月矣,女与男不可知也。愿延月余之命,得见妻所诞子,使父子一见归泉下,不望厚意。”
太守乃缓其狱。
可以看出,在法律层面上孙立是罪犯,可在道德层面上,他却被时人视作义士、英雄、大丈夫,为了“正义”之事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难怪孙立“就诛”时,太守要“为之泣下”,观闻者亦“多挥涕”。
由于罪犯和义士兼而有之的双重身份,宋人对侠客之义的评判出现了歧见。或重义轻法如上述人们对孙立杀人事件的态度(太守为了孙立之义而多有枉法之处),又或者重法轻义—在宋代传奇中,这一派意见似乎更占优势—如前述人们对向拱、高言、王寂等杀人事件的态度。人们对向拱、高言、王寂杀人事件的态度大体上是负面的。除了在杀人理由上表现了其正义之外,在杀人后果的安排方面,作者显示了消极的评价。何以知之?向拱在杀人逃罪遇赦后归家,“父忧之,形于颜色”,并对滕公说:“用何术免此子破吾家?”向拱的父亲是“长者,有节行”,他认为儿子侠行是“破家”的行为。后向拱在滕公引导下改邪归正,是为“徙义”。高言杀人后被迫流亡胡地和海外计二十年,“溪行山宿,水伏蒿潜,寒热饥苦,集于一身”,可谓吃尽了苦头,而作者之所以写他的故事,是欲“士君子观之以为戒焉”,“欲其为谨肃端雅之士,不愿其为豪侠也”。王寂杀人后沦为强盗,后主动自首,接受招安,又为黄冠道士所点化。通过对这些侠客结局的安排以及直接评判,宋人表现了新的侠义观。
唐传奇中的侠客很少动刀剑杀人,所见多是排难解纷、义慑他人之类,如黄纻衫豪士胁迫李益面见霍小玉(《霍小玉传》),古押衙设“奇法”令王仙客、刘无双团圆(《无双传》),红线女盗金合震慑军阀田承嗣勿轻举妄动(《红线》),昆仑奴磨勒背负豪家红绡妓飞赴崔宅与其少主崔生相聚(《昆仑奴》),等等。即使有动刀剑杀人的,也只涉侠义不及触法,是纯粹肯定、歌颂的文字。虬髯客追寻十年终杀“天下负心者”,没有人将这件事和犯法联系起来,虬髯客在小说中是完全正面的形象。(《虬髯客传》)魏之豪人冯燕在滑与张婴妻私通,张婴妻要冯燕乘张婴醉且瞑时杀掉张婴,冯燕便杀掉这位不义的妇人,这件事竟感动滑之相国贾耽,“请归其印,以赎燕死”,并得诏:“凡滑城死罪皆免。”作者赞曰:“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冯燕传》)聂隐娘由魏帅转投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并以法术杀死魏帅的刺客精精儿,又击退妙手空空儿的刺杀,也是一个杀人不犯法的女侠客形象。(《聂隐娘》)
唐代侠客空灵、洒脱、神奇,对付不义之人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翻新出奇,反映了传奇作家的创造性;宋代侠客则显得形象呆板、手法单一,除了摘取负义者的项上人头之外,似乎别无他法,令人兴味索然。在具体描写中,宋代侠客的“义行”也缺乏生动细节的支撑。究其原因,一是宋人学唐,在情节乃至细节上亦步亦趋(如《向中令徙义》之于《冯燕传》),缺少创新精神;二是由于中晚唐和宋代在社会风气上有巨大不同,侠客群体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没有了,侠义行为被纳入法的范畴,受到了法的约束。换言之,宋人写侠客行为并不像唐人那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创作中没有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有力支持。
在古代,刀剑除了用于侠客们行侠仗义,还有其他诸多用途,比如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报效君主和国家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李贺:《李贺诗集》,徐传武校点,第40页。]“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宋]辛弃疾:《破阵子》,见唐圭璋编《全宋词》(第三册),第1940页。
]儒家倡导“三不朽”,其中之一便是立功于世,显亲扬名,而在冷兵器时代,刀剑乃是立功扬名的重要工具。可惜宋代传奇作家没有在这一意义上加以挖掘,只把刀剑作为斩杀不义之人的工具,导致作品纠结于侠义和法律之间,无所适从。
后世有两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分别把刀剑意象的上述两种意义发挥到了极致。大体说来,《三国演义》主要发挥了三国人物用刀剑建功立业的意义,《水浒传》则主要发挥了梁山好汉用刀剑行侠仗义的意义,二书的侧重点不同。可以看出,宋人的侠义观对《水浒传》的主题抉择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要表现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另一方面,又要表现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终接受朝廷招安的心迹。梁山好汉们同样徘徊在侠义与法律之间,故而造成了悲剧命运,令后人为之深深地感叹。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