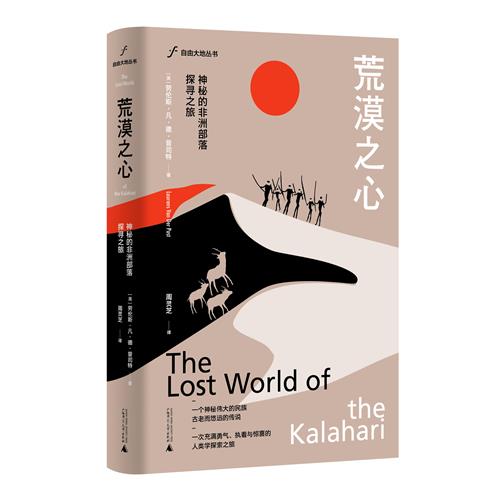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1-03-01
定 价:68.00
作 者:(英)劳伦斯·凡·德·普司特 著 周灵芝 译
责 编:张曼
图书分类: 世界各国文化
读者对象: 非虚构、旅行文学爱好者,人类学研究者,普通大众
上架建议: 文化/世界各国文化
开本: 32
字数: 210 (千字)
页数: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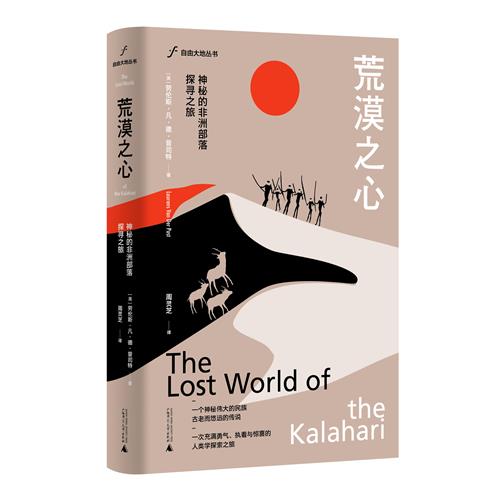
本书记录了一场神秘的非洲部落探寻之旅,对象是荒漠布须曼人。据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早人类形态的代表,能够在狮群中来去自如而毫发无伤;知道如何骗过鸵鸟,使其变成“母鸡”为自己下蛋;更知道如何在荒漠中保存好珍贵的水资源以备不时之需。他们征服了世界上最贫瘠的土地,却在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历史中败下阵来,被所谓“文明人”污蔑为肮脏的野蛮人、无耻的小偷、残忍的野兽而肆意虐杀,终至于行将灭绝。
然而,事实的真相如何?真正的布须曼人到底是怎样的?借由本书,作者带领我们深入荒漠之心,见证真正的布须曼人如何生活、狩猎,由此不仅一一戳破侵略者的谎言,也开启了人类学界研究布须曼人的先河;本书亦因此成为拯救布须曼人免于灭绝命运的伟大著作。
作者简介:
劳伦斯·凡·德·普司特,1906年出生于南非,20世纪著名作家、探险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1934年出版的处女作《在某省》,是第一本出自南非人之手的反种族歧视小说。两本描述沙漠布须曼人的著作《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世界》(1958年)和《猎人之心》(1961年),被世人赞誉为拯救这支神秘种族免于灭绝命运的伟大著作。
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执导、豆瓣高分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又译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即根据他的作品《种子与播种者》(1963年)改编而来。
译者简介:
周灵芝,曾任报社编译,现专职从事翻译及艺术创作。译作有《山高水清:五百天徒步跨欧之旅》《人生的9个学分》《在我道别之前》《迷路的地图》《解放儿童》等。
第一章 消失的民族 1
第二章 消失的方式 41
第三章 誓约与飘荡的年代 65
第四章 大突破 83
第五章 启程前的阴影 103
第六章 踏上北上的征途 127
第七章 失望的沼泽 161
第八章 措迪洛山的神灵 227
第九章 井边的猎人 261
第十章 雨之歌 303
《荒漠之心》导读
看到这本《荒漠之心》时,是2020年金华的深秋,距离我2011年3月在博茨瓦纳西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实地探访南部非洲最早的居民——“布须曼人”[现有的考古研究已证明,早在1万年前,身形瘦小、肤色较浅、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桑人(San)就已经生活在南部非洲,他们是南部非洲最早的居民。桑人又被后来的荷兰殖民者蔑称为“布须曼人”(Bushman,意为丛林人)。本文为了与译著表述统一,也用布须曼人来指称桑人,但不含任何贬义。]已经过去九年了。这九年中,我持续关注博茨瓦纳、南非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先后出版了《博茨瓦纳族群生活与社会变迁》《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两本专著,里面都有对布须曼人的论述,然而直至我看到劳伦斯·凡·德·普司特爵士(Sir Laurens Van Der Post)的这本《荒漠之心》(又译《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世界:伟大和渺小的记忆》),才让我从日常繁重的行政、科研与家庭事务中短暂抽离,回归到一种现实中无法企及的宁静状态,那是一种返回初心的窃喜和满足,这种感觉伴随我走近劳伦斯本人和他在非洲的探险,同他一道找寻人类最本真、最原初的情感以及被人类遗失的灵魂……
劳伦斯爵士1906年12月13日出生于奥兰治河殖民地菲利普波利斯的一个小镇上;卒于1996年12月16日,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为期五天的90岁生日庆祝活动后不久。90载传奇人生,从他令人目不暇接的“南非白人作家、农民、军人、英国政府首脑的政治顾问、查尔斯王子密友、威廉王子教父、教育家、记者、人道主义者、哲学家、探险家和环保主义者”等头衔称谓中就可见一斑。作为家中13个孩子里最小的儿子,他在南非农场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也正是这段农场生活,让他同周边的布须曼人、班图黑人有了亲密深入的接触和互动,并从他身为律师与政治家的父亲的个人图书馆里,阅读、体味到诸如荷马、莎士比亚等欧洲古典哲人、文学家的经典著作,为他日后终身从事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在布隆方丹的格雷学院毕业后,即成为一名记者,亦创办过杂志,出版过小说;他在英国结婚生子,又在南非邂逅激情和矛盾;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于1940年自愿加入英国军队,奔赴了东非的战场,此后又在爪哇、印尼等地执行军事任务,直至1947年从军队退役,劳伦斯结束了七年的军旅生涯,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同年末,他回到南非就职于《纳塔尔日报》,然而随着南非国民党在1948年的胜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正式实施,他又回到了伦敦生活。他始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持批评态度,因为他对于南非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充满了同情和怜爱,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布须曼人和非洲深深吸引他的地方——
他们属于我的家乡,而且比任何其他民族还来得彻底、完全。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的特质与需要,都与这片土地深深吻合。他们的精神很自然地与大自然无比契合,因为在这本能的明确归属感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严格遵守着既定的法则。我从未发现在我们全体来到他们的生长之地、破坏了他们的家园之前,有哪一项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破坏了这些法则。他们的猎捕就像狮子的猎捕般,是无罪的,因为那是为了存活;他们从来不会出于好玩或毫无目的地展开捕猎,即使是为寻找食物而进行猎捕,他们也会很奇怪地为这种行为惴惴不安和懊悔。
非洲像个相当出色但还未实现愿望的野蛮妇人,依旧在物色一个值得的爱人,因此总会以她那高深莫测性格中的各种任性、善变、极端和诡计多端测试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但那些不因此稍减对她的爱的人,将会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平静夜晚,发现他们突然获得了温柔、优雅且毫无保留的回报,甚至超过他们所能理解的。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劳伦斯对布须曼人、对非洲深入骨髓的了解与共情。在先后写出了《内陆冒险》(Venture to the Interior, 1952)、《火旁的脸》(The Face Besides the Fire, 1953)等畅销书后,他于1955年重返卡拉哈里沙漠探访布须曼人,并在BBC支持下,带领一个摄制团队,拍摄了一部关于布须曼人的纪录片。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荒漠之心》,它是劳伦斯最著名的作品,其同名纪录片亦获得了巨大成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被遗忘、被迫害的布须曼人的关注和保护。紧接着,劳伦斯又根据早期人类学家搜集的有关布须曼人的民间传说创作了《猎人之心》(The Heart of the Hunter, 1961)等。
劳伦斯的作品被誉为“捕捉到古老大陆的独特而无法定义的精神,并探索人们心灵的内在”,同时他也在努力指明重新发现人类生活中荒野的积极价值观与路径。随着劳伦斯的讲述,“乔贝”“赞比西河”“马翁”“杭济”“措迪洛”等有关布须曼人的重要景观、地点一一浮现在我眼前,也把我带回了探访布须曼人的过往岁月中……
作为南非最早居民的布须曼人,在与荷兰人相遇之前,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游牧生活,他们不使用金属工具也不种植庄稼,更不会饲养牲畜。他们使用的工具器皿都由木头、骨头、石头制成,日常所需也都来自大自然,因此其如何合理利用自然的知识十分丰富,所有的自然资源均由大家共同享有。布须曼人以15—25人的小规模群体追逐食物与水源过着频繁流动的生活,成员之间关系平等,没有发展出制度化的权威,祈雨者和仪式专家们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大自然中的洞穴岩壁成了布须曼人的临时避风港,亦成了他们记录日常生活、人生重要时刻以及抒发情感的天然画板。他们用黄土、片麻岩等有色矿石磨成粉末,再混入取自植物根茎的汁液或将其与动物血、内脏里的黏液一起搅拌,制成粘附性极强又不易褪色的颜料。布须曼人用的“画笔”有时是羽毛,有时是兽骨,有时也会把木棍一端磨尖了作为画笔。在南非很多地区,特别是德拉肯斯堡山(Drakensberg,又称龙山)一带的山洞里和悬崖上留下了大量丰富的岩画,展现了他们的信仰、仪式与生活。
这样一个古老族群,在后来与其他非洲人、白人族群相遇时,却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人口锐减、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他们被抓去打仗、做奴隶,过着卑微而屈辱的生活。直至劳伦斯的作品和纪录片问世,才让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现代人和当时南非的殖民政府反思并关注那些身处边缘和弱势地位却保存延续着人类古老文化基因与密码的原住民,他们代表着全人类“失落的灵魂”。这些关于布须曼的记叙和影像促使殖民政府在1961年建立了中央卡拉哈里野生动物保护区,来保证他们的生存。在1966年博茨瓦纳独立时,这个保护区亦成为国家法律所固定保护的一部分。然而,1970年南非通过的一项法律却使得布须曼人失去90%的狩猎土地;时至今日,南非境内的布须曼人已经没有可以狩猎采集的土地。[The website of 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The San”, accessed Dec 11, 2018.]
失去土地的布须曼人靠什么生活呢?2011年3月初,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一个名叫罗伯特的有色人种导游的陪同下,我和几位中国朋友驱车800多公里前往布须曼人聚居的小镇——杭济。罗伯特告诉我,他会说七种语言,曾经跟布须曼人一起生活了八年,所以他会说布须曼人的独特语言,我试图努力模仿,却总是失败。据说,这种发声方法产生于人类的发音器官还没有完全形成之时,因此,布须曼人的语言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语言之一。在罗伯特指引下,我们来到一家白人开的度假村,行进在村附近的灌木丛中没多久,眼前就出现了男女老少六七个布须曼人,他们几乎全身赤裸,男人穿着兽皮短裤,女人有的赤裸上身,有的披着兽皮。男人背着兽皮口袋,里面插着狩猎用的弓箭,一个稍显年老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浑身赤裸的婴儿,婴儿眨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我们,咬着妈妈的乳头使劲吃奶。
队伍中的一个年轻女人很热情地跟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一边问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一边能马上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让人啧啧称奇。与此同时,一旁的布须曼老人在地里使劲儿地挖着,不一会儿就挖出一颗根茎类植物,他高举着这个植物大声用布须曼语喊着。罗伯特给我们翻译说:“这个植物首先是一种染料,可以把布须曼人的身体染成黄褐色透着红色;其次它有避孕的功效,女人每3个星期吃一次,可以避孕。”紧接着,这个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向我们展示了布须曼人特有的生存技能与文化:一个布须曼少女手举一种草药,告诉我们这种草药专治关节痛;一个妇女展示了大啖白蚁的本事,屁股圆鼓鼓的白蚁是布须曼人在沙漠中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她嚼得津津有味、嘎嘣作响;一个布须曼小伙子展示了如何猎杀动物,箭身与箭头分离,他在箭头上涂上麻醉药,射中猎物后,箭头留在动物体内,随着动物逃跑,会慢慢被麻醉;而最开始在土里挖出根茎的老人据说是当下最好的猎人,他可以连续追踪猎物7公里,直到猎物昏迷倒下。很多人出去几天都打不到猎物,这个老人却总能满载而归。因此,在布须曼人社会里,最好的猎人也是最容易娶到老婆的人。布须曼人的葬礼也很有趣,他们会把死者抱成一个团,直接放进挖好的坑里埋掉……人出生之前就是在妈妈肚子里抱成一团,死了依然是抱成一团回归到土地里。
紧接着,布须曼人又向我们演示了钻木取火,拿一根木棍压在一堆干草上,一个年轻小伙用另一根木棍对准下面木棍上的洞,使劲揉搓,一会儿功夫便有一缕青烟从孔中冒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兴奋,这时那位老人再次出手,他双手紧握木棍搓了几下,烟就大起来,他捧起干草,放在嘴边吹气,越吹烟越大,接着就冒起火来,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人类在野外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生起一堆火总是一件令人很兴奋和欣慰的事情。
回到营地,布须曼人将一张兽皮铺在地上,示意大家可以给他们付小费了,我给了背着孩子的女人50普拉,其他人觉得不公平,用英语说着,他们没有拿到钱……我只好再给每人一些小费,他们开心地数着钱。罗伯特说,他们拿到钱就去买酒喝,白人教会了他们抽烟喝酒,他们现在除了依靠展演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赚钱,也没有别的生存技能了,多数人靠政府的救济金维持温饱。
在杭济镇区布须曼人聚居的棚户区里,有人闲散地坐在路边抽烟,也有几个醉汉东倒西歪地在路边晃。我突然发现了那些“表演的布须曼人”,他们兴奋地跑过来要烟,但我们没有。接着,我又遇到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她现在已完全不是早上的赤裸模样,她穿着现代的衬衫裤子,扎着头巾,一边吃着薯条,一边说她用我们给她的钱给孩子买了一条短裤,还拍拍孩子的屁股,我们感到一丝欣慰,给小孩买短裤好过他们去抽烟喝酒。
很难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上午这些布须曼人赤身裸体地“表演”他们的传统文化,下午便衣着光鲜地在街边抽烟、吃薯条,这种反差实在强烈。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法再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博茨瓦纳政府因为在沙漠中发现了钻石矿而不断驱逐他们,让他们放弃古老的狩猎生活,定居在城镇周边,还给他们建了房子、给生活补贴,让他们过上现代人的城市生活。然而多数布须曼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他们不具备在城市里生活的技能,他们的孩子也很难适应现代学校教育。老一辈布须曼人仍然可以本色地“表演”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让游客信以为真。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当定居在城市里的年轻人长大以后,是否能保留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呢?
劳伦斯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布须曼人的观察与书写引发了学术界对布须曼人的研究与保护,布须曼人研究亦成为20世纪末期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主题。人类学家们担心他们的狩猎采集文化和生活方式能否幸存到20世纪。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在我2011年去博茨瓦纳探访布须曼人时,就只能看到“表演的布须曼人”,年轻一代正在丧失他们在沙漠中生存的技能,并逐渐被现代城市所吞噬和遗忘。
南非的布须曼人境遇如何呢?我在2017年4月专门探访了位于北开普省的普莱特方敦的布须曼人社区,这是一个鲜活展现非洲原住民从“流离失所”到“定居成为当地人”的案例。[参见拙作《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版。]直至1994年新南非成立之时,人们仍普遍认为南非布须曼人是一个“垂死的种族”[A Barnard, Hunters and Herders of Southern Africa: A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of the Khoisan Peo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因为他们在与班图黑人、欧洲殖民者的接触、对抗、融合中,逐渐被同化甚至“异化”,他们不仅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其身份认同亦随着殖民者不同时期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们的基因融进了不同的种族和族群中,特别是有三百万之众的有色人。
为了修正过去300多年来以白人为核心的历史,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布须曼人的地位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布须曼人的身份不再与原始和落后联系在一起,而是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重新建构。首先,布须曼人代表们开始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共同体,或南非文化独特而统一的构成。正如南非国徽上盾牌图案下方的口号——“不同人团结起来”,是用一种布须曼语来书写。[ A Barnard, Diverse People Unite: Two Lectures on Khoisan Imagery and the State, Edinburgh: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Edinburgh University, 2003.]对于南非新政府来说,迫切需要有一个国家建设的象征与符号,并能调和种族之间的仇恨;为了反思种族隔离,政府在原则上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和尊重少数族群权利,布须曼人可以成为这个后种族隔离政权的象征,所以新南非政府对同布须曼人的谈判持相对开放与支持的态度,极尽所能满足他们的诉求。其次,新政权开启了“有色人”身份政治与认同的新时代,人们讨论并发展了比种族隔离时期人为强加的分类“有色人种”更适当的新身份。随着南非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近300万有色人开始探寻他们的根源,并开始自称为科伊人或桑人(布须曼人)。他们只有利用土著人的身份概念,才能获得土地和资源、经济机会和政治上的承认。
纵观布须曼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流动的史诗,他们的足迹遍布南部非洲,哪里有水源和食物哪里就有他们的生存遗迹。然而随着殖民入侵,他们被迫迁徙到生存条件恶劣的卡拉哈里沙漠中,练就了一身狩猎采集游牧生活的绝世本领,但这身本领却在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大潮中被淹没被遗弃……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劳伦斯以及其他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作品[ J Solway, “Culture fatigue”: The state and minority rights in Botswana.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2011, 18(1):211-240; J Maruyama, “From ‘space for ruling’ to ‘space for living’: Indigenous peoples’ movements among the San in Botswana” (in Japanese), Jap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12,77(2), pp. 250-272; M Pelican & J. Maruyama, “The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 in Africa: Pespectives from Botswana and Cameroon”, 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2015, vol(36),no.1,pp.49-74.]来了解布须曼人怎样在沙漠中生存繁衍。这本《荒漠之心》看到最后,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劳伦斯关于措迪洛神山的那段描述,他们因为对神山的不敬而遭遇所有摄影录音设备失灵的厄运,在半个多世纪后的2011年2月26日,我去游览这个博茨瓦纳唯一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时,同行的当地导游向我发出了同样的警告:措迪洛山是一座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这里保存着三千多年前布须曼人留下的岩画,先民们的神灵居住在这里,来这里的每个人都要心怀敬畏,不能破坏这里的任何东西,曾经有人打死了山里的动物,他带来的所有摄像器材全部失灵……不知是当地导游看过了劳伦斯的这本书,还是这本书早已成为布须曼人口耳相传的故事。总之,关于布须曼人的传说,没有随风而逝,而是越传越远,甚至随着这本书中译本在大陆的出版,传到了21世纪的中国。让我们跟随劳伦斯的探险,重返人类的童年,找寻失落的灵魂,让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和神灵相遇……
徐 薇
2020年12月5日于浙师大非洲研究院
徐薇简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非洲人类学、种族与族群社会学、非洲华侨华人等研究,重点关注南部非洲与东非。她在2012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赴博茨瓦纳大学访学一年,曾多次赴南非、赞比亚、坦桑尼亚、喀麦隆、吉布提、津巴布韦等国进行调研访学。
许多人对荒漠布须曼人的认识,恐怕都来自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上帝也疯狂》。在这部电影中,布须曼人所展现出来的善良、纯粹、“无知”,给无数人带来笑料,继而感动或沉思。他们代表着“人之初”,是人类自蒙昧时代走出后,留给世界的最早影像。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他们锻炼出了一身有用的本领:能够在狮群中来去自如而毫发无伤;知道如何骗过鸵鸟,使其变成“母鸡”为自己下蛋;更知道如何在荒漠中保存好珍贵的水资源以备不时之需。他们征服了世界上最贫瘠的土地,却在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中败下阵来,以至于行将灭绝。在近代的殖民战争中,他们被形容为肮脏的野蛮人、无耻的小偷、残忍的野兽而肆意虐杀,甚至在历史上也未有一席之地。然而,随着作者的脚步深入蛮荒的沙漠腹地,我们才得以一窥这支古老民族的真实面貌,他们依然保留着的纯粹、善良和创造力,一一戳破侵略者的谎言,使我们得以一窥人类历史长河中这支闪光的民族及其伟大的历史、文化、艺术。
消失的民族
这是一个述说跋涉过无垠荒漠,追寻一支在我家乡南非境内独特而几近消失的最早民族——非洲布须曼人(Bushmen)残余后代的故事。事实上,这趟旅程一年多以前才开始,但在我内心深处,它远在更早之前就开始了。的确,早到我根本无法精确指出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只记得,自有记忆以来,我的想象就像手伸入手套那般,自然地滑进了和那些矮小的布须曼人及其悲惨命运无比密切的关系里。
我出生在靠近“大河”一带的地区,有好几千年的时间,这里一直是布须曼人的大本营。虽然他们现在实质上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我自出生后,就生活在许多有关布须曼人及其文化的动人传说中,以至我总觉得和他们十分亲近。我常从周遭人的口中听到他们的事迹。比如寒冷冬天的晚上,在我母亲位于“狼山”(Wolwekop, the Mountain of the Wolves)的农场的露天火炉边,或是围绕着营火时,衬着背后胡狼的悲鸣,以及附近村庄羊圈里一头刚出生的小羊害怕的叫声,夜行鸟在黑暗的平原上哀泣,像水手长的长哨声。这时,已消失的布须曼人就会鲜明地出现在某些艰辛的拓荒回忆中。在这些回忆中,一个快活的、英勇的布须曼人,往往会逐渐变得爱恶作剧、反复无常,最后转为死不悔改、傲慢挑衅。他们虽然已经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但仍悄悄潜藏在周遭有色人种的血液里而不为人知,一如他们从前悄悄追踪着非洲大陆上那不计其数的猎物时一般。我出生后,他们出现在我第一个奶妈的眼睛里,她闪亮的眼睛暴露了某个古老悠久的非洲时代令人无法置信的第一道光芒。他们也出现在其他人种身上:这里一点布须曼人的血统,那原本好看的班图人(Bantu)的脸上,就有了一对不搭调的细长的小眼睛;那里一点布须曼人的血统,又使得一个好看的中非黑人有了杏黄肤色,或是说起话来像布须曼人那样不时迸出类似弹舌的拟声词,那是布须曼人为侵入者原本铿锵有力的腔调所添加的元素。
我越长大,越遗憾没能早一点出生,没机会在布须曼人原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认识他们。有许多年我都无法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布须曼人相通的大门已经关上了。我不断寻找和他们有关的各种新闻、消息,好像随时准备迎接那扇大门再度开启,而他们会再度出现在我们中间。事实上,我相信我人生中第一个有关生命的客观问题就是:“布须曼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无论种族、肤色,只要是有可能曾和布须曼人接触过的人,我都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甚至问到了令许多原本有耐性的人也受不了的地步。那时还是孩子的我,执拗又不懂事,事实上,他们已经告诉了我不少,但他们所说的却只会让我想知道更多。
他们说,布须曼人是一群个子很小的人,但并不是侏儒,也不是小黑人,就只是身高不高,只有约一米五。他们四肢匀称,身材结实有力;肩膀很宽,手脚却极小。我们最老的索托(Sotho)仆人告诉过我,只要你在沙漠里看过一次他们那细小的脚印,就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脚踝细瘦,跟赛马一样,双腿柔软灵活,肌肉放松,跑起来像一阵风,又快又远。事实上他们移动的时候从来不用走的,而是像瞪羚或野狗般轻快地小跑。在大草原和大圆石上,没有人可以跑得像他们那样快。你可以在大太阳底下发现许多巴苏陀人(Basuto)和科拉纳人(Koranna)孤单的枯骨,足以证明其想远远超越布须曼人的企图,只不过结局是全然失败。他们的皮肤松垮,很容易就变得皱纹处处。当他们大笑时,脸上会出现无数细小的纹路和褶皱,纵横交错,织成可爱的图案,而他们又很爱大笑。
我那信仰虔诚的外公解释说,他们这种松弛的皮肤是“上帝的杰作”,因为可以使布须曼人一顿就吃下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民族的人都要多的食物。由于他们以狩猎为生,也就必须尽可能地将大量食物贮存在自己的身体里。结果,当饱餐一顿后,他们的肚子就像怀孕的妇人那样鼓起来。在狩猎成果甚丰的季节里,他们的身体会像鲁本斯画笔下的丘比特那样,前凸后翘。不仅如此,这些原始的小布须曼人的身体还有一项特色,即他们的臀部功能恰如骆驼的驼峰!大自然赐予他们这一能力,好让他们储存额外的珍贵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以对抗干旱和饥饿的时刻。我想我所学到的第一个科学名词,正是解剖学家赋予布须曼人身体这种现象的名词:臀脂过多(steatopygia)。
有一夜在火边,我似乎记得我的外公和大阿姨说,每逢艰苦的季节,布须曼人的屁股便会缩小,直至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差别是,在他们光滑的臀部和柔软灵活的双腿之间,多了很多细密的褶皱。但是在狩猎季收获甚丰的时候,他们的臀部就会再度突出,而且可以在上面摆放一瓶白兰地,外加一个高脚酒杯!我们听到这里都笑了,不是嘲笑,而是带着一种骄傲和欣喜的感叹,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家乡竟然有这么独特的一类人。
不知怎的,我的心思和想象从此被布须曼人的体型这件事深深地占据了。虽然霍屯督人(Hottentots)和他们长得也很像,而且我也一样喜欢,但他们就是没法像布须曼人那样使我兴奋——他们的个子太高大了。布须曼人则刚刚好,他们那短小的身材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每当我的母亲讲故事给我们听,说到一个小矮人会耍弄神奇的把戏时,他的形象立刻在我脑海里转换成布须曼人。也许我们这种人的人生——开始时作为孩童,渴望长大成人;长大成熟后,却又希望找回自己的孩童本质——特别需要找到某种孩童与成人完美结合的清楚形象,就好比完美结合这两种元素的布须曼人。唯有如此,我们那困惑的心灵才能稍稍释怀,安适地留在于这两者之间循环往复的短暂片刻中。
不过,尽管布须曼人的胃口、身材和肥臀相当惊人,这些也还不是他们的身体仅有的特征。我听说,他们的肤色跟其他非洲民族不同,是一种好看的普罗旺斯的金黄。我曾提过的老巴苏陀人告诉我,布须曼人最惊人的体质特征之一是,就算他们不穿衣服,皮肤也从不会被太阳晒黑。他们在炫目的非洲大地上移动时,像一抹金色的火焰闪过,仿佛中亚草原上年轻的蒙古族小伙子。他们的双颊也像蒙古人,颧骨高高耸起,相距甚远的两只眼睛斜吊着,以至我的祖先有些人直接称他们为“中国人”(Chinese-person)。在南非,有一块被青山包围的大平原直到今天都还叫作“中国草原”,因为布须曼猎人曾经住在那里。他们的瞳孔是暗褐色的,是一种除了羚羊之外,你在任何其他动物身上都看不到的那种褐色,清澈闪亮,像十分罕见的有露水的非洲清晨那褐色的天光,具有无比强的穿透力和无比高的精准度。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视力所不及的遥远地方的事物,这已经成为非洲英雄传奇的一部分。他们的脸型通常像心脏的形状,前额很宽,下巴柔而尖;耳朵像牧神,尖而匀称;头发是黑色的,浓密地长成一卷一卷的,被我的同胞轻蔑地比喻成“胡椒子头发”(pepper-corn hair)。他们的头是圆的,轻巧平顺地连接在细长的脖子和喉头上,下面是宽阔的肩膀;鼻子通常宽而扁,嘴唇厚实,牙齿整齐而发亮;臀部很窄,而且就像我阿姨说的:“天啊,他们移动的样子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但也许布须曼人最令人惊讶的特质,还是他们的起源。即便是身体最深处、最隐秘的部分,他们也和其他人种非常不同。女性一出生,在她们的生殖器上就有一天生的小阴唇,即所谓“埃及围裙”;男性则从出生到死亡,性器官永远呈半勃起的状态。布须曼人为这一生理特点感到自豪,丝毫不想加以掩饰。事实上,他们不但完全接受这个与众不同的重要差异,还以此特征称自己的民族为“科怀-兹克威”(Qhwai-xkhwe),并公开宣扬这个事实。这个词从他们嘴里所发出的声音带着一种毫不造作的沾沾自喜,实在美妙好听,而当他们说这个词时,复杂的音节夹杂着轻微的弹舌声,像阳光洒在阴暗的山上一朵盛开的荆豆花上。他们甚至将自己画在非洲所有的岩壁上,这些裸身的侧影坦率地表现了属于他们自己种族的这一特征,一点也没有某些欧洲考古学家所认为的猥亵意涵,单纯只是因为他们的神早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就深思熟虑地将他们塑造成如此形状,赤裸但无须羞赧。
关于他们的一切,似乎只有一点让他们感到苦恼,那就是个子。我对他们无尽的反抗精神印象深刻,那是我所遇到过的许多矮个子人身上都具有的精神,同时我也看到这种精神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其他生命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我并未忘记在整个种族群体的情绪和政策的驱动下,这种反抗精神所带来的灾难。当我还是日本人的战俘时,不断被处以苦刑,我相信原因只不过是我的个子比那些俘虏我的人高。然而我怀疑,布须曼人对自己个子矮小的反应并非因此,那种反应是因为无力抵抗那些比他们高的人无情入侵他们的家园而产生的。事实上,那些人太高了,以至于布须曼人把他们一起画在岩壁上时,简直就像被巨人包围!知道他们的人心里都很清楚,一提到个子,他们的神经就会变得敏感而脆弱。据我们最喜爱的阿姨(她为了逗我们开心,会用布须曼语从一数到十,并使用布须曼人见面打招呼的正式用语,而为了发出这些声音,她几乎使自己窒息)表示,如果当着布须曼人的面提起他的个子矮小,后果将十分严重。还有,即使没说出口,但若在行为举止上显露出你很清楚你是在和一个个子比你矮很多的人打交道,后果也同样不堪设想。
我们的老索托仆人也用他们生动的描述支持我阿姨的说法。他们说,他们一再被警告,如果在大草原上和布须曼人不期而遇,千万不可露出惊讶的神色,以免被他们误解为,若非因为他个子矮小,你早就看见他了。因此,当一个人因意外和布须曼人相遇而露出惊讶神色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责怪自己:“请不要介意。你想一个这么大的人怎么可能藏得看不见?但是我们搞不懂为什么刚刚才远远看见你,怎么一下子你就到了面前!”于是那对闪亮眸子中的怒火马上熄灭,金黄色的胸膛立刻张开,他会非常有礼貌地欢迎你。事实上,老巴苏陀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曾经告诉我,最好是用布须曼人的方式向他们打招呼,也就是把右手打开,高举过头,然后大声说:“特西雅姆(Tshjamm,你好),我老远就看到你了,我快饿死了。”
——摘自《荒漠之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8元,2021年3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