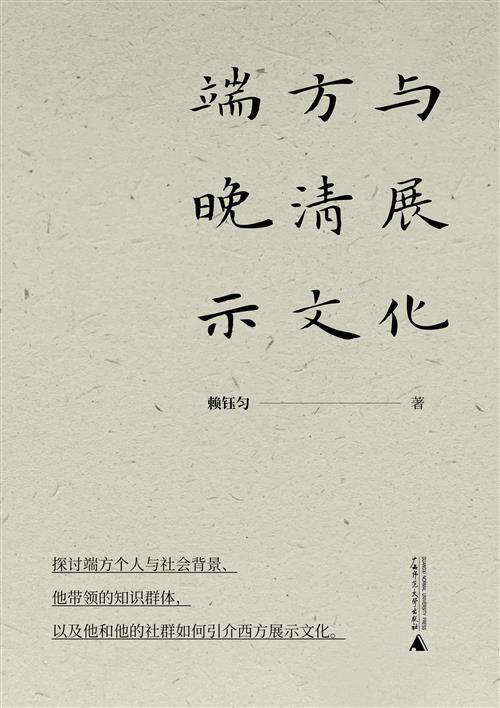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1-07-01
定 价:58.00
作 者:赖钰匀 著
责 编:邢文桦
图书分类: 传统文化
读者对象: 高校师生,近代史学者
上架建议: 近代人物
开本: 32
字数: 200 (千字)
页数: 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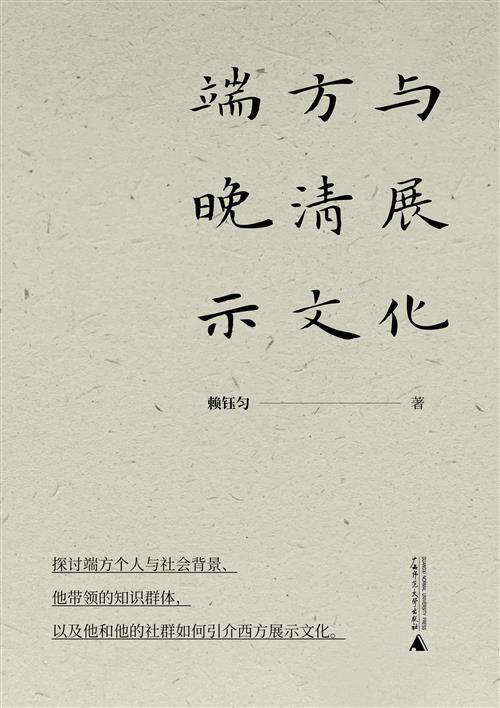
“展示文化”是晚清重要的文化现象,与清末中西文化交流息息相关。本书从以端方为代表的晚清鉴藏群体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传统的雅集鉴赏活动以及西洋展示活动的完整引进与发展。端方与其背后的鉴赏团体形成了一个沟通中国传统收藏活动与西洋展示文化的桥梁,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本书对研究晚清艺术收藏史与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参考价值。
赖钰匀,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翻译员。研究方向为晚清思想文化史、艺术史。曾发表论文《天道与群道:严复思想初探》、《端方与晚清展示文化》。译著《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沈录》。
前言
代序 端方之死对清遗民文化圈之影响
第一章绪论
1.1 问题意识:晚清知识群体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认识与转化
1.2 对于题目的说解
1.2.1 关于展示文
1.2.2 关于知识群体1.2.3 关于赏鉴传统
1.2.4 以端方为个案研究的考虑
1.2.5 金石学:知识群体的认同核心、赏鉴传统与展示文化的交会点
1.3 相关文献回顾
1.3.1 艺术品味与文化资产的文献综述
1.3.2 关于晚清展示文化的文献综述
1.3.3 与本书相关的端方研究
1.4 研究视角与方法、研究时段
第二章 晚清展示文化的兴起:端方之前的使西使节团
2.1 引言
2.2 词汇的混用与博览会的内涵:珍奇与商战纷然并存
2.2.1 “南洋劝业会”一词的使用
2.2.2 光绪初年“使西日记”译词混用情形
2.3 首任驻英法使节团与博览会
2.3.1 黎庶昌与郭嵩焘的巴黎博览会记录
2.3.2 郭嵩焘对于其他博览会的关注
2.4 郭嵩焘驻英法使节团对博物馆的记录:博览会之前的博物馆
经验
2.4.1 大英博物馆 \2.4.2 南肯辛顿博物馆
2.4.3 郭嵩焘对于中西学术的态度:兼容并蓄、字斟句酌
2.5 本章小结:“博览会”与“博物馆”的离合——兼论译词的
使用与中西知识系统中的“博物”
第二章晚清展示文化的发展:从上海博物院到南洋劝业会
第三章3.1 引言
3.2 中国人首个博览会的流产:郭嵩焘与上海博物院计划
3.2.1 上海博物院计划与上海格致书院
3.2.2 首任驻英法使节团与上海博物院计划
3.2.3 上海博览会计划失败的原因
3.3 端方与五大臣出洋:端方参访博览会与博物馆的经验
3.3.1 端方出使前参与博览会与博物馆的经历
3.3.2 五大臣出洋:端方出使期间参访博览会和博物馆之经历
3.4 端方的博览会与博物馆事业
3.4.1 筹划办理南洋劝业会
3.4.2 端方与南通博物苑
3.4.3 端方与陶氏博物馆
3.5 本章小结:郭嵩焘与端方的比较
第四章 端方及其周围的知识群体:中西之间的趣味
4.1 引言
4.2 以端方为中心的知识群体与文化活动
4.2.1 故人桂莲舫之侄:端方与翁同龢及南清流
4.2.2 从“端午桥”到“端忠愍”:端方与叶昌炽的交谊
4.2.3 全方位的文化事业合作者缪荃孙
4.2.4 杨守敬
4.2.5 满族秀异:盛昱、溥伟、志锐
4.2.6 僚属、宾友、幕客
4.2.7 名士名宦:张謇、郑孝胥
4.2.8 友朋、后进:罗振玉、王国维
4.2.9 外国友人:福开森、莫理循、内藤湖南
4.3 本章小结:鉴赏集团与展示文化
第五章 端方的收藏经历与金石著录
5.1 引言
5.2 收藏经历
5.2.1 京官时期: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89—1898年)——以藏石为起点的收藏家
5.2.2 陕西布政使时期:光绪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98—1901 年)——收藏青铜器的开始
5.2.3 湖北巡抚时期:光绪二十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1—1905 年)——对中国书画的兴趣
5.2.4 出使西洋时期:光绪三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5—1906 年)——扩大收藏的品项与眼界
5.2.5 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时期: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906—1909 年)——公共展览的准备与推动,搜罗保存,敦煌写本
5.3 藏品流向
5.3.1 由福开森等人直接中介卖往欧美各国
5.3.2 由日本商人介绍,辗转流至欧美
5.3.3 日本收藏家直接收购收藏
5.3.4 由当时或稍晚的中国其他收藏家收藏
5.3.5 文物辗转流到台湾
5.3.6 由国内文物单位、研究单位与博物馆保存
5.3.7 端方分赠海外君王、友人与博物馆
5.4 端方的金石著录与晚清展示文化的关系
5.4.1 端方的金石著录内容简介: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
5.4.2 端方金石著录的著作主旨:端方的金石著录在清代金石著录中的定位
5.4.3 金石著录与晚清展示文化的关系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
6.1 以端方为核心的知识群体对于晚清展示文化的贡献
6.2 近代知识阶层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
6.3 余论
前言
本书以端方(午桥,1861—1911 年)这位晚清倡议举办全国性博览会、创办私人博物馆、较早使用新式印刷术行收藏目录并保存藏品的先驱者为视角,考察晚清展示文化活动的发展。晚清历史学界素来重视中西文化交流激荡的问题。知识群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虽已在公共空间、文化活动与教育出版事业等文化史范围被研究,但探讨知识群体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著作仍属少数。除了讨论端方个人与社会背景,本书研究端方背后何以能形成一个艺术鉴赏方面的知识群体,以及他如何在引介西方展示文化的过程中运用此群体,借此考察知识群体如何协作沟通中西文化的问题。本书草创迄今,已历十载寒暑。这十年间,文化史或艺术史领域对于传主端方的研究日益增多,以艺术鉴赏为凝聚核心的知识群体研究更有长足的进步。a 所以不揣浅陋,让此书付梓面世的原因,爰有以下数端:
(一)研究主题。本书以晚清的展示文化现象切入,并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端方及其周围的鉴赏集团,补足过去史学界的研究。
(二)研究时段。过去研究展示文化的断限多以1911年左右的展示活动与出版品为主,本书将研究断限上推至同治光绪年间,有助于完整晚清到民国之间的相关研究序列。
(三)研究内容。过去的研究多半注意端方出使西洋的经历对于其展示活动的影响,本书以端方之前的首任驻英法使节团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使节团,是开创性的研究。
(四)研究方法与视角具备新意。过去对于端方收藏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单一人物研究,而本书强调晚清“知识群体”的概念,并有别于过去仅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外缘角度诠释知识群体面对中西冲突的抉择,而以该知识群体具备的知识背景和金石学素养与文化品味(Taste)为切入点,以明代为例,白谦慎教授较早注意到书画家的社会文化脉络,例如《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 年)、《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年)等。近年来,白谦慎教授以晚清学者收藏家吴大澂为中心,注意其社会交际圈对传主收藏与研究的贡献,足见艺术史领域已不满足于以单一人物为中心,转而注意群体性。本书与前贤略微不同:其一,端方以权位笼络英才,其周围赏鉴集团亦客亦友,有较强的凝聚力;其二,本书虽然重视端方的人际交往,且选择以知识分子为案例,并非因为端方周遭仅有知识分子,而是因为这个知识群体凸显了中西文化融会过程。曾有学者提出笔者为何要标出端方不同阶层的社会交际网问题。盖当时虽已有艺术史学者重视研究传主周围的文人群体,但是像端方这样交游广阔的封疆大吏,身边不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阶层,更充斥着收藏世家的前辈、经纪商、幕僚、师
友乃至外国友人等,将之复杂的交际圈以简图的形式标出,亦在强调此多种不同的群体以
端方为核心聚集,同时个体、群体间也略有重合,使得其交际圈显得立体。从学术对话的层面凸显了晚清金石学和西方展示文化的交融。
(五)研究资料。本书精选一手档案与清人笔记、日记、书信和各种题跋,辅以第二手文献作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范式参考,使用了以前较少为研究者深入运用的材料。本书第一章为文献回顾。由于精力所限,2011 年以后的部分二手文献未及录入。鉴于过去的文化史研究注意端方出使西洋的经历对于其展示活动的影响,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前半部分加入端方之前的首任驻英法使节团作为对照组,具体研究展示活动在使节团出使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展览会在中国创办的过程,由此探析端方之所以能够相对完整地引进西洋展示活动,乃因其背后的幕僚形成一个庞大的赏鉴集团。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此集团的成立和聚合,通过该集团日常的文化活动、交谊和收藏品味,发掘此集团所具备的“双重性”:这个集团一方面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雅集与鉴赏活动的精髓,特别在晚清的金石学话语圈中的相对强势背景,另一方面又成为南洋劝业会的规划者以及端方博物馆的第一批看客。在前述研究端方创立南洋劝业会与私人博物馆的成果和领导该赏鉴集团的成果后,本书第五章接着研究端方的金石收藏和金石著录。《斋藏石记》和《陶斋吉金录》的出版,从新式照相技术与传播媒体的角度体现了端方参与西洋展示文化的另一面成果。最后,本书在实证研究中,认为端方与其周遭赏鉴集团对中西文化的沟通,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从知识群体的角度看,端方及其背后的鉴赏集团形成了一个沟通中国传统与西洋展示文化的桥梁;从收藏的角度看,端方的金石著录和博物馆则表现了一个私人藏家“由私到公”的进程——这个进程也象征了晚清金石学由私人化到公众化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显示,西洋的展示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收藏活动,不只是由于外缘因素而有沟通的可能,更是因为金石学内在转化的动力促使一群兼具中西
经验的知识分子作为桥梁,为曾一度走向私人化和精英化的清代金石收藏开辟出一条新的面向大众的路径。至此,本书可说开展了金石学传统与西方展示文化对话的可能,从过去研究者没有注意过的理论高度诠解了端方进行中西文化沟通的文化史和学术史内涵。
然而,本书犹有憾者:为了让郭嵩焘驻英法使节团作为端方使节团的对照组,传主端方与其周遭的知识群体迟至第三章出场。经过思考,笔者决定将一篇旧文《端方之死对清遗民圈之影响》作为代序。此文作于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借由端方之死对清遗民的影响体现端方生前身后确曾为一方政治和文化界盟主的事实,使传主和周遭知识群体提前出场。希望这
样的调整,能使全书的开展更为顺理成章。
本书可说开展了金石学传统与西方展示文化对话的可能,从过去研究者没有注意过的理论高度诠解了端方进行中西文化沟通的文化史和学术史内涵。
2.5 本章小结:“博览会”与“博物馆”的离合—— 兼论译词的使用与中西知识系统中的“博物”
重新省视早于端方出洋 30 年以前,首任驻英法使节团“使 西日记”中的记录,并非单纯地为了做背景铺叙,而是以比 较的视野,重新省视在晚清展示文化初兴时,这种译词混用 的现象背后的含义,避免以光绪末年或者现代性的眼光介入 其中,以诸人对于西学的赞扬或反对态度作为评判功过得失 的标准。相反,其目的是要探究什么样的事物是被这些士大夫认为可以或值得记录的,是怎样的知识训练或者思想背景让他们选择记录这些事物而非其他,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 对于博览会、博物馆或其他与展示相关的事物有着不同的评价与看法;从“使西日记”材料厘清晚清展示文化开始传播到中国的初期,第一批正式的驻外使节以及受过良好中国传统训练的士大夫是如何理解博览会与博物馆,通过他们的记录焦点与对译词的使用,意图凸显在概念层次上,博览会或
博物馆这些观念,如何被中国的知识群体理解与吸纳。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接纳,连接的是中西之间的知识系统。然而,“博览会”“博物馆”“博物”等词汇之间复杂的离合重叠关系,虽然困扰着研究者,但也是一把通往理解中西两个知识系统 的钥匙。本章一开始,探究了“赛会”与“博览会”的不同, 将这两个词汇所涉及的奇珍与商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范畴做了探讨。本章的结语,则将对于“博览会”“博物馆” 这两个词汇间的离合,再根据“使西日记”的材料做进一步说明,并且探究“博物”一词在中国知识系统中的对应位置,以及这两个词汇交错使用所折射的意义。博物馆与博览会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离合关系?虽然晚清的端方等人已经逐渐分别出这样的概念,但在光绪初年的日记中,仍不十分清楚。中国古有“博物”一词,当时日本也已开始使用“博物馆”一词,随使的张德彝也知道该词汇。这个译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传播和报道。为什么郭嵩焘很少单独使用“博物馆”一词,而是用音译的“妙西因”或者其他词汇?与郭嵩焘同时而稍早的佐野常民认为,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区别在于:“博览会者,乃与博物之宗旨相同者也……大博览会只不过是一个将博物馆规模扩张的暂时性设施。故而两者经常为若即若离的关系。”a
从郭嵩焘对于大英博物馆与南肯辛顿博物馆所用译词的不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英博物馆的设立,是以私人收藏为基础,进一步转为向公众开放的展示空间。而南肯辛顿博物馆,却是以伦敦博览会为基础改造而来。二者就性质而言,虽然在名义上,都称作博物馆(Museum),但由于从不同的展示空间演化而来,南肯辛顿博物馆是作为博览会(Exhibition)的延续,属博览会的系统,收藏的目的,也是着重于展示具有经
济价值的产品为主,有别于大英博物馆以珍奇标本和浩瀚的藏书取胜。郭嵩焘的时代,“博览会”与“博物馆”这两个名词还没有确定。因此,郭嵩焘等人使用的词汇,正好展现了在接受展示文化初期,他们对于博览会与博物馆存在不同的认知。对于大英博物馆,无论是郭嵩焘、刘锡鸿还是张德彝等人,所使用的主要词汇是“书院”“书馆”等词,并搭配音译,组成了半音译、半意译的词汇。这时,他们所认知的博物馆这类机构,是对应于中国的教育机构。而当郭嵩焘参观南肯辛顿博物馆时,他曾经听闻这也是一个“博古院”。而这时,他采取了完整的音译词——“妙西因”,更明确说明妙西因是陈设之意。
这是他对于展示文化机构的一点极大的补充与认识。而从大英博物馆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记录侧重点不同,也可看出,虽然当时对“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名词还不能够做非常清楚明白的厘清,但是中国当时知识分子认为这两者所代表的内涵,仍然是略有出入的。有别于佐野常民氏所说的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宗旨相同,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仍然较为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而对于博览会则是倾向于认为是各国争奇斗巧,以及其
中获取的后续商业利益的场所。那么,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将这些词汇混用,没有骤然使用“博物”“博览”的词汇,跟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有何关系?首先必须说明,中国传统对于“博物”一词 的使用,本身就有多种含义,并非完全正面的。“博物君子”,固然是美词。“博物洽闻”“博物多闻”等,往往是用来形容一个人见识广博,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并不能够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代表或者学术内涵。魏晋以下的《博物志》采用了“博物”一词,但其内容,却不见得为正统出身的知识分子所认可,而往往被认为不过是传闻异词的志怪之流。特别是自宋代至清代,在中国儒学系统中,尊德行与道问学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径时有沉浮之势。追求广博的见闻本来并非儒者所专注之事,勉强来说,只可算是道问学之一端,与道德心性并无关连。因此,博物这种专向外界探寻的方式,并不能在正统学术中取得任何地位。对于这一点,民国初年的博物学者,时常加以诟病,认为这是中国博物学之不振的悲哀。实际上,这些学者完全没
有注意到,所谓的西方博物学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适当的对应学术领域,中国所用的“博物”一词,其内涵也与西方不同。这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在晚清表现得尤其强烈。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最早接触到西方展示机构,刘锡鸿用以比较西方博物馆中陈列的知识内容的书,是《博物志》《珍玩考》《格古论》这一类的书籍,都是中国子部杂家的作品,或者说,是在学术边缘的作品。这就是刘锡鸿心中所对应的知识系统。在他
的观感中,西方的博物馆,其实并没有多么了不起,其分量与子部杂家中一些博古、收藏类的书籍差不多。而郭嵩焘则不同,他所引据的,如《尔雅》《仪礼》等都是经部书籍。换言之,他是将西方文明去比附上古三代素朴的博物传统。将西方文明 的英锐发进,与中国上古三代相比,这是在晚清展现民族自信 心的一种特殊表现。同样的情形,也可在其他外交官(如曾纪泽)的日记中见到。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的“博物”一词内涵如此之复杂,而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将西式博物学所比附的中国学术,也有高低不同的看法,因此,才会没有出现一个简单直接的译词“博物馆”。事实上,这种复杂的用法,正透显出了晚清时代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对话时,是如何调度传统文化中各种丰富的文化资源,加以理解并融摄西方文明,而不是简单地像民初博物学者批评的那样,认为是晚清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地理解“博物馆”的内涵。正如前面所述,中国传统“博物”一词的内涵本身就并不单一。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词汇表现出中西知识系统的何种差异性?中国“博物”一词的内涵和近代西方的“博物学”“博物馆” 或“博览会”概念略有区别。“博物”一词指的是见识丰富渊博。乍看之下,似乎两者词意相近甚至熨帖。“博物”的内涵与“博物馆”的内容与意旨并无捍隔,并可互为补充。中国传统的“博物”和“博物馆”与“博览会”的近似之处是“博物”是闻见之学,而“博物馆”“博览会”则是重视耳目之教。然而,博学闻见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通过阅读文本或传闻来获取知识;耳目之学则重在展览的立即实效。细究两者的内涵,由于时空条件不同,仍略有出入。然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广泛地存在于各种新旧或中西知识的交界缝隙之处,不足以为“博物”和“博览会”“博物馆”区分为二的判准。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区别乃在于分类系统与安排展示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博物”一词,并不涉及知识分类的内涵。中国第一部以“博物”为名的《博物志》,实际上也与知识分类架构毫无关系。虽然其立意在于博采异闻、增广见识,但内容偏重志异记怪,所以《博物志》早轶,其目录已不可见。即使从现在可见最早的明人辑轶本来看,《博物志》的结构不同于西方经过分类,将人类智能与知识以不同的种类区别开来,再加以展示,传达出知识建立者欲
安排的秩序,以及被规定过、被认为适合展示给市民、国民或预设受众参观的博物学。中西对于“博物”一词的侧重点也不同。中国传统的博物,重在博通;而西方的博物学,恰恰是一个有着严格框架,重视专门分科的系统。佐野常民注意到了博览会与博物馆之间的离合,并非以展示的内容为区分,而是以陈列的时间长短与常设性与否为判准。这样的眼光,与中国知识分子是相当不同的。在“博物馆”这一译名草创之初,可以看到
中国知识界与日本知识界的知识背景影响了对于“博物馆”一词的接受与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未对“博物馆”一词进行明确的定义,何种展示机构或者知识传播机构被称为或应该被称为博物馆,仍是相当困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因此,“博物馆”一词尽管已经以汉字的表达形式出现了三十多年,到了端方的时代,虽然大抵已经能够区分几个词汇的不同,但仍会因应实际的状况而调整,有时也会出现混用或者语焉不详的状况。这并非单纯由于词汇本身的问题,或者单纯的音译、意译的问题,而是背后有着更加深遂的象征意义与价值取向。郭嵩焘与同时代的人物没有立即而全面地采用“博览会”与“博物馆”一词,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知识系统中徘徊摆荡的必然结果。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